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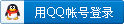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毕玉谦 中国政法大学
一、关于阐明权的界定
在民事诉讼上由法官所享有的阐明权是由公法意义上的程序规则与民事诉讼主要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私权纷争这一矛盾交汇点的产物。民事诉讼具有保护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属性,从而使辩论主义成为一项支柱性的诉讼原则。在辩论主义架构下,为民事诉讼法所设立的用于保护当事人私权利益、确定某项权利存否及归属的法定程序,法院在裁判上所考量的范围只能限于当事人请求的范围以及为其请求所提供的诉讼资料。凡当事人未请求的利益,法院不得予以裁断,凡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或证据,法院不得予以审查确定。但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使得这种内在实体内容得以调整的程序规则则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妥当、效率等一系列价值内涵。这种公法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职权主义的体现,它有利于澄除由于极端采用辩论主义所产生的某些价值观念上的盲点,使得采用正当程序用于解决社会冲突而避免采用远古时代那种优胜劣汰的简单粗暴方式成为一种现实的抉择。从历史的发展轨迹给两大法系各国在立法、司法上所打下的烙印来看,适度的职权主义倾向有利于克服辩论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可以说,适度的职权主义有利于保障辩论主义本旨的实现。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上有各种表现形态,其中包括法官阐明权的行使。应当说,作为职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的监管权力之上,这种监管权力的行使主要体现为对民事诉讼活动的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两种形式。
笔者认为,所谓阐明权是指,为了防止极端辩论主义对诉讼的公正性所造成的损害,当遇有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声明、陈述或举证上存在不甚明了、不尽妥当、有所欠缺等情形时,由法官向当事人进行适当发问、提醒、告知其作出释明或者予以明了、补充、修正的一种权力与职责。这种权力行使的效果主要体现在,能够使有关一方当事人在遇有特定情形时获得司法上的必要救济。
在大陆法系,阐明权的形成来自这样一种理论悟识,即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围绕如何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从而引领诉讼沿着使得那些本应胜诉的人最终获得胜诉的结局,这无异于是在要求由一种理性之人在诉讼上提出妥当而完备的声明及陈述,以期获得预期的裁判结果。然而,现实当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实难达到一种理想状态,特别是由本人亲自诉讼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其提出妥当而完备的声明与陈述亦非切合实际。但是,仅仅因为当事人本人并不懂得获得胜诉的要领而丧失本应属于他的权益,将与司法正义的本旨相违背。对此,法官阐明权的行使将有助于克除辩论主义的这一弊害,从而发挥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及矫正功能。
从传统观念上而言,由于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间的强式对抗辩论主义,因此很难接受由法官采用阐明权的方式介入当事人的程序对抗之中来实施这种司法救济,但是,随着诉讼实践的不断激增、律师凭借玩弄诉讼策略作为制胜法宝的弊端日渐显现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英美法系国家原本竭力禁止法官主动介入当事人的程序对抗的态度已趋于缓解,并且还出现了引入职权主义模式、加强程序管理的迹象。
从阐明权行使的方法来看,通常是向当事人发问,故又称发问权。在德国通常称之为阐明义务或发问义务,而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被称之为阐明权。
关于阐明权的性质之认定,包括对阐明权的定性及法官如应尽而未克尽这一职守所产生法律后果的界定。阐明权的理论及学说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上源远流长,对这一权属的判定,期间时有反复,尚无统一的定论。早期在德国,有部分学说将阐明权视为训示性规定,而并非法官在职务上的义务,其效果为,即使不予行使,也不得将其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时至189o年初期的判例仍采用这一观念。但在此之后的情况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因为在此之后居于多数的学说及判例则一改前辙,进而将阐明权视为法院或法官的义务,如有违背,则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显示出职权主义的强化之势。在日本继受德国后期这一观念影响下,其大审法院所作判例始终认为,凡当事人主张的事实遇有不明了的情形时,法院应予阐明,此属法院的权利抑或一种义务,如未加以阐明而影响当事人就事实陈述不能明了,最终导致影响判决时,该判决即属违法。在日本学术界,处于非主流派的学者则持有与之相反的见解,多数学者观念与判例相一致。按照德国的判例及学说,凡违反阐明义务属于程序违法,可构成当事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相较而言,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对于违反阐明义务未有明确统一的见解,基本上是未将违反阐明义务、未尽审理职责、怠于阐明加以区别,而是混合使用。
笔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权是司法审判权在诉讼上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职责,而不宜定性为一种义务。因为,法官的这种阐明权,既是一种职务上的权力,又是一种职务上的责任。它并非是一种抛开法官职务的一种个人身份“权利”,因此,这种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也无从谈起。而“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侧重适用于处在平等诉讼主体地位的诉讼当事人之间。法官的这种特有职责可以理解为:既是一种职权,又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在实务当中,当因审理法官未能及时履行这种审判上的职责而导致一方当事人遭致不利裁判时,有关当事人可以此为理由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救济途径寻求司法救济。当上诉审法院发现有关法院法官未能及时履行这一审判职责有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时,可将案件发回重审。
二、阐明权的行使范围
所谓阐明权的行使范围,主要是指在何种情形下针对何种事项由法官行使阐明权,以便要求当事人进行相应的释明。当事人为了保障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正当性的需要,应表明提起诉讼请求的理由,这种理由通常包括事实上的陈述与法律上的陈述。由此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必要的攻击与防御态势,作为当事人言词辩论的对象。对法院而讲,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主张与另一方当事人的抗辩形成审理对象,经过言词辩论而形成裁判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如当事人主张某一特定法律效果时,应就该法律效果发生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进行陈述和证明,如果在此层面显有疏漏,法院应行使阐明权使其知晓;从法院的角度而论,当事人所声明的事实主张与诉讼请求究竟应与何种法律关系互有牵连,常有不尽明了的情形,就该不明了的情形向当事人进行发问,令其作出必要的陈述,也应属于阐明权行使的范围。
按照大陆法系的学理见解,一般认为,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主要表现于下述范围:
(一)为使不明了的事项予以明了而行使阐明权在诉讼上,如遇有当事人声明及陈述出现包括语义含混不清或者前后相互矛盾之处时,例如,原告请求被告给付房屋租金,但在其陈述事实理由当中又称持有被告的欠款凭据,请求被告清偿此笔欠款。在此项诉讼当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究竟是基于房屋租赁关系还是基于借贷关系,两者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相距甚远,裁判理由应当如何叙载,对于裁判的作出关系甚重,故此际确有行使阐明权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据此而形成审理的基础,法院进而便会作出不符合事实真相之裁判,为了使有关的事项得以明了则有必要对有关当事人进行释明。如在此情形下法官不及时行使阐明权最终将会构成有关当事人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这是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二)为了排除不适当的事项而行使阐明权
在德国,当遇有显然不存在胜诉希望的诉讼,法官可劝谕当事人撤回其诉讼请求;对于并非基于真实基础而作出的声明或陈述,法官可指令当事人就其真实性作出释明;对于无意义或带有欺诈性的声明及陈述,法官可行使阐明权将其排除。但是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种阐明权行使的效果并不具有强制性,即纵然在上述情形下不行使阐明权也不会导致违背审判职责,并且不能构成当事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而只能将其视为法院的权限所涉及的范围而已。
(三)当有必要弥补有关欠缺为使当事人补充诉讼资料时而行使阐明权
当涉及提出对不当声明或陈述要求当事人予以释明,如果处于补充诉讼资料之需所提出的声明或陈述的,法官应行使阐明权要求当事人作出释明,否则,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判例及学理均认为这已构成第三审上诉的理由。在细节上,德国与日本的判例学说似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德国的判例学说认为,在此,法官应行使发问权以便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来使有关事项得以明了,并求得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完整的构塑。但这一切必须以当事人所提出的攻击与防御方法为必要限度,法院也只能在此限度内将当事人就事实陈述所暴露的瑕疵告知并要求当事人作出必要补充,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资料出现缺陷时,应指令当事人加以补充。法院就此而作出的阐明被视为审判上的义务。按日本的判例则认为,凡当事人的陈述事实出现欠缺时,法院应指令其补充,这种做法并非违背当事人主义的原则而指令当事人另行陈述他种新的主张,而是就业已陈述的真实意旨加以释明,也就是对于其有密切相联的事项加以释明,以便为审理的进行促成一个完美的效果。
(四)为使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而行使阐明权
在大陆法系的理论学说上,就法院能否使当事人追加新的声明及新的陈述或将以前所提出的并非适当的声明及陈述变更为新的声明及新的陈述,颇有争议。即使在德国国内,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肯定者认为,法院不能仅凭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审判职责,即使当事人在诉讼上未作出何种陈述,未声明有何证据或未作出适当声明,法院也应就上述各诸事项主动予以发问,而不能直接将当事人的这些消极诉讼作为据为裁判的理由。例如,当原告基于被告对其特定物加以损坏而请求判令被告恢复原状时,如法院在经审查判断后认为该特定物已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时,应行使阐明权,提醒该原告注意,将恢复原状的请求变更为赔偿特定金额的请求。反对者认为,阐明权应仅限于辩论主义的范围之内,法院并非享有指令当事人就新的请求原因或新的抗辩事由进行陈述的权力。即使向当事人行使发问权,也应仅限于因攻击防御方法变更所牵连的事项。按照日本的判例见解认为,为了使审理获得正确的裁判结果,以便使本应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胜诉,法院应行使阐明权,指令有关当事人提出新的声明或新的主张,否则将构成第三审上诉的理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使本应胜诉者最终获得胜诉的结论”这一命题具有先验、先知以及先定后审的思想观念,从而使得法院的阐明权具有某种扩张性的锋芒,由此可以窥见到,阐明权的适用范围在这些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已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
《五)因当事人在举证上的欠缺而行使阐明权
就证据的提供而言,原则上,只有因当事人过失或误解其并无举证责任而致使出现未有举证的情形时,法院才有告知其提出证据的义务。所谓告知当事人提出证据,主要是就特定待证事实而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不提出证据时促使其注意。这种情形应仅限于按照诉讼的具体进程,当认为因当事人忽略、误解或确不掌握诉讼旨意而致使其未提出证据的情形,才有必要对其行使阐明权。假若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在经过调查之后,其结果对该当事人不利(如证据本身相互矛盾、内容并不确定、真伪无法判明等)而指令其再加提出证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能证明待证事实,而指令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的情形,则属于超出阐明权的行使范围,显为不当干预之举。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法院对于证据上阐明权的行使,应在当事人业已有何种主张或声明,而漏未提及其有何证据时才能为之。因此,法院不得在欠缺上述情形时指示当事人应为何种主张、何种主张较可获得利益、何种防御可以免除责任,或者何种证据易为法院所接受。
三、两大法系各国对阐明权的认知与功能定位
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比较来看,.尽管各国对法官行使阐明权的表现形式和涉及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于诉讼上是否需要法院从事程序管理及是否需要行使阐明权的问题, 而是存在着法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行使这种阐明权来从事程_序管理的问题。从传统上而言,英美法系国家更依赖于当事人在程序上占主导地位来开展诉讼活动,由此而引发出来诸如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实施证据突袭、节外生枝的诉讼请求与抗辩等情形,这些都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使整个诉讼过程几乎成了演练诉讼技能从而获得审判上优势的竞技场。“很长时间以来,以所谓‘竞技理论’为特征的对抗性程序有其自身的问题这一点已被广泛认识。这种程序过分依赖于当事者各自所拥用的资源。开庭审理的集中对决方式总是伴随着不意打击的危险。”这些弊端在近几十年来引发许多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开展程序改革,即借鉴大陆法系的程序管理原理,从强化法官的职权管理职能的角度来对诉讼的正当程序加以实质性的保障。与法官的程序管理职能以及行使阐明权的程度与范围具有密切关系的便是律师强制代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具有普通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进行诉讼时,必须由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两大法系各国在实行这一制度时有所不同。例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等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等实行的是这种律师强制主义,而大陆法系的日本等以及英美法系的美国等并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主义或者没有实行完全的律师强制主义。
对于美国而言,在立法上虽然没有采取律师强制主义,但是,事实上,在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人都有律师进行代理。这是因为,美国的诉讼程序除了凸显的对抗辩论模式之外,由于法律的庞杂以及诉讼程序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具有事实上很高的技术要求,以至于如不采用律师代理,将会使当事人在诉讼上感到寸步难行、无所事事。抛开英美法系的对抗辩论式诉讼模式姑且不论,即使在大陆法系更为注重法官的职权作用的情形下,往往需要法官通过行使阐明权来使包括法官在内的三方主体对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形成必要的共识或相近的认识,虽然法官在这一过程当中通过行使阐明权来发挥这种统合作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将其对法律的理解强加给各方当事人,而是意味着为了达成这种共识,法官与当事人双方之间彼此借助于程序所开展的对话与讨论来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所发挥的应有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双方都有律师代理的前提下,法官行使阐明权则具有对等或平等的基础,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此前提下都具有利用各自的法律信息资源与法官进行对等或平等交流机会,都能够即时享有利用各自的诉讼经验来提出相关动议,启用一些程序或针对对方当事人诉讼行为或法官的职务行为提出异议的空间。如果仅有~方当事人有律师代理,法官就可能会不得不顾及诉讼上这一失衡的局面,以行使阐明权的方式加以补救,从而使司法的中立性受到质疑,这样就不能够实现在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实行对等的法律观点的交流;而法官对法律上的理解与观点就可能会简单地加强于有关当事人,因为原本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除了只能根据法官的建议提出主张和证据之外,难以存有任何主动、积极利用法律本已赋予的救济手段来推进诉讼进行的可能。在此情形下,可能原本具有显著的胜诉实力,但却将随着诉讼程序一步步的开展因不得要领而丧失殆尽,最终面临败诉的结局。
关于法官的阐明义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l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 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充分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当与当事人共同就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提出发问。审判长对于应依职权调查的事项中所存在的可疑之处,应予注意。”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 “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第一款)。陪席法官向审判长报告后,可以进行本条前款所规定的处置(第二款)。当事人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可以请求审判长进行必要的发问(第三款)。如果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在口头辩论的期日之外,依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对攻击和防御方法进行产生重大变更的处置时,应当将其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第四款)。”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设置的审前准备程序是旨在提高诉讼时效以便集中审理,对程序的进程进行控制,因此,这些国家的法官能够在诉讼的初期阶段就集中审理所要预期实现的目标,结合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攻击与防御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表达方式也主要是从行使阐明权的角度来进行的。
相较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等,其基本程序理念是建立在高度制度化的对抗辩论式的一种程序模式,即通过诉讼主张和证据对抗,并借助审前证据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各方当事人获悉有关对方所能够提供的所有的涉及争议事实的信息与资料,并且能够使审判者处于中立与超然的地位,并可能根据来自各方提供的信息和证据资料来解决争端。“美国体系中的法官通常并不揭示案件的法律理论,而仅仅回答当事人提出的争议。法官并不查明潜在的相关证据,而只是监督当事人提交证据。法官并不对证人进行主询问或交叉询问,最多,法官在律师终止盘问后提出一些补充性问题。法官通常不寻求收集额外证据的可能性。如果证据在法律上是不充分的,法官将作出不利于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裁判。”美国诉讼当中的这种对抗式程序所显示的功能主要来自于陪审团审理所形成的特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在审判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似乎不是法官而是陪审团成员,但是,这些既不懂法律又不娴熟审判技术的社会普通常人,他们在当事人的对决过程中唯一所能够有所作为的便是在诉讼的最后阶段对裁判给出结论,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很难像大陆法系那样由法官作为程序管理者, “对抗制的理论认为,为了作出公正的决定,法官必须是中立的,而法官要是中立的,就必须是消极的。”由于无法将诸如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定位于程序的管理者,因此,很难想象作为消极裁判者的英美法系法官能够具体行使诸如大陆法系法官所享有的那种阐明权。 注释:
参见陈玮直著:《民事证据法研究》,台湾新生印刷厂l970年版,第9页。
[日]谷口安平著:《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l996年版,第29页。
在美国,在小额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十分常见,但是这些小额法院的管辖权是极为有限的。
在此,陪席法官是指坐在审判长左右两边的法官。
[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录伊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l—92页。
汤维建著:《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
240331
毕玉谦 中国政法大学
一、关于阐明权的界定
在民事诉讼上由法官所享有的阐明权是由公法意义上的程序规则与民事诉讼主要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私权纷争这一矛盾交汇点的产物。民事诉讼具有保护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属性,从而使辩论主义成为一项支柱性的诉讼原则。在辩论主义架构下,为民事诉讼法所设立的用于保护当事人私权利益、确定某项权利存否及归属的法定程序,法院在裁判上所考量的范围只能限于当事人请求的范围以及为其请求所提供的诉讼资料。凡当事人未请求的利益,法院不得予以裁断,凡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或证据,法院不得予以审查确定。但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使得这种内在实体内容得以调整的程序规则则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妥当、效率等一系列价值内涵。这种公法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职权主义的体现,它有利于澄除由于极端采用辩论主义所产生的某些价值观念上的盲点,使得采用正当程序用于解决社会冲突而避免采用远古时代那种优胜劣汰的简单粗暴方式成为一种现实的抉择。从历史的发展轨迹给两大法系各国在立法、司法上所打下的烙印来看,适度的职权主义倾向有利于克服辩论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可以说,适度的职权主义有利于保障辩论主义本旨的实现。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上有各种表现形态,其中包括法官阐明权的行使。应当说,作为职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的监管权力之上,这种监管权力的行使主要体现为对民事诉讼活动的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两种形式。
笔者认为,所谓阐明权是指,为了防止极端辩论主义对诉讼的公正性所造成的损害,当遇有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声明、陈述或举证上存在不甚明了、不尽妥当、有所欠缺等情形时,由法官向当事人进行适当发问、提醒、告知其作出释明或者予以明了、补充、修正的一种权力与职责。这种权力行使的效果主要体现在,能够使有关一方当事人在遇有特定情形时获得司法上的必要救济。
在大陆法系,阐明权的形成来自这样一种理论悟识,即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围绕如何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从而引领诉讼沿着使得那些本应胜诉的人最终获得胜诉的结局,这无异于是在要求由一种理性之人在诉讼上提出妥当而完备的声明及陈述,以期获得预期的裁判结果。然而,现实当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实难达到一种理想状态,特别是由本人亲自诉讼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其提出妥当而完备的声明与陈述亦非切合实际。但是,仅仅因为当事人本人并不懂得获得胜诉的要领而丧失本应属于他的权益,将与司法正义的本旨相违背。对此,法官阐明权的行使将有助于克除辩论主义的这一弊害,从而发挥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及矫正功能。
从传统观念上而言,由于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间的强式对抗辩论主义,因此很难接受由法官采用阐明权的方式介入当事人的程序对抗之中来实施这种司法救济,但是,随着诉讼实践的不断激增、律师凭借玩弄诉讼策略作为制胜法宝的弊端日渐显现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英美法系国家原本竭力禁止法官主动介入当事人的程序对抗的态度已趋于缓解,并且还出现了引入职权主义模式、加强程序管理的迹象。
从阐明权行使的方法来看,通常是向当事人发问,故又称发问权。在德国通常称之为阐明义务或发问义务,而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被称之为阐明权。
关于阐明权的性质之认定,包括对阐明权的定性及法官如应尽而未克尽这一职守所产生法律后果的界定。阐明权的理论及学说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上源远流长,对这一权属的判定,期间时有反复,尚无统一的定论。早期在德国,有部分学说将阐明权视为训示性规定,而并非法官在职务上的义务,其效果为,即使不予行使,也不得将其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时至189o年初期的判例仍采用这一观念。但在此之后的情况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因为在此之后居于多数的学说及判例则一改前辙,进而将阐明权视为法院或法官的义务,如有违背,则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显示出职权主义的强化之势。在日本继受德国后期这一观念影响下,其大审法院所作判例始终认为,凡当事人主张的事实遇有不明了的情形时,法院应予阐明,此属法院的权利抑或一种义务,如未加以阐明而影响当事人就事实陈述不能明了,最终导致影响判决时,该判决即属违法。在日本学术界,处于非主流派的学者则持有与之相反的见解,多数学者观念与判例相一致。按照德国的判例及学说,凡违反阐明义务属于程序违法,可构成当事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相较而言,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对于违反阐明义务未有明确统一的见解,基本上是未将违反阐明义务、未尽审理职责、怠于阐明加以区别,而是混合使用。
笔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权是司法审判权在诉讼上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职责,而不宜定性为一种义务。因为,法官的这种阐明权,既是一种职务上的权力,又是一种职务上的责任。它并非是一种抛开法官职务的一种个人身份“权利”,因此,这种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也无从谈起。而“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侧重适用于处在平等诉讼主体地位的诉讼当事人之间。法官的这种特有职责可以理解为:既是一种职权,又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在实务当中,当因审理法官未能及时履行这种审判上的职责而导致一方当事人遭致不利裁判时,有关当事人可以此为理由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救济途径寻求司法救济。当上诉审法院发现有关法院法官未能及时履行这一审判职责有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时,可将案件发回重审。
二、阐明权的行使范围
所谓阐明权的行使范围,主要是指在何种情形下针对何种事项由法官行使阐明权,以便要求当事人进行相应的释明。当事人为了保障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正当性的需要,应表明提起诉讼请求的理由,这种理由通常包括事实上的陈述与法律上的陈述。由此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必要的攻击与防御态势,作为当事人言词辩论的对象。对法院而讲,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主张与另一方当事人的抗辩形成审理对象,经过言词辩论而形成裁判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如当事人主张某一特定法律效果时,应就该法律效果发生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进行陈述和证明,如果在此层面显有疏漏,法院应行使阐明权使其知晓;从法院的角度而论,当事人所声明的事实主张与诉讼请求究竟应与何种法律关系互有牵连,常有不尽明了的情形,就该不明了的情形向当事人进行发问,令其作出必要的陈述,也应属于阐明权行使的范围。
按照大陆法系的学理见解,一般认为,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主要表现于下述范围:
(一)为使不明了的事项予以明了而行使阐明权在诉讼上,如遇有当事人声明及陈述出现包括语义含混不清或者前后相互矛盾之处时,例如,原告请求被告给付房屋租金,但在其陈述事实理由当中又称持有被告的欠款凭据,请求被告清偿此笔欠款。在此项诉讼当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究竟是基于房屋租赁关系还是基于借贷关系,两者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相距甚远,裁判理由应当如何叙载,对于裁判的作出关系甚重,故此际确有行使阐明权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据此而形成审理的基础,法院进而便会作出不符合事实真相之裁判,为了使有关的事项得以明了则有必要对有关当事人进行释明。如在此情形下法官不及时行使阐明权最终将会构成有关当事人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这是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二)为了排除不适当的事项而行使阐明权
在德国,当遇有显然不存在胜诉希望的诉讼,法官可劝谕当事人撤回其诉讼请求;对于并非基于真实基础而作出的声明或陈述,法官可指令当事人就其真实性作出释明;对于无意义或带有欺诈性的声明及陈述,法官可行使阐明权将其排除。但是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种阐明权行使的效果并不具有强制性,即纵然在上述情形下不行使阐明权也不会导致违背审判职责,并且不能构成当事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而只能将其视为法院的权限所涉及的范围而已。
(三)当有必要弥补有关欠缺为使当事人补充诉讼资料时而行使阐明权
当涉及提出对不当声明或陈述要求当事人予以释明,如果处于补充诉讼资料之需所提出的声明或陈述的,法官应行使阐明权要求当事人作出释明,否则,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判例及学理均认为这已构成第三审上诉的理由。在细节上,德国与日本的判例学说似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德国的判例学说认为,在此,法官应行使发问权以便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来使有关事项得以明了,并求得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完整的构塑。但这一切必须以当事人所提出的攻击与防御方法为必要限度,法院也只能在此限度内将当事人就事实陈述所暴露的瑕疵告知并要求当事人作出必要补充,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资料出现缺陷时,应指令当事人加以补充。法院就此而作出的阐明被视为审判上的义务。按日本的判例则认为,凡当事人的陈述事实出现欠缺时,法院应指令其补充,这种做法并非违背当事人主义的原则而指令当事人另行陈述他种新的主张,而是就业已陈述的真实意旨加以释明,也就是对于其有密切相联的事项加以释明,以便为审理的进行促成一个完美的效果。
(四)为使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而行使阐明权
在大陆法系的理论学说上,就法院能否使当事人追加新的声明及新的陈述或将以前所提出的并非适当的声明及陈述变更为新的声明及新的陈述,颇有争议。即使在德国国内,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肯定者认为,法院不能仅凭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审判职责,即使当事人在诉讼上未作出何种陈述,未声明有何证据或未作出适当声明,法院也应就上述各诸事项主动予以发问,而不能直接将当事人的这些消极诉讼作为据为裁判的理由。例如,当原告基于被告对其特定物加以损坏而请求判令被告恢复原状时,如法院在经审查判断后认为该特定物已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时,应行使阐明权,提醒该原告注意,将恢复原状的请求变更为赔偿特定金额的请求。反对者认为,阐明权应仅限于辩论主义的范围之内,法院并非享有指令当事人就新的请求原因或新的抗辩事由进行陈述的权力。即使向当事人行使发问权,也应仅限于因攻击防御方法变更所牵连的事项。按照日本的判例见解认为,为了使审理获得正确的裁判结果,以便使本应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胜诉,法院应行使阐明权,指令有关当事人提出新的声明或新的主张,否则将构成第三审上诉的理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使本应胜诉者最终获得胜诉的结论”这一命题具有先验、先知以及先定后审的思想观念,从而使得法院的阐明权具有某种扩张性的锋芒,由此可以窥见到,阐明权的适用范围在这些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已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
《五)因当事人在举证上的欠缺而行使阐明权
就证据的提供而言,原则上,只有因当事人过失或误解其并无举证责任而致使出现未有举证的情形时,法院才有告知其提出证据的义务。所谓告知当事人提出证据,主要是就特定待证事实而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不提出证据时促使其注意。这种情形应仅限于按照诉讼的具体进程,当认为因当事人忽略、误解或确不掌握诉讼旨意而致使其未提出证据的情形,才有必要对其行使阐明权。假若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在经过调查之后,其结果对该当事人不利(如证据本身相互矛盾、内容并不确定、真伪无法判明等)而指令其再加提出证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能证明待证事实,而指令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的情形,则属于超出阐明权的行使范围,显为不当干预之举。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法院对于证据上阐明权的行使,应在当事人业已有何种主张或声明,而漏未提及其有何证据时才能为之。因此,法院不得在欠缺上述情形时指示当事人应为何种主张、何种主张较可获得利益、何种防御可以免除责任,或者何种证据易为法院所接受。
三、两大法系各国对阐明权的认知与功能定位
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比较来看,.尽管各国对法官行使阐明权的表现形式和涉及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于诉讼上是否需要法院从事程序管理及是否需要行使阐明权的问题, 而是存在着法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行使这种阐明权来从事程_序管理的问题。从传统上而言,英美法系国家更依赖于当事人在程序上占主导地位来开展诉讼活动,由此而引发出来诸如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实施证据突袭、节外生枝的诉讼请求与抗辩等情形,这些都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使整个诉讼过程几乎成了演练诉讼技能从而获得审判上优势的竞技场。“很长时间以来,以所谓‘竞技理论’为特征的对抗性程序有其自身的问题这一点已被广泛认识。这种程序过分依赖于当事者各自所拥用的资源。开庭审理的集中对决方式总是伴随着不意打击的危险。”这些弊端在近几十年来引发许多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开展程序改革,即借鉴大陆法系的程序管理原理,从强化法官的职权管理职能的角度来对诉讼的正当程序加以实质性的保障。与法官的程序管理职能以及行使阐明权的程度与范围具有密切关系的便是律师强制代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具有普通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进行诉讼时,必须由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两大法系各国在实行这一制度时有所不同。例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等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等实行的是这种律师强制主义,而大陆法系的日本等以及英美法系的美国等并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主义或者没有实行完全的律师强制主义。
对于美国而言,在立法上虽然没有采取律师强制主义,但是,事实上,在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人都有律师进行代理。这是因为,美国的诉讼程序除了凸显的对抗辩论模式之外,由于法律的庞杂以及诉讼程序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具有事实上很高的技术要求,以至于如不采用律师代理,将会使当事人在诉讼上感到寸步难行、无所事事。抛开英美法系的对抗辩论式诉讼模式姑且不论,即使在大陆法系更为注重法官的职权作用的情形下,往往需要法官通过行使阐明权来使包括法官在内的三方主体对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形成必要的共识或相近的认识,虽然法官在这一过程当中通过行使阐明权来发挥这种统合作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将其对法律的理解强加给各方当事人,而是意味着为了达成这种共识,法官与当事人双方之间彼此借助于程序所开展的对话与讨论来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所发挥的应有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双方都有律师代理的前提下,法官行使阐明权则具有对等或平等的基础,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此前提下都具有利用各自的法律信息资源与法官进行对等或平等交流机会,都能够即时享有利用各自的诉讼经验来提出相关动议,启用一些程序或针对对方当事人诉讼行为或法官的职务行为提出异议的空间。如果仅有~方当事人有律师代理,法官就可能会不得不顾及诉讼上这一失衡的局面,以行使阐明权的方式加以补救,从而使司法的中立性受到质疑,这样就不能够实现在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实行对等的法律观点的交流;而法官对法律上的理解与观点就可能会简单地加强于有关当事人,因为原本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除了只能根据法官的建议提出主张和证据之外,难以存有任何主动、积极利用法律本已赋予的救济手段来推进诉讼进行的可能。在此情形下,可能原本具有显著的胜诉实力,但却将随着诉讼程序一步步的开展因不得要领而丧失殆尽,最终面临败诉的结局。
关于法官的阐明义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l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 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充分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当与当事人共同就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提出发问。审判长对于应依职权调查的事项中所存在的可疑之处,应予注意。”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 “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第一款)。陪席法官向审判长报告后,可以进行本条前款所规定的处置(第二款)。当事人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可以请求审判长进行必要的发问(第三款)。如果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在口头辩论的期日之外,依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对攻击和防御方法进行产生重大变更的处置时,应当将其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第四款)。”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设置的审前准备程序是旨在提高诉讼时效以便集中审理,对程序的进程进行控制,因此,这些国家的法官能够在诉讼的初期阶段就集中审理所要预期实现的目标,结合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攻击与防御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表达方式也主要是从行使阐明权的角度来进行的。
相较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等,其基本程序理念是建立在高度制度化的对抗辩论式的一种程序模式,即通过诉讼主张和证据对抗,并借助审前证据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各方当事人获悉有关对方所能够提供的所有的涉及争议事实的信息与资料,并且能够使审判者处于中立与超然的地位,并可能根据来自各方提供的信息和证据资料来解决争端。“美国体系中的法官通常并不揭示案件的法律理论,而仅仅回答当事人提出的争议。法官并不查明潜在的相关证据,而只是监督当事人提交证据。法官并不对证人进行主询问或交叉询问,最多,法官在律师终止盘问后提出一些补充性问题。法官通常不寻求收集额外证据的可能性。如果证据在法律上是不充分的,法官将作出不利于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裁判。”美国诉讼当中的这种对抗式程序所显示的功能主要来自于陪审团审理所形成的特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在审判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似乎不是法官而是陪审团成员,但是,这些既不懂法律又不娴熟审判技术的社会普通常人,他们在当事人的对决过程中唯一所能够有所作为的便是在诉讼的最后阶段对裁判给出结论,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很难像大陆法系那样由法官作为程序管理者, “对抗制的理论认为,为了作出公正的决定,法官必须是中立的,而法官要是中立的,就必须是消极的。”由于无法将诸如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定位于程序的管理者,因此,很难想象作为消极裁判者的英美法系法官能够具体行使诸如大陆法系法官所享有的那种阐明权。 注释:
参见陈玮直著:《民事证据法研究》,台湾新生印刷厂l970年版,第9页。
[日]谷口安平著:《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l996年版,第29页。
在美国,在小额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十分常见,但是这些小额法院的管辖权是极为有限的。
在此,陪席法官是指坐在审判长左右两边的法官。
[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录伊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l—92页。
汤维建著:《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