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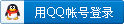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原作者:苏永钦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六. 不同民事规范的解释原则
不同的民事规范,从国家制定的法规,社会形成的习惯,到人民订立的契约,
适用于个案争议,可能都需要解释。而基于上述民事规范的多元性格,以及私法自治解放出来无可估量的澎湃活力,作为连结应然和实然的解释者,就有必要在做每一个解释的时候,像一个小小的立法者一样,针对各规范的不同功能,选择最适切的解释方法,使国家的强制和社会的活力以最有利的方式辩证统合。民法本身并未提供太多的解释规则,而民法学者尽管生产了汗牛充栋的释义教材,迄今也还欠缺一本简明文法或操作手册[59] ,故以下从规范功能切入所作的说明,或许可以当成探路的小瓦片。
具有强行规范性格的某些法令和习惯,既以行为的管制为其目的,则在解释方法上合目的性的观点很自然的会优先于其它观点,各种迂回手段可能会被定性为「脱法行为」,而排除其法效,或甚至令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但在扩大打击面以协助管制目的的落实以外,目的取向的解释常常也会导向规范适用的限缩,使国家的强制在私法自治领域要能「见好就收」,强其所当强,而又小心呵护自治机制,使其免于不必要的扭曲。民法第七一条的但书:「但其规定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就是强制规范留给私法自治的一个气窗,教科书作者常把这个但书当成民法内强制规定的引致条款,真是小觑了它的体制功能,倒是最高法院采取了类似「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的二分法,虽然始终还没有建立清晰的理论架构-这本来就是对审判机关的过度期待-,但实质上赋予但书概括条款的功能,为裁判者创造了调和管制和自治的解释空间,真是难能可贵[60] 。最高法院依强行规范的目的而限缩其适用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对旧农业发展条例第二二条,有关「耕地不得分割」这个禁止规定的解释:「农业发展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旨在防止农地细分,而禁止原物分割,用收农地使用上更大之效用。系争共有耕地,既经原审命变卖分配价金,尚不发生农地细分之情事」[61] ,就是值得一书的高明手笔。
事实上不只强行规范有管制目的,在特别民法中很多的规定性质上是强制而非强行的规范(不涉行为的强制或禁止),背后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管制目的,这时候解释者也不能不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决定适用的范围该放大或收缩到哪里。比如,基于土地政策考量,而打破了私法自治基本法理:「任何人不得为大于自己权限之处分」,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的处分,不需要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而「应以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意」,或只要「应有部分合计逾三分之二」即可,目的显然在避免土地这样的稀有资源在不利的产权结构下,无法透过交易而发挥最大的资源效益。于是少数共有人,或甚至多数的小共有人,他们受到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处分权限)就在更大的公共利益之下被限制了。但本条所谓的处分,到底该有何种内涵,实务上一直有各种争论,解释者如果能从此一规定的政策目的出发,而以私法自治的维护作为落实目的的外缘界限,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首先,处分是否应该包含抵押权的设定?从处分(Verfügung)的通常意涵(文义解释),以及从更高度的让与尚且许可而举重明轻(文理解释),固然应该肯定;但从第三十四条之一的修正经过(历史解释)[62] ,以及第一项特在处分之外列举「设定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或典权」观之(文理解释),似乎又该采否定说。这时即有必要把该条的政策目的,也就是排除不动产交易障碍,并藉以避免「妨碍都市计画之执行,影响社会经济之发展」(修正说明),纳入解释的考量而重新加以权衡。抵押权的设定涉及的是担保交易,如果排除抵押,不动产是不是会因少数共有人作梗而无法充分发挥其担保效益?这里只要想想抵押权的「价值权」本质,即其利用不受限于物的本体,与用益权因受限于物的本体而势须由共有人共管共享,正好不同,故各共有人本来就可以将其应有部分设定抵押权(释字第一四一号解释),而使共有物的担保利益充分发挥,并无闲置之虞,此时让多数共有人侵越少数人的处分权限,即属过度。至于因为抵押权必从属于一债权,若容许多数共有人就全部共有物设定抵押,将在共有人之间或与第三人间形成如何复杂的债权关系,从而增加多大的整体交易成本,就更不消说了。故当然还是以限缩处分概念的否定说为当[63] 。
其次,处分是否应该扩张到买卖、赠与、出租这一类的债权行为?实务上,内政部发布的「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执行要点」第二点就说:「本法第一项所称『处分』,包括买卖、交换、共有土地上建筑房屋及共有建物之拆除等法律上之处分与事实上之处分。但不包括赠与等无偿之之处分及共有物分割」。最高法院研究之后认为应不包含「出租」,理由是本条文特别规定,「影响于少数共有人之权益甚钜,在适用上自不宜扩大其范围,及于共有物之管理,共有物之出租」[64] ,似乎非常在意对私法自治基本原则的维护,然而为什么同样是处分概念的扩张,买卖可以,出租又不可以?学者对于赠与的排除多无异议[65] ,但又有人极力反对将出租排除[66] 。足见透过处分概念的扩张来落实土地政策,可以到什么程度;而同属支撑私法自治不可或缺的概念精确性,又可以容忍多大的混乱,都有待辩明。如果我们回到原点,肯定土地法真正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是土地利用障碍的排除,则当相关概念不待扩张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任何扩张所造成的处分权限制和概念体系的混乱,都是对私法自治的扭曲,而欠缺正当性。简言之,我国民法既已将财产权的交易在概念上切分为债权行为(原因)和物权行为(结果),则因为直接构成土地利用障碍的就只有物权行为部分,也就是特殊所有权结构(共有)所形成的处分困难,合理的政策干预当然就应该只到此处为止,原因部分涉及的复杂关系,既不适合由国家以某种简单的规范越俎代庖的强行介入,还不如听由私法自治原有的机制去处理。因此,不论买卖、互易、出租或赠与,应该都不是此处所谓的处分,共有人基于何种原因作成共有物的处分,根本不在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的射程范围。
这里其实已触及我国民法一个不容轻易动摇的原则,也就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二分。债权行为如果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负担行为,也就是对行为人发生创设法律负担的效力,而不直接对自己或他人财产权发生任何处分的效力,则所谓出卖或出租他人之物、一物两卖等等,都只是创设了出卖人、出租人自己的给付义务,试问法律秩序有何理由否定其效力-不论从宪法人权保障,或社会善良风俗维护的角度?出卖人或出租人嗣后能不能履行其债务,或只能选择履行其一,要他自己去「摆平」即可,何劳国家操心?自由市场本来就充满风险,风险也就是商机,国家可以协助建立排除风险的制度,但是最好不要尝试对人民自甘风险的行为轻率介入。以共有不动产来说,部分共有人可能自行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契约而发生效力,本来就不待其它共有人的同意,只是履行契约所必要的物权行为(移转所有权),如果没有得到其它共有人的同意,依民法第八一九条第二项即属无权处分而不生效力而已。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既排除了这部分的障碍,产权的移转即没有任何困难。惟土地法排除的只是处分权障碍,并未提供所有权移转和价金取得的「原因」,故不仅买卖双方需要有效的买卖契约,其它共有人因此一交易所受到的损害也需要法律的原因,否则就有不当得利的问题。在多数共有人出卖共有物的情形,所得价金就其它共有人的应有部分而言即属不当得利,其它共有人自得向得利人请求返还。如果不是买卖而是赠与,或价金远低于市价(部分赠与),也可以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买受人请求返还(第一八三条)。处分共有物的多数共有人若是以全体共有人名义订立买卖契约,而以多数共有人名义处分共有物,则买卖契约有无权代理问题,少数共有人可以承认买卖而向多数共有人请求分配价金,也可以不承认而使买卖确定不生效力,再依不当得利向买受人请求返还不动产所有权。足见民法现有规定已可合理处理共有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把处分概念扩张到买卖,只是画蛇添足而已[67] 。
出租的问题略有不同。部分共有人固可有效出租共有物,无待其它共有人的同意,但履行租赁契约必须交付共有物供承租人使用,并定期收取租金,这就涉及共有物管理的问题,依民法第八二~条第一项,一般的管理行为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租赁是一种重要的不动产交易,而且基地租赁依民法第四二二条之一(即土地法第一~二条)还可能转换为地上权,如果处分概念不及于此,确实可能对不动产的租赁交易构成妨碍。不过此时精确而言,已不是从物权行为扩张到债权行为(租赁)的问题,而是从法律处分扩张到事实处分(管理)的问题,法院不能不考量民法第八二~条对一般管理行为和特殊管理行为(保存、改良)在权限分配上的三分决定,由于改良行为也只需要多数共有人的同意(第八二~条第三项),就方法论而言,此时与其从特别法上明显较遥远的「处分」概念切入去做目的性扩张,实不如从普通法上的「管理」概念去做解释,出租共有不动产即使不能解释为一种改良行为,也可以「类推」适用改良行为,同样可以达到活络不动产租赁的政策目的。物权编修正草案已将共有物管理的权限,一律改为以多数决为原则,仅保存行为得由共有人单独为之,若立法院照此通过,不动产的出租管理依民法即可采多数决,将更无扩张土地法第三四条之一中处分概念的必要。
总结上述土地法第三四条之一的争议可知,具有政策目的的强制规范(含强行规范),目的解释通常是最重要的方法,必要时得为一定的超法规(extra legem)扩张,但在尊重私法自治的前提下,更多的时候,需要对法条做目的性的限缩。不过民法中的任意规范和绝大部分的强制规范,只是单纯为支撑私法自治的运作而设,不具有任何公共政策的目的。其解释在方法上就可能更强调体系的观点,以维系自治机制的顺畅及价值权衡的一致为其主要考量,故解释者关切意思自由、交易安全、交易便捷,乃至交易成本的降低[68] ,并尽量维持一致的评价,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子可说不胜枚举。这里只再谈一个在解释上可能遭遇的难题,就是当需要解释的规范,是否具有公共政策的目的,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应该采何种解释方法?
我们可以举动产担保交易法为例,附条件买卖其实就是以保留所有权方式(物权行为附条件)作成的担保交易,此时由于法律规定了可供担保的动产类别(第四条),特别的生效(书面)对抗(登记)要件(第五条),并规定了契约记载事项(第十六、二七、三三条),与担保利益保全、实现的程序(第十七至二三条),如果当事人不依此规定作成担保交易,比如就动担法未规定的动产,或以口头而非书面方式,作成附停止条件的物权移转合意,或以移转所有权为债权担保的约定,是否仍应承认其效力?解释的关键,就在动担法有关三种担保交易所设的强制规定,是否具有经济政策的目的,如藉动产种类与担保方式的控制,来调节市场景气(景气不足则开放,过热则限缩);或藉登记来供金融管理机关掌握担保交易资料。从第四条第二项刻意保留行政院对动产品名「视事实需要及交易性质以命令定之」的调控权看来,此说当非毫无依据,但就金融与经济实务而言,动产担保作为一种管制工具的功能实在相当有限,若一定要朝此方向解释而排除基于自治所创设的各种担保交易的效力,如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或融资性租赁,对私法自治的机制无疑将造成甚大的斲伤,因此在动担法未如荷兰一九九二年的新民法那样,明文以新制(以公证方式设定非占有质)废除旧制(让与担保)的情形下[69] ,解释上应以该法有关三种担保交易的强制规定,并无排除基于自治作成其它担保交易的政策目的,惟有关动产担保的约定若不符合动担法的规定,当事人自不得依动担法主张其权利,而只能依其约定及民法一般规定主张其权利。此外,在本次民法修正,明定不动产交易的负担行为应作成公证(第一六六条之一)以后,对于未经公证的买卖或赠与约定,是否仍应肯定可发生预约的效力,学者间也有不同看法[70] 。解释的关键,也在是否赋予此一强制规定一定的政策目的,如迅速建立一有效能的民间公证制度,如果肯定,则自应一并排除预约的效力。但若从该条第二项得以完成物权行为补正债权行为欠缺生效要件的瑕疵,而认为公证规定目的仅在减少交易纠纷,仍属单纯自治规范而无其它公共政策的目的,则似乎又没有必要从合目的性观点认定未经公证的买卖或赠与预约,也不发生效力。至于在个案中,当事人间究竟作成的是买卖本约的合意,从而因未公证而不生效力,或仅是买卖预约的合意,或可探求真意而从本约转换为预约,发生预约效力[71] ,尚应就实际情形加以认定,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宁采后说。
总之,本文认为,基于对私法自治的尊重,在强制性质的民事规范是否具有特殊公共政策目的不甚明确的时候,即应朝单纯自治规范的方向去解释,法官应避免假设有特殊公共政策目的的存在,或对合目的性作扩大解释,而斲伤了自治机制,换言之,就是「有疑义,从自治」。类此的思考还可用来处理强制规范和任意规范的灰色地带,各种之债的规定中,常常会出现当事人可否排除的争议,此时除非有坚强依据,可认定立法者基于强化自治机制或衡平考量而有强制的意思,如有关解释规则(第四八三条、第五三~条、第七~九条之三第三项等)、期间上下限(第三八~条、第四四九条第一项、第五~一条、第七五六条之三第一项等)、效力(第三六六条、第五~一条之一、第六~九条、第六五九条等)或法定物权或物权关系(第四四五条、第五一三条第一项、第六四七条第一项、第六六八条等)等的规定,甚至基于社会政策而具有一定「强行性」的规定(如第四五七条第二项),原则上应朝任意规范的方向解释,并不限于法条明定「除契约另有订定」的情形,也就是「有疑义,从任意」,最高法院在解释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的规范性质时,一贯强调其为「为补充当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设」[72] ,当事人当然得以特约排除;就第四二七条:「就租赁物应纳之一切税捐,由出租人负担」是否强制规定的争议,也作成本条「非强制规定,当事人不妨为相反之约定」的判例[73] ,大体都能掌握此一立场
最后,对于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民事规范-契约,该如何解释?以其在实务上的重要性而言,我国法学迄今付出的注意实在是相当的不足。我国民法也未如法国、意大利民法,以专节(法国民法第一一五六条至一一六四条;意大利民法第一三六二条至第一三七一条)来规范契约的解释,而是参考了德国民法,针对各种之债个别作了若干零散的规定,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和德国一样(德国民法第一三三条),在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做了一个非常原则性的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第九八条),法国民法和意大利民法提出的第一个解释原则,皆与此雷同(法国民法第一一五六条,意大利民法第一三六二条)。这已充分说明了契约解释在方法上的特色,也就是绝对的主观取向,甚至可以不拘泥于文义。换言之,解释者放在心里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当事人「要什么」,而不是此一契约类型的本质「是什么」,私法自治的落实,便在此一关键[74] 。契约不只需要狭义的解释,还经常需要「补充」,这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学说上就很有争议了,德国学者多强调「假设的当事人意思」(das hypothetische Parteiwillen),虽然当事人通常正好就是未虑及此,从而所谓假设,实际上可能就是照相关法律去解释而已[75] 。然而无论如何,这又再一次说明,民事规范的解释活动,是如何的因规范性质与功能不同,而应该有所不同。
七. 本土化与社会化的新挑战
如果不太吹毛求疵的话,民法的移植,整体而言应该可以得到相当高的评价。
很自然的,就像西欧在完成罗马法移植之后,台湾的民法学者也开始尝试跳脱比较法的思考,从本土化、社会化的角度对民法的现状提出批判,立法者尽管仍大量援用欧陆和日本的民法来合理化财产法的修正,但从若干技术改良以外的创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本土化和社会化的挑战,绝非视而不见。然而沿着法律必须在社会的土壤里生根成长,这样的自明之理再往下思考,我们还是会碰到规范功能的问题。民法的响应如果不是建立于功能的正确认知,则本土化、社会化的热情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修正,也许我们会为立法者迄今的响应还只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应景」层次,感到庆幸。
如果正确理解民法的自治法、技术法和裁判法本质,如本文所论述,就知道民法面对的本土化课题,完全不同于经济法或社会法,乃至宪法那样的政治法。当学者严厉批评,把德国特有的、深具日耳曼法色彩的物权行为移植到东亚社会,注定会水土不服时,他可能忽略了这里涉及的,其实只是一个单纯的分析工具,一个裁判者内部操作的技术问题。物权行为把法律行为推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度,使它更能涵摄社会上多样而复杂多变的交易,而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争议时,提供更精致的正义,这里需要的「本土化」,只到专家间的技术移转为止,还不必到使用者的层次,交易者不需要知道或「认同」这些技术的细节,一点也不会影响交易的作成。就像动物学家需要一套更精密的语言,一些「学名」,作为彼此沟通、辩难的工具,对于到动物园里观赏动物的游客,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要确定的,是把生活中的一笔交易切分成法律上的三个行为(一个债权行为和两个物权行为),是否较能公平的处理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争议,如果肯定,它就是符合我们需要的民事规范[76] 。绝大部分的民法规定不以影响人民的行为为目的,已如前述,既不要「使由之」,又何需「使知之」?因此真正需要本土化的,是强制规定背后的价值观,和任意规定所反映的交易类型,这些才是决定法院最后产出的裁判,能否为人民接受的关键。而不是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体系,我们不可能重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民法概念体系,不管你称之为中华法系或台湾法系;即使做得到,那也是毫无意义的锁国政策。
民事规范牵涉到的价值决定,如交易安全与意思自由间(无权代理)或与财产权间(善意取得)的权衡,意思自由与利益衡平间的权衡(无因管理),创新与守成间的权衡(动产加工),未成年保护与交易安全间的权衡(成年制度),亲情与公共利益间的权衡(死亡宣告)等等,是可以也应该因社会而异的。我国民法从一个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立法者有时一开始就审慎的做了不同的价值决定,比如在法律行为的基本设计上比德国更偏向交易安全的维护;有的则是实施后才作调整,比如死亡宣告制度增加检察官的声请权。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有的制度在我国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比如人格权保护,因为欠缺尊重人格权的文化而没有太大的发展,背俗侵权则因为前缺「第六伦」的伦理观,而只在狭隘的五伦范畴发挥了有限的社会控制功能。我们也很难体会根植于日耳曼社会的那种对占有的重视,使得所谓所有人与占有人关系的制度(第九五二条至第九五九条),几乎完全未被利用。另外一个受到价值观影响的显著例子,就是区分所有权,当区分所有的客观需要随着都市化早已发生,而国家还来不及教育人民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所有权观念时,公寓大厦已经大量出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立法者,立刻发现源于欧陆的区分所有权观念极不容易本土化,台北市四万个公寓大厦单位,实际顺从该法「强制」而实施自治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这些例子说明,本土化的重点,不在勉强让技术性的语言及规范通俗化到一般人民可以了解的程度,而是尽量缩短规范与民众在价值判断上的差距,尽量贴近人民素朴的法感。而当民法的强制规范大致符合人民普遍的价值观或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只剩下专业间的技术移转问题,换言之,此时立法者应努力的,是使技术规范和语言更为逻辑、精确而具高度可操作性,不是刻意牺牲精确来成就表面的「本土化」。
任意规范的主要功能既在辅助自治,减省交易成本,补强合意的不足,则立法者越能掌握各种交易的典型,上述功能就越可发挥,已见前述。这应该是当前民法本土化的另外一个重点,从这个角度看本次修法,增设三种有名契约和五种次类型的努力,就相当值得肯定。有名契约的规定如果不能抓住交易社会的脉动,其结果就是被民间造法取而代之,拥有法律知识和经验的大企业将处于结构性的优势,本次修法把定型化契约纳入规范,固然可以降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欠缺有名契约指导的情形下,对于许多新兴交易,如补习、顾问、融资性租赁、应收帐款转让等,如何期待法院以第二四七条之一那样抽象的规范作成裁判,而仍有高度的可预见性?足见这部分的本土化,应该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
不过和本土化的诉求比起来,社会化恐怕是一个更难抗拒,也更具危险性的挑战。如果我们同意,绝大部分民法典的条文,至少财产法的部分,是无意管制人民私法行为的,它的本质只是一部裁判法,一套帮助法官做出合理裁判的法典,则我们等于承认,民法完全不具有社会改革的功能。然而吊诡的是,正因为民事财产法不去直接碰撞社会的痛处,像当初面对三从四德、宗祧继承的旧中国,民事身分法所扮演的角色那样,它才会比身分法更快速的进入我们这个和罗马法完全没有任何渊源的社会,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助力[77] 。不用强行,甚至不太强制,民事财产法像春阳一样,剥掉了台湾社会传统封建的外衣。也许要花上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必将看到同样的过程在中国大陆重演,在不幸的内外战争和乌托邦式的改革,浪费了整整七十年之后。从这个角度看,民法促成的又何尝只是改革,毋宁更近于一场宁静的革命,或者,一个「和平演变」的大阳谋。
微观和巨视也足以让我们看穿民法保守和改革的两面性和摆荡性。民法无视于阶级间的剥削,所得分配的恶化,也不管企业的精明和消费者的无知,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蒙住双目的女神,把现实的种种不平等,都放在同一个抽象的天平上,这是它保守的一面。但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民法也让各种改革的十字军自由进入自治的领域,使承租人可以主张土地法上的先买权,买受人可以主张消保法上的无过失责任,这又是它进步的一面。当改革者以「市场失灵」为理由进场干预时,民法的规定自动退让;等改革者承认「政府失灵」而解除管制时,民法又当仁不让成为自由市场的中流砥柱。因此尽管外观如一,民法的精神风貌其实是随着每个时代改革热情的起伏而迥然不同。对于这样的特质,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满意。德国就一直有学者从提升人民法律认知的角度,主张民法典应该像一部真正的法典一样,把散布于外,越来越芜杂的特别民法都搜集进来,重新整编,让人民可以一次看清楚他的权利和行为界限。主张以「内设」模式替代「外接」模式的学者,还强调体制中立、意识形态中立的虚矫,一九四二年的意大利民法,不就把土地法、建筑法的规定全部内接于相邻关系,劳动法置于债编之后独立成编,公司、合作社、保险、智能财产权等等,也都回归民法,造就一个全新的民法典范?然而这些批评者大概也很难否认,法典的理想永远和事实有段距离,即使条文数多达两千九百六十九条的意大利民法典,也像它的历史标竿-罗马法大全一样,很快就必须面临单行法在法典之外自立门户的残酷事实[78] 。内设各种特别法只是使得习法者对民法的原理原则更难掌握而已。
内设或外接,各有所长,偏偏民法这次修正,采取的是「局部内接」策略。土地法中的民事规定大举转进民法典,包括土地法第一~二、一~四、一~七、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九、一二~等,乃至土地法施行法、平均地权条例、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的零星规定。在另一个社会「敏感」领域-雇用契约,立法者虽未直接把劳工法规定移植进来,但依其精神,增订了雇用人保护义务(第四八三条之一)和对受雇人的无过失赔偿责任(第四八七条之一),强化了雇用关系的「社会性」,而减低了民事契约的「对等性」。不过最具有社会改革色彩的,应该还是在侵权行为增设的商品制造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一)、动力车辆驾驶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二)及危险制造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三),尽管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特别侵权责任都还延续动物占有人与工作物所有人的责任,采举证责任倒置类型,不能算是过于极端的改革,但以商品、车辆、危险所涵盖的社会活动之广,说我国民法所采的过失责任原则已经近于颠覆,恐怕也不为过。
然而民法推动的大部分改革,其实都还只是呼应民法外的社会改革,立法者显然又没有重新整编,把民法典变成「真正」民事法典的鸿图,只是择其一二纳编,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社会化,既不能使民事裁判者从此一本民法典走天下,反而使它的原始「市民法」图像变得完全模糊。尤其令人玩味的是,新修的商品制造人责任和定型化契约效力规定(第二四七条之一),和消费者保护法几乎是同时进行而先后完成,民法一方面表现「改革不落人后」的气概,另一方面又在用语上刻意的去除「社会角色」的痕迹,如避用「消费者」或「企业经营者」,以维持其「普通法」的风格。整个修正给人的观感,就是立法者的举棋不定,放不下法典的华丽风韵,又怕跟不上改革的时代脚步。我们现在也许很难评估,内设和外接何者才是最佳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说,本次修法所采的局部内设策略,并不能许给民法什么美好的未来。
结语
从人类历史的长流来看﹐社会生活的法律化是从民法开始,如果不把彰显国家刑罚权的刑法算进去的话,国家公权力被用法律「驯化」,已是相当晚近的事。优秀的罗马法律人两千多年前就在民法领域推敲各种公平正义的规则,而发展出十分精致的概念体系;中西欧各国继受罗马法,才能先后制定了技术上更臻成熟的民法典,和刚刚萌芽的公法不可同日而语。长期和未法律化的公权力关系并存,民法的教义学可以说自始就没有纳入公法的考量,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公法的发展一日千里,民法和公法的互动与冲突,才渐渐成为法学的重要课题。存在于民法内部的国家强制,和外部的国家强制,因为后者的法律化,而逐渐汇流。检察官介入民事生活,民法变成公共政策的工具,乃至在民事单行法法中加入若干行政制裁,都好象见怪不怪。
至于我国的发展,因属整套欧陆法制的移植,公私法本来应该没有先后,但民主政治条件不足,使得公权力阴影下的公法未受到重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法律人也和古罗马人一样集中耕耘民刑法领域,一直到民国七十年代,公权力关系的法律化才逐渐落实,整个发展过程,如同欧陆国家的缩影。但民法和公法的接壤问题,迄今仍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形下,功能法的研究角度,也就是去区分国家强制在公私法领域的不同性质,对国家强制和人民自治如何配合、互动加以类型化,再据以为民事立法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功能,做更清楚的定位,应该会有助于法律体系整体的顺畅运作,使公私法走向有机的结合。本文提出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观念,如果能在问题意识或研究方法上,促成那么一点微末的提升,也就达到目的了。
(全文结束)
*现经作者苏永钦先生特许登载在中国民商法网站,以飨读者!
注释:
[59]王泽鉴大法官去年出版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建立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无疑应列为法律系学生研究民法的必读书。
[60]前注10
[61] 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五四三号判例
[62]参阅立法院第一届第五十五会期第四十次会议审查「土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会议纪录,立法院公报第六十四卷第五十六期,院会纪录,页22, 民国六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二读会时多数意见认为不宜概括规定「设定负担」而采列举方式,刻意排除设定抵押权,以免「严重影响他共有人之权益」
[63]持肯定说的学者见解详参吴光陆,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之商榷,法学丛刊,第一三六期(民国七十八年),页49; 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民国六十五年,页366
[64]最高法院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民事庭会议决议
[65]如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民国八十一年修订版,页396-97, 注16
[66]如谢哲胜,共有土地的出租与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的适用,收于财产法专题研究,民国八十四年,页145-156
[67]多数共有人出卖共有物本来就不发生效力问题,已如说明。如果扩张到买卖,可以解释成该少数共有人未参加的买卖效力及于其身,而可成为财产损失的「原因」,则本条将成为多数共有人(或少数大共有人)诈害少数共有人(或多数小共有人)的合法管道,不公孰甚!
[68] 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的观点,作为新兴的解释方法,它无疑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过就此处所区隔的政策性强制规范与单纯自治规范而言,在经济分析上刚好也可能分别运用不同的理论,后者最适用的就是以厂商或消费者行为为中心的个体分析,前者则可能还有运用某些总体理论的余地,这个看法是从法律经济学者熊秉元在今年五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举办的「法与经济分析」研讨会中发言得到的启发,不敢掠美,特加说明。
[69]荷兰新民法第3:84条第3项明文禁止让与担保;另参B. Wessels的引介, 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 System, Contents and Future, 41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78(1994)
[70]在民法研究会在去年的第十五、十六两次学术研讨会中,针对黄立与陈自强所提论文,学者间对于未经公证的不动产买卖或赠与约定可否发生预约的效力,颇有不同看法
[71]至于我国民法未对预约作一般性规定,不动产交易的预约是否和本约一样要经公证,也还有待深论,德国学者认为此处属于隐藏性漏洞,应透过解释加以补充,可参Larenz/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A., 1995, 198f.; 就我国而言,不仅不动产公证制度刚刚萌芽,功能有待考验,且预约效力毕竟不同于本约(前注49),应无Larenz/Canaris顾虑的脱法问题,是否适宜「类推适用」,本文暂持保留看法
[72]如二十九年上字第八二六号、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三二二八号判例
[73]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一一九号判例
[74]不知道是否有意,大陆民法通则就没有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学者解释虽也强调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但显然较偏向文义与客观的目的,如梁彗星,合同的解释规则,收于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二册,一九九九年,页255-268; 新通过的合同法第一二五条规定合同的解释方法同此
[75]Flume, 前注21, S.321ff.
[76]参阅拙文,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收于「跨越自治与管制」,民国八十八年,页219-259
[77]拙文,韦伯理论在儒家社会的适用-谈台湾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收于「经济法的挑战」,民国八十三年,页59-81
[78]参阅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前言中提到一九七八年通过的第三九二号法律规定有关城市不动产租赁,一九八二年第二~三号法律规定乡村土地租赁,都未直接在法典内规定 出处:本文原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
240331
原作者:苏永钦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六. 不同民事规范的解释原则
不同的民事规范,从国家制定的法规,社会形成的习惯,到人民订立的契约,
适用于个案争议,可能都需要解释。而基于上述民事规范的多元性格,以及私法自治解放出来无可估量的澎湃活力,作为连结应然和实然的解释者,就有必要在做每一个解释的时候,像一个小小的立法者一样,针对各规范的不同功能,选择最适切的解释方法,使国家的强制和社会的活力以最有利的方式辩证统合。民法本身并未提供太多的解释规则,而民法学者尽管生产了汗牛充栋的释义教材,迄今也还欠缺一本简明文法或操作手册[59] ,故以下从规范功能切入所作的说明,或许可以当成探路的小瓦片。
具有强行规范性格的某些法令和习惯,既以行为的管制为其目的,则在解释方法上合目的性的观点很自然的会优先于其它观点,各种迂回手段可能会被定性为「脱法行为」,而排除其法效,或甚至令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但在扩大打击面以协助管制目的的落实以外,目的取向的解释常常也会导向规范适用的限缩,使国家的强制在私法自治领域要能「见好就收」,强其所当强,而又小心呵护自治机制,使其免于不必要的扭曲。民法第七一条的但书:「但其规定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就是强制规范留给私法自治的一个气窗,教科书作者常把这个但书当成民法内强制规定的引致条款,真是小觑了它的体制功能,倒是最高法院采取了类似「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的二分法,虽然始终还没有建立清晰的理论架构-这本来就是对审判机关的过度期待-,但实质上赋予但书概括条款的功能,为裁判者创造了调和管制和自治的解释空间,真是难能可贵[60] 。最高法院依强行规范的目的而限缩其适用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对旧农业发展条例第二二条,有关「耕地不得分割」这个禁止规定的解释:「农业发展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旨在防止农地细分,而禁止原物分割,用收农地使用上更大之效用。系争共有耕地,既经原审命变卖分配价金,尚不发生农地细分之情事」[61] ,就是值得一书的高明手笔。
事实上不只强行规范有管制目的,在特别民法中很多的规定性质上是强制而非强行的规范(不涉行为的强制或禁止),背后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管制目的,这时候解释者也不能不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决定适用的范围该放大或收缩到哪里。比如,基于土地政策考量,而打破了私法自治基本法理:「任何人不得为大于自己权限之处分」,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共有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的处分,不需要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而「应以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意」,或只要「应有部分合计逾三分之二」即可,目的显然在避免土地这样的稀有资源在不利的产权结构下,无法透过交易而发挥最大的资源效益。于是少数共有人,或甚至多数的小共有人,他们受到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处分权限)就在更大的公共利益之下被限制了。但本条所谓的处分,到底该有何种内涵,实务上一直有各种争论,解释者如果能从此一规定的政策目的出发,而以私法自治的维护作为落实目的的外缘界限,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首先,处分是否应该包含抵押权的设定?从处分(Verfügung)的通常意涵(文义解释),以及从更高度的让与尚且许可而举重明轻(文理解释),固然应该肯定;但从第三十四条之一的修正经过(历史解释)[62] ,以及第一项特在处分之外列举「设定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或典权」观之(文理解释),似乎又该采否定说。这时即有必要把该条的政策目的,也就是排除不动产交易障碍,并藉以避免「妨碍都市计画之执行,影响社会经济之发展」(修正说明),纳入解释的考量而重新加以权衡。抵押权的设定涉及的是担保交易,如果排除抵押,不动产是不是会因少数共有人作梗而无法充分发挥其担保效益?这里只要想想抵押权的「价值权」本质,即其利用不受限于物的本体,与用益权因受限于物的本体而势须由共有人共管共享,正好不同,故各共有人本来就可以将其应有部分设定抵押权(释字第一四一号解释),而使共有物的担保利益充分发挥,并无闲置之虞,此时让多数共有人侵越少数人的处分权限,即属过度。至于因为抵押权必从属于一债权,若容许多数共有人就全部共有物设定抵押,将在共有人之间或与第三人间形成如何复杂的债权关系,从而增加多大的整体交易成本,就更不消说了。故当然还是以限缩处分概念的否定说为当[63] 。
其次,处分是否应该扩张到买卖、赠与、出租这一类的债权行为?实务上,内政部发布的「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执行要点」第二点就说:「本法第一项所称『处分』,包括买卖、交换、共有土地上建筑房屋及共有建物之拆除等法律上之处分与事实上之处分。但不包括赠与等无偿之之处分及共有物分割」。最高法院研究之后认为应不包含「出租」,理由是本条文特别规定,「影响于少数共有人之权益甚钜,在适用上自不宜扩大其范围,及于共有物之管理,共有物之出租」[64] ,似乎非常在意对私法自治基本原则的维护,然而为什么同样是处分概念的扩张,买卖可以,出租又不可以?学者对于赠与的排除多无异议[65] ,但又有人极力反对将出租排除[66] 。足见透过处分概念的扩张来落实土地政策,可以到什么程度;而同属支撑私法自治不可或缺的概念精确性,又可以容忍多大的混乱,都有待辩明。如果我们回到原点,肯定土地法真正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是土地利用障碍的排除,则当相关概念不待扩张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任何扩张所造成的处分权限制和概念体系的混乱,都是对私法自治的扭曲,而欠缺正当性。简言之,我国民法既已将财产权的交易在概念上切分为债权行为(原因)和物权行为(结果),则因为直接构成土地利用障碍的就只有物权行为部分,也就是特殊所有权结构(共有)所形成的处分困难,合理的政策干预当然就应该只到此处为止,原因部分涉及的复杂关系,既不适合由国家以某种简单的规范越俎代庖的强行介入,还不如听由私法自治原有的机制去处理。因此,不论买卖、互易、出租或赠与,应该都不是此处所谓的处分,共有人基于何种原因作成共有物的处分,根本不在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的射程范围。
这里其实已触及我国民法一个不容轻易动摇的原则,也就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二分。债权行为如果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负担行为,也就是对行为人发生创设法律负担的效力,而不直接对自己或他人财产权发生任何处分的效力,则所谓出卖或出租他人之物、一物两卖等等,都只是创设了出卖人、出租人自己的给付义务,试问法律秩序有何理由否定其效力-不论从宪法人权保障,或社会善良风俗维护的角度?出卖人或出租人嗣后能不能履行其债务,或只能选择履行其一,要他自己去「摆平」即可,何劳国家操心?自由市场本来就充满风险,风险也就是商机,国家可以协助建立排除风险的制度,但是最好不要尝试对人民自甘风险的行为轻率介入。以共有不动产来说,部分共有人可能自行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契约而发生效力,本来就不待其它共有人的同意,只是履行契约所必要的物权行为(移转所有权),如果没有得到其它共有人的同意,依民法第八一九条第二项即属无权处分而不生效力而已。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既排除了这部分的障碍,产权的移转即没有任何困难。惟土地法排除的只是处分权障碍,并未提供所有权移转和价金取得的「原因」,故不仅买卖双方需要有效的买卖契约,其它共有人因此一交易所受到的损害也需要法律的原因,否则就有不当得利的问题。在多数共有人出卖共有物的情形,所得价金就其它共有人的应有部分而言即属不当得利,其它共有人自得向得利人请求返还。如果不是买卖而是赠与,或价金远低于市价(部分赠与),也可以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买受人请求返还(第一八三条)。处分共有物的多数共有人若是以全体共有人名义订立买卖契约,而以多数共有人名义处分共有物,则买卖契约有无权代理问题,少数共有人可以承认买卖而向多数共有人请求分配价金,也可以不承认而使买卖确定不生效力,再依不当得利向买受人请求返还不动产所有权。足见民法现有规定已可合理处理共有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把处分概念扩张到买卖,只是画蛇添足而已[67] 。
出租的问题略有不同。部分共有人固可有效出租共有物,无待其它共有人的同意,但履行租赁契约必须交付共有物供承租人使用,并定期收取租金,这就涉及共有物管理的问题,依民法第八二~条第一项,一般的管理行为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租赁是一种重要的不动产交易,而且基地租赁依民法第四二二条之一(即土地法第一~二条)还可能转换为地上权,如果处分概念不及于此,确实可能对不动产的租赁交易构成妨碍。不过此时精确而言,已不是从物权行为扩张到债权行为(租赁)的问题,而是从法律处分扩张到事实处分(管理)的问题,法院不能不考量民法第八二~条对一般管理行为和特殊管理行为(保存、改良)在权限分配上的三分决定,由于改良行为也只需要多数共有人的同意(第八二~条第三项),就方法论而言,此时与其从特别法上明显较遥远的「处分」概念切入去做目的性扩张,实不如从普通法上的「管理」概念去做解释,出租共有不动产即使不能解释为一种改良行为,也可以「类推」适用改良行为,同样可以达到活络不动产租赁的政策目的。物权编修正草案已将共有物管理的权限,一律改为以多数决为原则,仅保存行为得由共有人单独为之,若立法院照此通过,不动产的出租管理依民法即可采多数决,将更无扩张土地法第三四条之一中处分概念的必要。
总结上述土地法第三四条之一的争议可知,具有政策目的的强制规范(含强行规范),目的解释通常是最重要的方法,必要时得为一定的超法规(extra legem)扩张,但在尊重私法自治的前提下,更多的时候,需要对法条做目的性的限缩。不过民法中的任意规范和绝大部分的强制规范,只是单纯为支撑私法自治的运作而设,不具有任何公共政策的目的。其解释在方法上就可能更强调体系的观点,以维系自治机制的顺畅及价值权衡的一致为其主要考量,故解释者关切意思自由、交易安全、交易便捷,乃至交易成本的降低[68] ,并尽量维持一致的评价,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子可说不胜枚举。这里只再谈一个在解释上可能遭遇的难题,就是当需要解释的规范,是否具有公共政策的目的,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应该采何种解释方法?
我们可以举动产担保交易法为例,附条件买卖其实就是以保留所有权方式(物权行为附条件)作成的担保交易,此时由于法律规定了可供担保的动产类别(第四条),特别的生效(书面)对抗(登记)要件(第五条),并规定了契约记载事项(第十六、二七、三三条),与担保利益保全、实现的程序(第十七至二三条),如果当事人不依此规定作成担保交易,比如就动担法未规定的动产,或以口头而非书面方式,作成附停止条件的物权移转合意,或以移转所有权为债权担保的约定,是否仍应承认其效力?解释的关键,就在动担法有关三种担保交易所设的强制规定,是否具有经济政策的目的,如藉动产种类与担保方式的控制,来调节市场景气(景气不足则开放,过热则限缩);或藉登记来供金融管理机关掌握担保交易资料。从第四条第二项刻意保留行政院对动产品名「视事实需要及交易性质以命令定之」的调控权看来,此说当非毫无依据,但就金融与经济实务而言,动产担保作为一种管制工具的功能实在相当有限,若一定要朝此方向解释而排除基于自治所创设的各种担保交易的效力,如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或融资性租赁,对私法自治的机制无疑将造成甚大的斲伤,因此在动担法未如荷兰一九九二年的新民法那样,明文以新制(以公证方式设定非占有质)废除旧制(让与担保)的情形下[69] ,解释上应以该法有关三种担保交易的强制规定,并无排除基于自治作成其它担保交易的政策目的,惟有关动产担保的约定若不符合动担法的规定,当事人自不得依动担法主张其权利,而只能依其约定及民法一般规定主张其权利。此外,在本次民法修正,明定不动产交易的负担行为应作成公证(第一六六条之一)以后,对于未经公证的买卖或赠与约定,是否仍应肯定可发生预约的效力,学者间也有不同看法[70] 。解释的关键,也在是否赋予此一强制规定一定的政策目的,如迅速建立一有效能的民间公证制度,如果肯定,则自应一并排除预约的效力。但若从该条第二项得以完成物权行为补正债权行为欠缺生效要件的瑕疵,而认为公证规定目的仅在减少交易纠纷,仍属单纯自治规范而无其它公共政策的目的,则似乎又没有必要从合目的性观点认定未经公证的买卖或赠与预约,也不发生效力。至于在个案中,当事人间究竟作成的是买卖本约的合意,从而因未公证而不生效力,或仅是买卖预约的合意,或可探求真意而从本约转换为预约,发生预约效力[71] ,尚应就实际情形加以认定,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宁采后说。
总之,本文认为,基于对私法自治的尊重,在强制性质的民事规范是否具有特殊公共政策目的不甚明确的时候,即应朝单纯自治规范的方向去解释,法官应避免假设有特殊公共政策目的的存在,或对合目的性作扩大解释,而斲伤了自治机制,换言之,就是「有疑义,从自治」。类此的思考还可用来处理强制规范和任意规范的灰色地带,各种之债的规定中,常常会出现当事人可否排除的争议,此时除非有坚强依据,可认定立法者基于强化自治机制或衡平考量而有强制的意思,如有关解释规则(第四八三条、第五三~条、第七~九条之三第三项等)、期间上下限(第三八~条、第四四九条第一项、第五~一条、第七五六条之三第一项等)、效力(第三六六条、第五~一条之一、第六~九条、第六五九条等)或法定物权或物权关系(第四四五条、第五一三条第一项、第六四七条第一项、第六六八条等)等的规定,甚至基于社会政策而具有一定「强行性」的规定(如第四五七条第二项),原则上应朝任意规范的方向解释,并不限于法条明定「除契约另有订定」的情形,也就是「有疑义,从任意」,最高法院在解释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的规范性质时,一贯强调其为「为补充当事人之意思表示而设」[72] ,当事人当然得以特约排除;就第四二七条:「就租赁物应纳之一切税捐,由出租人负担」是否强制规定的争议,也作成本条「非强制规定,当事人不妨为相反之约定」的判例[73] ,大体都能掌握此一立场
最后,对于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民事规范-契约,该如何解释?以其在实务上的重要性而言,我国法学迄今付出的注意实在是相当的不足。我国民法也未如法国、意大利民法,以专节(法国民法第一一五六条至一一六四条;意大利民法第一三六二条至第一三七一条)来规范契约的解释,而是参考了德国民法,针对各种之债个别作了若干零散的规定,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和德国一样(德国民法第一三三条),在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做了一个非常原则性的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第九八条),法国民法和意大利民法提出的第一个解释原则,皆与此雷同(法国民法第一一五六条,意大利民法第一三六二条)。这已充分说明了契约解释在方法上的特色,也就是绝对的主观取向,甚至可以不拘泥于文义。换言之,解释者放在心里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当事人「要什么」,而不是此一契约类型的本质「是什么」,私法自治的落实,便在此一关键[74] 。契约不只需要狭义的解释,还经常需要「补充」,这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学说上就很有争议了,德国学者多强调「假设的当事人意思」(das hypothetische Parteiwillen),虽然当事人通常正好就是未虑及此,从而所谓假设,实际上可能就是照相关法律去解释而已[75] 。然而无论如何,这又再一次说明,民事规范的解释活动,是如何的因规范性质与功能不同,而应该有所不同。
七. 本土化与社会化的新挑战
如果不太吹毛求疵的话,民法的移植,整体而言应该可以得到相当高的评价。
很自然的,就像西欧在完成罗马法移植之后,台湾的民法学者也开始尝试跳脱比较法的思考,从本土化、社会化的角度对民法的现状提出批判,立法者尽管仍大量援用欧陆和日本的民法来合理化财产法的修正,但从若干技术改良以外的创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本土化和社会化的挑战,绝非视而不见。然而沿着法律必须在社会的土壤里生根成长,这样的自明之理再往下思考,我们还是会碰到规范功能的问题。民法的响应如果不是建立于功能的正确认知,则本土化、社会化的热情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修正,也许我们会为立法者迄今的响应还只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应景」层次,感到庆幸。
如果正确理解民法的自治法、技术法和裁判法本质,如本文所论述,就知道民法面对的本土化课题,完全不同于经济法或社会法,乃至宪法那样的政治法。当学者严厉批评,把德国特有的、深具日耳曼法色彩的物权行为移植到东亚社会,注定会水土不服时,他可能忽略了这里涉及的,其实只是一个单纯的分析工具,一个裁判者内部操作的技术问题。物权行为把法律行为推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度,使它更能涵摄社会上多样而复杂多变的交易,而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争议时,提供更精致的正义,这里需要的「本土化」,只到专家间的技术移转为止,还不必到使用者的层次,交易者不需要知道或「认同」这些技术的细节,一点也不会影响交易的作成。就像动物学家需要一套更精密的语言,一些「学名」,作为彼此沟通、辩难的工具,对于到动物园里观赏动物的游客,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要确定的,是把生活中的一笔交易切分成法律上的三个行为(一个债权行为和两个物权行为),是否较能公平的处理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争议,如果肯定,它就是符合我们需要的民事规范[76] 。绝大部分的民法规定不以影响人民的行为为目的,已如前述,既不要「使由之」,又何需「使知之」?因此真正需要本土化的,是强制规定背后的价值观,和任意规定所反映的交易类型,这些才是决定法院最后产出的裁判,能否为人民接受的关键。而不是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体系,我们不可能重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民法概念体系,不管你称之为中华法系或台湾法系;即使做得到,那也是毫无意义的锁国政策。
民事规范牵涉到的价值决定,如交易安全与意思自由间(无权代理)或与财产权间(善意取得)的权衡,意思自由与利益衡平间的权衡(无因管理),创新与守成间的权衡(动产加工),未成年保护与交易安全间的权衡(成年制度),亲情与公共利益间的权衡(死亡宣告)等等,是可以也应该因社会而异的。我国民法从一个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立法者有时一开始就审慎的做了不同的价值决定,比如在法律行为的基本设计上比德国更偏向交易安全的维护;有的则是实施后才作调整,比如死亡宣告制度增加检察官的声请权。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有的制度在我国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比如人格权保护,因为欠缺尊重人格权的文化而没有太大的发展,背俗侵权则因为前缺「第六伦」的伦理观,而只在狭隘的五伦范畴发挥了有限的社会控制功能。我们也很难体会根植于日耳曼社会的那种对占有的重视,使得所谓所有人与占有人关系的制度(第九五二条至第九五九条),几乎完全未被利用。另外一个受到价值观影响的显著例子,就是区分所有权,当区分所有的客观需要随着都市化早已发生,而国家还来不及教育人民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所有权观念时,公寓大厦已经大量出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立法者,立刻发现源于欧陆的区分所有权观念极不容易本土化,台北市四万个公寓大厦单位,实际顺从该法「强制」而实施自治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这些例子说明,本土化的重点,不在勉强让技术性的语言及规范通俗化到一般人民可以了解的程度,而是尽量缩短规范与民众在价值判断上的差距,尽量贴近人民素朴的法感。而当民法的强制规范大致符合人民普遍的价值观或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只剩下专业间的技术移转问题,换言之,此时立法者应努力的,是使技术规范和语言更为逻辑、精确而具高度可操作性,不是刻意牺牲精确来成就表面的「本土化」。
任意规范的主要功能既在辅助自治,减省交易成本,补强合意的不足,则立法者越能掌握各种交易的典型,上述功能就越可发挥,已见前述。这应该是当前民法本土化的另外一个重点,从这个角度看本次修法,增设三种有名契约和五种次类型的努力,就相当值得肯定。有名契约的规定如果不能抓住交易社会的脉动,其结果就是被民间造法取而代之,拥有法律知识和经验的大企业将处于结构性的优势,本次修法把定型化契约纳入规范,固然可以降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欠缺有名契约指导的情形下,对于许多新兴交易,如补习、顾问、融资性租赁、应收帐款转让等,如何期待法院以第二四七条之一那样抽象的规范作成裁判,而仍有高度的可预见性?足见这部分的本土化,应该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
不过和本土化的诉求比起来,社会化恐怕是一个更难抗拒,也更具危险性的挑战。如果我们同意,绝大部分民法典的条文,至少财产法的部分,是无意管制人民私法行为的,它的本质只是一部裁判法,一套帮助法官做出合理裁判的法典,则我们等于承认,民法完全不具有社会改革的功能。然而吊诡的是,正因为民事财产法不去直接碰撞社会的痛处,像当初面对三从四德、宗祧继承的旧中国,民事身分法所扮演的角色那样,它才会比身分法更快速的进入我们这个和罗马法完全没有任何渊源的社会,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助力[77] 。不用强行,甚至不太强制,民事财产法像春阳一样,剥掉了台湾社会传统封建的外衣。也许要花上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必将看到同样的过程在中国大陆重演,在不幸的内外战争和乌托邦式的改革,浪费了整整七十年之后。从这个角度看,民法促成的又何尝只是改革,毋宁更近于一场宁静的革命,或者,一个「和平演变」的大阳谋。
微观和巨视也足以让我们看穿民法保守和改革的两面性和摆荡性。民法无视于阶级间的剥削,所得分配的恶化,也不管企业的精明和消费者的无知,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蒙住双目的女神,把现实的种种不平等,都放在同一个抽象的天平上,这是它保守的一面。但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民法也让各种改革的十字军自由进入自治的领域,使承租人可以主张土地法上的先买权,买受人可以主张消保法上的无过失责任,这又是它进步的一面。当改革者以「市场失灵」为理由进场干预时,民法的规定自动退让;等改革者承认「政府失灵」而解除管制时,民法又当仁不让成为自由市场的中流砥柱。因此尽管外观如一,民法的精神风貌其实是随着每个时代改革热情的起伏而迥然不同。对于这样的特质,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满意。德国就一直有学者从提升人民法律认知的角度,主张民法典应该像一部真正的法典一样,把散布于外,越来越芜杂的特别民法都搜集进来,重新整编,让人民可以一次看清楚他的权利和行为界限。主张以「内设」模式替代「外接」模式的学者,还强调体制中立、意识形态中立的虚矫,一九四二年的意大利民法,不就把土地法、建筑法的规定全部内接于相邻关系,劳动法置于债编之后独立成编,公司、合作社、保险、智能财产权等等,也都回归民法,造就一个全新的民法典范?然而这些批评者大概也很难否认,法典的理想永远和事实有段距离,即使条文数多达两千九百六十九条的意大利民法典,也像它的历史标竿-罗马法大全一样,很快就必须面临单行法在法典之外自立门户的残酷事实[78] 。内设各种特别法只是使得习法者对民法的原理原则更难掌握而已。
内设或外接,各有所长,偏偏民法这次修正,采取的是「局部内接」策略。土地法中的民事规定大举转进民法典,包括土地法第一~二、一~四、一~七、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九、一二~等,乃至土地法施行法、平均地权条例、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的零星规定。在另一个社会「敏感」领域-雇用契约,立法者虽未直接把劳工法规定移植进来,但依其精神,增订了雇用人保护义务(第四八三条之一)和对受雇人的无过失赔偿责任(第四八七条之一),强化了雇用关系的「社会性」,而减低了民事契约的「对等性」。不过最具有社会改革色彩的,应该还是在侵权行为增设的商品制造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一)、动力车辆驾驶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二)及危险制造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三),尽管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特别侵权责任都还延续动物占有人与工作物所有人的责任,采举证责任倒置类型,不能算是过于极端的改革,但以商品、车辆、危险所涵盖的社会活动之广,说我国民法所采的过失责任原则已经近于颠覆,恐怕也不为过。
然而民法推动的大部分改革,其实都还只是呼应民法外的社会改革,立法者显然又没有重新整编,把民法典变成「真正」民事法典的鸿图,只是择其一二纳编,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社会化,既不能使民事裁判者从此一本民法典走天下,反而使它的原始「市民法」图像变得完全模糊。尤其令人玩味的是,新修的商品制造人责任和定型化契约效力规定(第二四七条之一),和消费者保护法几乎是同时进行而先后完成,民法一方面表现「改革不落人后」的气概,另一方面又在用语上刻意的去除「社会角色」的痕迹,如避用「消费者」或「企业经营者」,以维持其「普通法」的风格。整个修正给人的观感,就是立法者的举棋不定,放不下法典的华丽风韵,又怕跟不上改革的时代脚步。我们现在也许很难评估,内设和外接何者才是最佳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说,本次修法所采的局部内设策略,并不能许给民法什么美好的未来。
结语
从人类历史的长流来看﹐社会生活的法律化是从民法开始,如果不把彰显国家刑罚权的刑法算进去的话,国家公权力被用法律「驯化」,已是相当晚近的事。优秀的罗马法律人两千多年前就在民法领域推敲各种公平正义的规则,而发展出十分精致的概念体系;中西欧各国继受罗马法,才能先后制定了技术上更臻成熟的民法典,和刚刚萌芽的公法不可同日而语。长期和未法律化的公权力关系并存,民法的教义学可以说自始就没有纳入公法的考量,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公法的发展一日千里,民法和公法的互动与冲突,才渐渐成为法学的重要课题。存在于民法内部的国家强制,和外部的国家强制,因为后者的法律化,而逐渐汇流。检察官介入民事生活,民法变成公共政策的工具,乃至在民事单行法法中加入若干行政制裁,都好象见怪不怪。
至于我国的发展,因属整套欧陆法制的移植,公私法本来应该没有先后,但民主政治条件不足,使得公权力阴影下的公法未受到重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法律人也和古罗马人一样集中耕耘民刑法领域,一直到民国七十年代,公权力关系的法律化才逐渐落实,整个发展过程,如同欧陆国家的缩影。但民法和公法的接壤问题,迄今仍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形下,功能法的研究角度,也就是去区分国家强制在公私法领域的不同性质,对国家强制和人民自治如何配合、互动加以类型化,再据以为民事立法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功能,做更清楚的定位,应该会有助于法律体系整体的顺畅运作,使公私法走向有机的结合。本文提出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观念,如果能在问题意识或研究方法上,促成那么一点微末的提升,也就达到目的了。
(全文结束)
*现经作者苏永钦先生特许登载在中国民商法网站,以飨读者!
注释:
[59]王泽鉴大法官去年出版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建立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无疑应列为法律系学生研究民法的必读书。
[60]前注10
[61] 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五四三号判例
[62]参阅立法院第一届第五十五会期第四十次会议审查「土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会议纪录,立法院公报第六十四卷第五十六期,院会纪录,页22, 民国六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二读会时多数意见认为不宜概括规定「设定负担」而采列举方式,刻意排除设定抵押权,以免「严重影响他共有人之权益」
[63]持肯定说的学者见解详参吴光陆,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之商榷,法学丛刊,第一三六期(民国七十八年),页49; 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民国六十五年,页366
[64]最高法院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民事庭会议决议
[65]如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民国八十一年修订版,页396-97, 注16
[66]如谢哲胜,共有土地的出租与土地法第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的适用,收于财产法专题研究,民国八十四年,页145-156
[67]多数共有人出卖共有物本来就不发生效力问题,已如说明。如果扩张到买卖,可以解释成该少数共有人未参加的买卖效力及于其身,而可成为财产损失的「原因」,则本条将成为多数共有人(或少数大共有人)诈害少数共有人(或多数小共有人)的合法管道,不公孰甚!
[68] 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的观点,作为新兴的解释方法,它无疑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过就此处所区隔的政策性强制规范与单纯自治规范而言,在经济分析上刚好也可能分别运用不同的理论,后者最适用的就是以厂商或消费者行为为中心的个体分析,前者则可能还有运用某些总体理论的余地,这个看法是从法律经济学者熊秉元在今年五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举办的「法与经济分析」研讨会中发言得到的启发,不敢掠美,特加说明。
[69]荷兰新民法第3:84条第3项明文禁止让与担保;另参B. Wessels的引介, 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 System, Contents and Future, 41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78(1994)
[70]在民法研究会在去年的第十五、十六两次学术研讨会中,针对黄立与陈自强所提论文,学者间对于未经公证的不动产买卖或赠与约定可否发生预约的效力,颇有不同看法
[71]至于我国民法未对预约作一般性规定,不动产交易的预约是否和本约一样要经公证,也还有待深论,德国学者认为此处属于隐藏性漏洞,应透过解释加以补充,可参Larenz/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A., 1995, 198f.; 就我国而言,不仅不动产公证制度刚刚萌芽,功能有待考验,且预约效力毕竟不同于本约(前注49),应无Larenz/Canaris顾虑的脱法问题,是否适宜「类推适用」,本文暂持保留看法
[72]如二十九年上字第八二六号、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三二二八号判例
[73]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一一九号判例
[74]不知道是否有意,大陆民法通则就没有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学者解释虽也强调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但显然较偏向文义与客观的目的,如梁彗星,合同的解释规则,收于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二册,一九九九年,页255-268; 新通过的合同法第一二五条规定合同的解释方法同此
[75]Flume, 前注21, S.321ff.
[76]参阅拙文,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收于「跨越自治与管制」,民国八十八年,页219-259
[77]拙文,韦伯理论在儒家社会的适用-谈台湾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收于「经济法的挑战」,民国八十三年,页59-81
[78]参阅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前言中提到一九七八年通过的第三九二号法律规定有关城市不动产租赁,一九八二年第二~三号法律规定乡村土地租赁,都未直接在法典内规定 出处:本文原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