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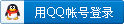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房保国
监狱是一种使坏人变得更坏的昂贵方式。
——1990年英国国会下议院,政府白皮书
与其将司法限定为报应,不如让我们把司法界定为恢复。如果犯罪是一种伤害,那么司法就应修复伤害和促进康复。
——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种所有与犯罪有关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决定如何解决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及对未来的影响的过程。 作为一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迅速发展起来的“非正式性司法”(Informal Justice),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纠纷解决方式。 它使刑事司法关注的焦点从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人身上转移到犯罪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害上,并且将刑事冲突的解决归还给了被害人和犯罪人,授权他们自己解决责任问题。恢复性司法在使人们重新考虑对待犯罪方式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处遇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总体上看,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于被告人的权利提供了系统的宪法保护,而被害人的保护明显不足。由于犯罪人数量的空前增长,被害人的数量也在增长,“既然被害人和犯罪人问题经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刑事司法制度为犯罪人提供了正当程序(due process),也必须为另外一批顾客——即被害人,提供相应的新规则和新规定” 。
恢复性司法就是通过让犯罪人承担责任和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以及社区通过对被害人的支持和为犯罪人提供机会和技能使其重新成为社会中有贡献的一员,从而实现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归复(rehabilitation)。恢复性司法中通常包含三方主体: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被害人在恢复性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恢复性司法也更强调对被害人的保护。通过恢复性程序,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得到消解,赔偿心理得到满足,伤害受到治疗,由怨恨到宽恕,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际关系得到维持,从而被害人得以回归社区与社会。鉴此,本文拟对被害人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实践效果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观念变革进行系统探讨。
一、 从疏远到参与: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范式
恢复性司法更强调被害人的参与,它把被害人从传统刑事司法的边缘状态中拉了回来,并且使其成为控制程序的主角之一。被害人对恢复性司法的参与,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美国司法部实施的邻里司法中心 ,1974年门诺派教徒中央委员会(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成员与缓刑官员一起在安大略省的基陈纳市(Kitchener)附近组织的“受害人——犯罪人调解”项目,是恢复性司法的第一次尝试,接着在1978年于印地安那州的俄克哈特市(Elkhart)也组建了类似的组织。 1980年在美国有超过80个城市拥有了非正式的纠纷调解项目,六年后也就是198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50个。同时,恢复性司法项目在其他国家也得到发展, 如加拿大是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VORP)的先驱,英国和法国也建立了许多项目,并且在日尔曼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鼓励。在新西兰,被害人被邀请参加的家庭团体会议(FGC)已经以立法的形式成为处理那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主要机制。
(一)基本模式
按照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方式和恢复性司法运作机制的不同,可以将恢复性司法分为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1.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简称VOM模式)
由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缺少对被害人的应有关注,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叫被害人作为证人,被害人就完全被刑事司法程序遗忘了。因此,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OM)就是针对此弊端所产生的改革运动,它将被害人和犯罪人聚集在一起,由一名调解人主持双方会谈和负责推动程序,在会谈中双方开诚布公,被害人讲述他们的受害体验和犯罪对自己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犯罪人解释他们究竟对被害人实施了什么伤害和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并且回答被害人提出的问题,在双方讲述完毕后,由调解人帮助双方确定使事情好转的方法和手段。
尽管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OM)在具体形式上有些细微差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结构,一般说来包括四个阶段——进入阶段(Intake)、调解准备阶段(Preparation for Mediation)、调解阶段(Mediation)和后续阶段(Follow-up),具体说来: (1)在进入阶段,进行一个预先筛选,由一个经过训练的社区自愿者或职员人员担任调解者进行审查,对那些双方表示愿意协商和相互之间没有明显敌意的被害人和犯罪人接受进入该程序;(2)在调解准备阶段,调解者与被害人和犯罪人分别谈话并确定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如果调解者感到还没有和每一方建立信任和友善的关系,那么这个案件就会被送回去法院;(3)在正式调解阶段,双方讲出自己经历的事实,详细地进行商议,理解彼此的处境,通常达成一项赔偿协议或工作命令,产生适当的解决方法。如果达不成协议,案件同样被送回法院;(4)在最后的后续阶段,监督犯罪人进行工作或进行赔偿,确保协议的履行。
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把被害人和犯罪人进行面对面(face-to-face)的联系,让被害人直接参与,赋予其对于结果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权,这样就可使被害人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重要性,并使其受到很好的治疗,以便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犯罪者也被希望为他们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结果,并且有机会恢复破裂的关系。在VOM模式中,引入社区的参与以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恢复性司法项目在具体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普遍地试图通过增加一些社区参与保持VOM的目标。社区成员被认为是非直接当事人,因为他们可能害怕将来成为被害人,他们可能希望重新确定犯罪行为违反的标准,吸收犯罪保险成本,当犯罪发生时有所反应。而且,他们经常被看作带来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联系”的能力,当其试图修复犯罪伤害时提供支持。”
VOM调解程序以当事人的自愿参加为前提,主要适用于第一次或第二次犯罪的青少年犯人中,也有些项目适用于杀人、抢劫、强奸等重罪案件,但是对于一些毒品、腐败和针对国家的犯罪等“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并不适用。近年来,VOM调解模式仅在美国就处理了16,500件案件,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125个项目; 并且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可,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新西兰毛利人的会商模式(Conference)
在新西兰,毛利人(Maori)有着自己传统的内在的独特刑事司法制度,尽管新西兰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法律受到英国的深刻影响,但毛利人的恢复性司法依然存在,形成了两种司法模式并存“一国两制”情况。
在毛利人地区,一些像盗窃、袭击之类的轻罪和一些更严重的性犯罪等都被交由当地的年长者处理,只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案件才找到警察。大概的程序是一方召集家庭成员在一起进行讨论,双方被邀请参加一个“会”(hui),被告人需要作有罪答辩并且不能隐瞒事实,年长者进行教育,对犯罪人及其家庭施加耻辱,经常达到使其流泪的程度。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医治创伤和使事情恢复到“正常”状态。被偷的东西予以返还或者进行赔偿,损坏的东西予以修复,刑罚经常包括犯罪人要进行一定的强制工作等。比如下面的这个案例就体现了该程序的完整过程:
在一个强奸未遂的案件中,一名17岁的男孩在被指称脱掉了一名16岁女孩的内衣裤之后才终止行为。当地毛利人的酋长兰格蒂勒就组织了一个“会”(hui),这名16岁的少女还有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和叔叔、阿姨等都参加了,他们坐在那名17岁男孩的对面。当这名男孩作有罪答辩后,主持会议的一名老年妇女就开始发言了,她痛斥这个男孩行为的罪恶,说他侵犯一名年轻的女子,既触犯了神的禁忌,也给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带来了耻辱。不一会,这名男孩和他的家人都流泪了。
接下来,对这名男孩的惩罚就是要求在12个月内无论何时有婚宴,该男孩的家庭都要供应肉和蔬菜。此外,他还必须把该会议室粉刷一遍,更换已经不能用的护墙板和瓦楞铁。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该会议室属于他们共有,这名女孩和其家庭成员就在男孩家庭人员工作的时候为其提供饭菜。两方走在一起显示出和解的倾向。最后,他们平静下来一起修理餐厅和周围的栅栏。整个程序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上述毛利人司法的事例中,没有警察的介入,这名女孩在程序中受到正当的对待,其创伤受到医治,那名男孩也没留下犯罪记录,体现了一种恢复、治疗和协商的精神。 “建立毛利人司法是为了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它不是对犯罪人落井下石,而是重视受到伤害的人——它谴责那些说社会是被害人的人。是我,而不是社会受到伤害。毛利人司法减轻被害人的责任,而将其施之于应该承担责任的犯罪人。” 毛利人司法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为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提供帮助与治疗。
3. 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模式(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s,简称VORP)
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VORP)是让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协调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恢复性程序,会议的通常结果是达成一份犯罪人以某种方式赔偿被害人的协议。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从与被害人的会见中受益。美国的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模式产生于安大略省,与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和教友派信徒(Quakers)相联系,被称为是“宗教性浪漫”。 在一些司法区,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的参与工作地如此的好,以致成为缓刑或者假释的一项条件。
4.青少年犯罪的恢复性项目
青少年犯罪是恢复性司法重点救助的对象之一,代表性的项目有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模式(Family Group Conference,简称FGC模式),和英国最近的犯罪座谈小组(Youth Offender Panels,简称YOPs)。
在新西兰,1989年通过了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法(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ct),进行了深入的司法改革,在阿尔提拉(Aotearon)地区兴起了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团体会议模式(FGC)。在家庭团体会议中,由一名协调人主持,地点通常由犯罪人的家庭来定,但有时也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朋友的家里或教堂等。在大多数案件中,一旦青少年犯罪人被警察逮捕或指控,他们就可以适用非正式程序。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对各国的恢复性司法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家庭团体会议经常首先由犯罪人的家庭启动,先是进行祈祷,接着由协调者介绍当事人,宣读警察提供的事实概要,这可以为被告方提出质疑和当场予以修正。如果被告人否认指控的内容,那么案件就会被转移到少年法院举行听证,当然一般来说被告人是承认有罪的。接着由被害人陈述,通常是阐述犯罪对其生活造成的严重不良影响,这通常会令犯罪人感到吃惊,使其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生活产生的严重妨碍。这种眼球对眼球(eyeball to eyeball)的见面是非常重要的,它使青少年犯罪人不再冷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被害人;也为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以及接触社区,掌握对程序的一定控制权。
犯罪人在认识到自己造成损害后,通常会自责和道歉。接下来讨论合适的惩罚问题,这时被害人的观点又是很重要的,他们拥有否决的权利。被害人一般会选择要求改正错误、修复损害、道歉和让犯罪人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做一定的工作。警察和协调人接着会陈述他们认为合适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阶段家庭成员是退场的。当家庭成员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家庭的代表站出来宣布就惩罚问题的决定,一般来说都会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在该会议中,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他们对程序的感受和与他们分享思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通常都会说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犯罪人。
家庭团体会议将对案件决定的权力由国家转移给了当事人及其家庭,让犯罪人对其自己的行为直接承担责任,让被害人参与到程序中来,并对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被害人被鼓励参加团体会议,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讨论决定适当的惩罚措施,这对被害人从被害状态中的康复具有重要作用。
同样,在英国,针对报应型司法的失败,兴起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 1998年通过了犯罪和无秩序法(Crime and Disorder Act),接着成立了青少年司法委员会(Youth Justice Board)和青少年犯罪组(Youth Offending Teams);1999年工党政府通过了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成立了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uth Offender Panels,即YOPs),在青少年恢复性司法上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s)会议的地点通常在离犯罪人和座谈小组成员住所都比较近的地方举行,至少包括两名经过青少年犯罪组(YOT)训练的社区志愿者参加,其中一名来主持会议。在法院发出命令后的15个工作日之内要举行第一次YOP座谈会议,年龄在16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者及其父母,还有被害人及其父母,社区成员等都参加座谈,程序不像法院的那么正式。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通常会和犯罪人达成一项协议,要求其为被害人和社区服务和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继续犯罪。如果达不成协议或者犯罪人拒绝签署协议,那么他将会被送回法院重新审判。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并且负责监督犯罪人遵守和履行协议,如果规定的期限达到后没有违反的情况,那么按照1974年犯罪归复法的规定他将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二)主要特征
从上面列举的几种代表性恢复性司法项目中,我们可以发现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有如下几点共同规律:
第一,恢复性司法项目的运作都是由一名作为第三方的调解者主持。这些调解者一般来自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社区,是自愿者性质的,他们往往经过一定的训练,也有些调解者是恢复性项目的职员。整个会议讨论的进行,由这名中立的调解者主持,保持讨论集中不偏离主题,当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并且负责监督各方的行为。
第二,把纠纷诉诸社区而不是国家。尽管大部分恢复性司法项目处理的案件是由检察院、法院等刑事司法机构介绍或者引进的,但纠纷的解决都在社区,它是一种“邻里纠纷解决”(neighborhood dispute resolution)。社区介入恢复性司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社区的代表直接介入,例如作为家庭团体会议的调解者、青少年司法座谈小组的成员等参与进来,这样被害人与犯罪人纠纷的解决就不仅诉诸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庭,而延伸到整个社区;二是非直接的形式,即社区是每一具体犯罪的非直接受害人,整个社区作为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进来。
第三,被害人与犯罪人通常是相互认识的。他们经常是邻居、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即使是商店老板和顾客也可利用这样的项目),纠纷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彼此熟悉,这种相互熟悉对于达成一个妥协协议是有益的。
第四,遵循自愿性原则。一是程序的启动要求被害人和犯罪人完全自愿,纠纷双方必须同意通过该项目来处理问题,如果一方拒绝参加,那么该纠纷就会回到更正式的法律诉讼领域;二是结果的自愿,基于双方的同意产生结果,在调解者的帮助下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的决定,当讨论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案件将会被送回到法院处理。
最后,程序的非专业性和非正式性。程序不是由法官引导,也没有律师的参与,没有法律的职业化色彩;程序没有固定的模式,正当程序的概念和证据规则都不适用,调解者可以按照他或她认为适合的方式自由地举行每次会议,“该程序提倡讨论而不是严格的事实发现” 。
二、 从复仇到和解: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对一系列司法概念和哲学观点引起挑战,具体说来就是涉及到从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到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从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到社区司法(Community Justice),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Reintegrative Shaming),和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到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司法模式的转换。从整体上看,“我们需要发现一种哲学,能够从惩罚到和解,从对犯罪人报复到对被害人医治,从疏远和粗暴到社区与全体,从消极和破坏到治愈、宽恕与同情。该哲学基础就是恢复性司法。” 因此,恢复性司法的引入对于保护被害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系列理念的转变和一种新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从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到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
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就是追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效果,追求被害人复仇心理的实现和愤怒仇恨的宣泄,追求犯罪人被判处监禁刑罚,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但在整体上看,在报应性正义理念指导下的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是不成功的。因为:
首先,在报应正义观念的影响下,刑事司法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强调的是复仇(Vengeance)、该当(Desert)和刑罚(penalty)。这种报应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实现报应和惩罚为主要目标,认为“惩罚能有效地谴责犯罪行为和要求为其报偿.法院的量刑表达了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反对和决定对它的惩罚,” 因此,它本质是一种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
而惩罚是一种法律上的暴力,却不是唯一和最好的方式。“我们是一个惩罚性的民族,我们正被迫接受我们复仇愿望带来的结果。”“在目前的制度下,所有的权力被交给国家——法官、警察、监狱看守人。被害人和犯罪人被遗忘,他们感到无能力;因为被害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没有给犯罪人提供任何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和举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相反,现有的倾向仅仅是惩罚,承担责任和使事情再次变好这一对概念被忽略了。被害人和犯罪人被否定了权利和责任。” 犯罪人通过对国家承担抽象的刑事责任,而规避了对被害人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
其次,报应性司法的成本非常高昂。一方面整个刑事程序的成本很高,诉讼周期很长,比如为了追诉一个盗窃200美元的案件,可能要耗费5000美元的刑事司法资源,同时当事人请律师也要花很大的费用;另一方面是监狱的成本高昂,国家花了千百万的钱财建造新的监狱和维持旧的监狱,比如在新西兰,看管一个需要采取最大安全措施的犯人国家每年要花$70,000,即使对于需要采取最小安全措施的犯人每年也要花$24,000—$35,000,这相当于每周每个犯人要花$1500,也就是大约一天$200。 同样在美国,自1980年到1996年花费在监狱上的成本从每年70亿美元增加到了380亿美元,增加了4.43倍,从1992年开始有四个州花在监狱上的费用每年超过10亿。 可见报应型司法的成本是多么高昂,而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却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
再次,作为报应型司法主要体现的监禁刑流弊颇多,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监狱成为整个国家藏污纳垢的地方,按照1987年新西兰天主教教主会议的描述,监狱是“国家血液中的毒药”,“他们认为监禁是对人类尊严的公开侮辱,应该部分的或全部的,当前的或者永远的对那些受到破坏的犯人负责。他们发现很难想象出一种比这种花费公共资金更具有破坏性或浪费性的方法了。” 吉姆·康瑟丁(Jim Consedine)列举了监禁的十大毒害:(1)被监禁的大多是穷人;(2)监禁使人变的更残忍;(3)监禁破坏了犯人与家庭、社区的关系;(4)监狱内的吸毒问题严重;(5)监狱成为训练新犯罪成员的基地;(6)监禁达不到阻吓他人犯罪的效果;(7)犯罪与失业相联,并且是恶性循环; (8)程序是选择性的和歧视性的;(9)监狱内非常高的自杀率;(10)警察等刑事司法人员的腐败。康瑟丁甚至激烈地批评,认为“监狱是一个走到尽头的措施。从社会上、道德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它都是正在吞噬人类社区心脏的癌症。它像奴隶制度一样有害和陈旧。”
而监狱里面会形成一种亚文化,使人感到厌倦、烦闷、暴力、浪费和压制,“监狱可以改变人们,但可以使一些人变得更狡诈,由于其惩罚的性质,监狱除了将犯人变成社会的终身负担外无能为力。”而绝大多数犯人不是杀人犯、强奸犯或无可救药的坏人,他们主要涉及的是饮酒、毒品和汽车犯罪等,年龄大多30岁以下,未能完成学业,缺少与家庭和社区的强有力联系,急需要接受教育。
最后,报应性司法的实施效果有限,犯人重新犯罪率高。比如在新西兰,大概2/3的人在判刑两年之内又回到监狱。犯人的重复犯罪率高,其原因可能有:一是监狱完全封闭,与外界隔绝,内部条件恶劣,使犯人的心灵和精神扭曲,加强了思想畸形和对生活的不真实期待,从而再犯;二是犯人之间相互“学习”,交叉感染。“监狱长期以来被称作‘犯罪大学’,是训练新朋友和新的团伙成员,学习新的犯罪技术,以及作出新的犯罪计划的主要地方。”三是社会对犯罪人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不接受以前被监禁过的人,犯人被释放后60%处于失业状态,从而诱发新的犯罪。
而犯罪人重新犯罪率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被害人,更多的伤害,更多的痛苦和对一些人更多的恐惧。“恢复性司法的提议者不赞成更严厉和更肯定的处罚来威慑或者使重复犯罪者丧失能力。他们很可能相信,把犯罪者放进监狱加强了而不是阻止了其犯罪行为,并不能为犯罪者提供他们成功重新回到社会所需要的技能。”
可见,报应性司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惩罚,成本高昂,对犯人的改造非常不力,重新犯罪率高,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A Dead-End Street)。“报应和复仇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方法和刑罚的核心。他们在一个饥饿的国家形成了一种昂贵的、粗暴的、令人失望的和浪费的选择,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结构性的非正义。”因此,报应性司法的哲学基础是破产了,就像新西兰基督堂市律师Wolfgang Rosenberg所说:“……公众需要报偿,这说明我们仍接近于野蛮状态。当复仇终止的时候文明才开始。”
而与报应性正义相对称,笔者称之为“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在恢复性正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恢复性司法则强调对被害人、犯罪人进行修复和赔偿。可以说,报应性正义追求的是被害人复仇心理的实现,恢复性正义则体现的是被害人的宽恕心理和要求赔偿的心理;报应性司法关注的是“我们如何惩罚犯罪人?” 而恢复性司法则关注“我们如何修复犯罪造成的损害?”在恢复性司法那里,不仅要指出犯罪人的错误,而且要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协调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关系,重建社区的安宁与和谐。
1990年英国“犯罪,司法和保护公众”的白皮书中,就认识到了报应性司法的弊端和在发挥阻吓作用方面的局限性,该白皮书鼓励对被害人的赔偿,发展出一种单位罚金的制度,提高对监禁社区为基础的选择,“这比监禁刑对被害人、公众和犯罪人更有利”,“它给法院以新的权力,可以结合使用补偿、监督和罚金等刑罚,提升了社区服务命令和缓刑作为对监禁刑的替代。它要求法院在作出监禁刑之前必需确信罪行严重到相当的程度,监禁是为保护公众避免更严重的伤害所必需.法院也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 恢复性司法认为,对犯罪的正确反应不是报应和惩罚,而是恢复因犯罪而造成的各种伤害;真正的负责不是消极地接受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地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加强犯罪预防作用。
恢复性司法与报应性司法的主要区别有:
报应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
犯罪被认为是孤立的个人反对国家的斗争 犯罪被认为是个人对个人的侵犯
强调惩罚、谴责,关注的是“是不是他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罚”,因而是回顾性的 强调解决问题,关注的是“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如何消除犯罪造成的影响”,是前瞻性的
对抗型的关系和标准化的过程 合作型的关系和非正规的,具有很大弹性的过程
为了报应和威慑而强行处罚 为了和解与恢复而协商、赔偿
正义被定义为目标和过程,强调规则的公正 正义被理解为良好的关系和理想的结果,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
刑罚被认为是一种恶害,刑事司法是以恶制恶 具有建设性和恢复性的措施去修补犯罪造成的损害,以消除犯罪形成的恶
社区地位边缘化,在理论上被抽象的理解,为国家所代表 社区发挥主导作用,调解纠纷,消除犯罪的影响
鼓励对抗性、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和个人主义 弘扬社群主义,强调集体价值
司法过程体现为国家和被告人的关系,被害人没有主体地位,犯罪只是被动地接受刑罚 司法过程体现为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通过协商讨论对犯罪的解决办法,被害人的物质精神要求得到尊重和承认,犯罪人被鼓励积极地面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并尽力消除这种损害
犯罪人的责任被定义为接受刑罚处罚 犯罪人的责任被定义为理解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并使因犯罪而恶化的情况好转
犯罪仅被视为对法律的违反,全无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维度 犯罪被全面理解,包括道德、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
犯罪人对国家负有“债务” 犯罪人对被害人和社区负有责任
针对的是犯罪人的行为 针对的是犯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
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带来耻辱 通过鼓励犯罪人积极地承担责任而消除犯罪带来的耻辱
既不鼓励犯罪人悔罪,也不鼓励被害人谅解 鼓励犯罪人认罪和道歉,鼓励被害人谅解
依靠专业人员的运作 依靠当事方的积极参与
(二)从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到社区司法(Community Justice)
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指的是以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为基础的刑事司法,这种刑事司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生纠纷后更多地诉诸社区和私力救济,国家远没有达到现在如此高的权威,按照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的观点,“综观西方的大部分历史,犯罪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犯,更像那些被视为‘民事’的冲突和错误。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候,人们认为主要的反映必须是如何使事情变得更好;赔偿和补偿非常普遍,或许是标准的形式。犯罪产生了义务和责任,这通常需要通过协商的程序予以承担。复仇的行为可能发生但并不是很经常,复仇的功能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被害人和犯罪人在这种程序负有责任,社区也要承担责任。国家也有作用但是受到限制的,只在必需时按照被害人的愿望发挥作用。” 那么是何因素促使社区司法让位于国家司法,国家取得了刑事司法的主导权呢?
对此,天主教大赦年文件中作出了阐释,认为直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君主制度的巩固之前,被害人经常是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诺曼第人入侵的时候发生了模式的转变。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子孙为维护政治权力必须与男爵和其他权威斗争,他们发现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法律程序在确立他们对一些长期事情上的主导权和增加政治权威上是一个高度有效的工具。为了达到该目的,威廉的儿子亨利一世在1116年发布了亨里西法(Leges Henrici),创造了“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这一理念,确立了王室对于违反该法的纵火、抢劫、谋杀、伪造货币和暴力犯罪等特定犯罪的管辖权。对于那些违反了“国王的和平”的人就是反对他们的人,因此国王就成为这种犯罪的主要被害人,就在法律上取代了实际被害人。实际的被害人在程序中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国家和犯罪人被留为主要的关注主体。
这种国家司法的观念,认为把刑事司法权交由国家进行垄断,有助于避免复仇和避免扩大社会暴力,刑事司法变成将来导向的,关心让犯罪人和潜在的犯罪人遵守法律,而不是让他们弥补过去的罪行。赔偿由于是过去导向的和关注于被害人,逐渐被废除;本应支付给被害人的金钱也被作为罚金支付给国家。这种完全忽视被害人的地位、视惩罚为主要意旨的国家司法,按照挪威犯罪学家尼尔·克里斯特(Nils Christie)的话说,国家通过法官、检察官等“治疗人员”和律师,“偷走了直接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不仅取走了被害人的直接补偿,而且剥夺了被害人及其社区参与、更充分理解和标准区分的机会”。
恢复性司法事实上对国家垄断权的合法性提出置疑,认为犯罪主要是对个人的侵犯和社区安宁的威胁,而社区在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回归社会上发挥至关重要的地位。这里就涉及到“国家”与“社区”的二分法问题,社区(community)又包括地域社区和熟人社区,前者指的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人们组成的一个小社会,后者指的是有共同兴趣和爱好,彼此熟悉的人们组成的交往圈。由此社区被纳入到恢复性司法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域社区因犯罪受到了影响;二是熟人社区与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关系特别,关系到恢复性司法的过程和结果。 在“社区”和“国家”之间暗含的区别贯穿于恢复性司法理论:国家司法是强制性司法、惩罚性司法和等级性司法;而社区司法是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包含了从国家权力向社区权力的转移,他们代表了一种向往,即通过社区提高市民权利和使司法变得更加可以接近、有效和公正,社区的福利和恢复到和平与和谐的状况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恢复性司法也就等同于社区司法。社区司法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取代犯罪概念中的国家司法形式,把一体化赔偿、协商、治疗和宽恕等理念融入到刑事司法中。与国家司法相比,社区司法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社区司法有助于恢复被害人和社区的良好关系,促进被害人的社会归复。让被害人、被害人的亲属,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社区成员参加进来,通过面对面的会谈和讨论,被害人能够收到关于犯罪的信息,表达自己因犯罪受到的影响,有效的控制程序的结果,从而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恢复。同时,社区成员有权利参与处理社区中发生的案件,可以使其避免对犯罪的恐惧,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增强集体感和荣誉感,有助于社区的团结安定。
其次,社区司法有助于节省国家司法资源,增加社区资本。与上文列举的报应性国家司法的昂贵成本相比,社区司法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如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e)导致了较低的法院出庭率——在1987年到1996年间几乎降低了2/3,较低的监禁率——在1987年到1996年间,降低了50%以上;犯罪人如能合作和履行社区服务,就可完全避免被监禁,从而大大降低了监狱的成本;被害人、犯罪人不需要请律师,也节省了律师费用等。
最后,社区司法有助于犯罪人的改造。在社区成员和犯罪人、被害人家庭成员及其亲属的参加下,犯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时,经常会倍感耻辱,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当看到被害人的伤痛和凄苦时,犯罪人经常后悔不已,主动进行赔偿;在看到社区成员对自己的宽容和支持后,犯罪人则经常深受感动,表示积极为社区做有益的事情,从而使犯罪问题在社区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三)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
重新融合性耻辱(Reintegrative Shaming)是指在惩罚谴责犯罪人,让其承担耻辱性后果的同时又保持着对犯罪人的尊重,它是把犯罪人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来对待的,注重犯罪人与社区的联系,在宽恕、协商的氛围中达到犯罪人的社会归复;而烙印型耻辱(Stigmatic Shaming)追求的是惩罚,通过肉体的或人身自由的限制(如监禁)将污名烙在犯罪人身上,使犯罪人与普通社区成员相区分,从而使犯罪人的社会归复非常困难。从整体上看,重新融合性耻辱与恢复性司法相联,而烙印型耻辱则是传统报应性司法的核心要素。
按照马凯(Makkai)、托尼(Toni)和布雷斯韦特(Braithwaite)的观点,重新融合性耻辱具有以下四项特征:一是在保持对行为尊重的同时谴责错误的行为本身,并且和谴责相伴随的是对犯罪人的支持、关心和帮助;二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使行为人感受到社区对他的行为的态度和评价,并且这种形式越郑重,参加越多,犯罪人感受到道德压力就越大,来自犯罪人熟悉和信任的人的谴责越多,犯罪人越容易产生耻辱感;三是在谴责的同时包含着鼓励和接纳,支持行为人改正错误,作一个积极的成员融入社区;四是避免给行为人贴上恶人、犯罪人的标签,不将行为人类型化为社区的破坏者,而是承认每一个人身上都蕴涵着积极的价值,都可以对社区,对他人有所贡献。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1995年举行了融合性耻辱实验项目(Reintegrative Shaming Experiment——RISE) ,在被害人方面访问了232个人,一部分是18岁以下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的有个体被害人的财产犯罪,二是30岁以下的犯罪人实施的暴力犯罪,对于严重的可起诉的犯罪,性犯罪和家庭暴力被排除。采取调解形式,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召开讨论会,通过让犯罪人直面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促使其产生耻辱感。这些主体一半被分配到恢复性司法组,一半被分到法院组按照传统刑事司法程序进行,最后分配到恢复性司法组的人员产生了较为积极的结果。
(四)刑事司法模式的变革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是以保护被告人为中心的模式,强调正当程序,强调对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和不受非法搜查、扣押的权利等一系列宪法性权利的保护,被告人由于其处境劣势的弱者地位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司法的关注。
然而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模式下,推崇国家的权威,由于它关心法律为什么被破坏和如何阻止其再次被破坏,所以它主要集中于犯罪人而不是被害人。被害人被完全边缘化,成为无足轻重的普通证人,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叫被害人作为证人,被害人就完全被刑事司法程序遗忘了。被害人充满巨大的痛苦而没有治疗,仅仅被作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这完全是一种国家决定型的犯罪处理方式。
而恢复性司法则使被害人成为司法体制的中心,强调被害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维护被害人的尊严,被害人对于最终结果拥有完全的否决权。它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其背后的理念是让对立的双方一起设计出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合适方案,这有利于改善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消除犯罪的不良影响 。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零和理论”问题。所谓“零和理论”(zero-sum),就是指一方的损失造成另一方的获益,或者说一方的获益是另一方的损失产生的,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那么,在被害人的权利和被告人的权利之间,能否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或者说形成一种双赢(win/win)的局面呢?调查结果显示,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普遍的。
例如,被害人对部分事实的承认,有可能就是被告人的获益,被告人与原告人面对面的诚实的对话和协商,完全可以使纠纷在协议的范围内解决。斯辰芝(Strang)建议在恢复性司法中,举行一种议程是很宽的程序,试图使其中一方的所得也有利于另一方;她把成对的问题相对比——例如犯罪人理解其他人是怎么感受的吗/被害人感到道歉是真诚的吗?——如果两者大多数回答是积极的,这被分类为双赢。大多数情况是如此的,比如在感情上,4/5的家庭会议都比法院在提高移情作用上明显的高(因为恢复性司法完全考虑感情,而法院则倾向于排除感情或者仅仅是利用感情来作为试图确保或避免定罪的工具),同时在信任警察和尊敬法律方面也都明显好于法院,在只关于协商会的问题上,大多数的问题也显示超过70%或80%的双赢,由此她得出结论说,“恢复性司法理论在所有法院受到强有力支持,在家庭会议上双赢是普遍的,而在法院司法上双输(lose/lose)是普遍的。”
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与被告人的权利可以完好的协调,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它提供一个更人性化,“更温暖的纠纷解决方式”,体现了一种建立“社会化法院”的努力;恢复性司法不仅是以被害人权利为中心的司法,它还是一种完全“当事人主义化”的,有利于诉讼各方的新型司法。
可见,从总体上来看,恢复性司法被认为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制度:被害人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赔偿获得补偿,在案件的处理中可以发表意见,成为处理犯罪人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犯罪人被认为要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并且要服从一切可能的处理,他们作出改进并被提供协助,以便减少将来再犯的机会;社区也可以通过犯罪人支付或者服务的方式获得补偿,同时社区还可以被用来协助被害人,让犯罪者工作和寻求消除犯罪的原因;国家采取这种方式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协助,将会对所有各方提供公正和衡平的程序。在本质上,“恢复性司法寻求把所有各方放到相互协助的谈判桌上。每个人怀着需求而来,带着某种程度的满足而归。”
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恢复性正义,而不是报应性正义,它是一种社区司法,而非国家司法,通过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使犯罪人得到教育,被害人得到康复和赔偿。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图表显示:
A.恢复性正义 恢复性司法 社区司法 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 被害人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 | | | |
B.报应性正义 报应性司法 国家司法 烙印型耻辱理论 被告人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出处:原载于作者个人主页 |
240331
房保国
监狱是一种使坏人变得更坏的昂贵方式。
——1990年英国国会下议院,政府白皮书
与其将司法限定为报应,不如让我们把司法界定为恢复。如果犯罪是一种伤害,那么司法就应修复伤害和促进康复。
——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种所有与犯罪有关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决定如何解决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及对未来的影响的过程。 作为一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迅速发展起来的“非正式性司法”(Informal Justice),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纠纷解决方式。 它使刑事司法关注的焦点从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人身上转移到犯罪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害上,并且将刑事冲突的解决归还给了被害人和犯罪人,授权他们自己解决责任问题。恢复性司法在使人们重新考虑对待犯罪方式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处遇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总体上看,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于被告人的权利提供了系统的宪法保护,而被害人的保护明显不足。由于犯罪人数量的空前增长,被害人的数量也在增长,“既然被害人和犯罪人问题经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刑事司法制度为犯罪人提供了正当程序(due process),也必须为另外一批顾客——即被害人,提供相应的新规则和新规定” 。
恢复性司法就是通过让犯罪人承担责任和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以及社区通过对被害人的支持和为犯罪人提供机会和技能使其重新成为社会中有贡献的一员,从而实现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归复(rehabilitation)。恢复性司法中通常包含三方主体: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被害人在恢复性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恢复性司法也更强调对被害人的保护。通过恢复性程序,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得到消解,赔偿心理得到满足,伤害受到治疗,由怨恨到宽恕,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际关系得到维持,从而被害人得以回归社区与社会。鉴此,本文拟对被害人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实践效果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观念变革进行系统探讨。
一、 从疏远到参与: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基本范式
恢复性司法更强调被害人的参与,它把被害人从传统刑事司法的边缘状态中拉了回来,并且使其成为控制程序的主角之一。被害人对恢复性司法的参与,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美国司法部实施的邻里司法中心 ,1974年门诺派教徒中央委员会(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成员与缓刑官员一起在安大略省的基陈纳市(Kitchener)附近组织的“受害人——犯罪人调解”项目,是恢复性司法的第一次尝试,接着在1978年于印地安那州的俄克哈特市(Elkhart)也组建了类似的组织。 1980年在美国有超过80个城市拥有了非正式的纠纷调解项目,六年后也就是198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50个。同时,恢复性司法项目在其他国家也得到发展, 如加拿大是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VORP)的先驱,英国和法国也建立了许多项目,并且在日尔曼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鼓励。在新西兰,被害人被邀请参加的家庭团体会议(FGC)已经以立法的形式成为处理那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主要机制。
(一)基本模式
按照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方式和恢复性司法运作机制的不同,可以将恢复性司法分为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1.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简称VOM模式)
由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缺少对被害人的应有关注,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叫被害人作为证人,被害人就完全被刑事司法程序遗忘了。因此,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OM)就是针对此弊端所产生的改革运动,它将被害人和犯罪人聚集在一起,由一名调解人主持双方会谈和负责推动程序,在会谈中双方开诚布公,被害人讲述他们的受害体验和犯罪对自己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犯罪人解释他们究竟对被害人实施了什么伤害和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并且回答被害人提出的问题,在双方讲述完毕后,由调解人帮助双方确定使事情好转的方法和手段。
尽管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VOM)在具体形式上有些细微差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结构,一般说来包括四个阶段——进入阶段(Intake)、调解准备阶段(Preparation for Mediation)、调解阶段(Mediation)和后续阶段(Follow-up),具体说来: (1)在进入阶段,进行一个预先筛选,由一个经过训练的社区自愿者或职员人员担任调解者进行审查,对那些双方表示愿意协商和相互之间没有明显敌意的被害人和犯罪人接受进入该程序;(2)在调解准备阶段,调解者与被害人和犯罪人分别谈话并确定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如果调解者感到还没有和每一方建立信任和友善的关系,那么这个案件就会被送回去法院;(3)在正式调解阶段,双方讲出自己经历的事实,详细地进行商议,理解彼此的处境,通常达成一项赔偿协议或工作命令,产生适当的解决方法。如果达不成协议,案件同样被送回法院;(4)在最后的后续阶段,监督犯罪人进行工作或进行赔偿,确保协议的履行。
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把被害人和犯罪人进行面对面(face-to-face)的联系,让被害人直接参与,赋予其对于结果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权,这样就可使被害人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重要性,并使其受到很好的治疗,以便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犯罪者也被希望为他们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结果,并且有机会恢复破裂的关系。在VOM模式中,引入社区的参与以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恢复性司法项目在具体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普遍地试图通过增加一些社区参与保持VOM的目标。社区成员被认为是非直接当事人,因为他们可能害怕将来成为被害人,他们可能希望重新确定犯罪行为违反的标准,吸收犯罪保险成本,当犯罪发生时有所反应。而且,他们经常被看作带来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联系”的能力,当其试图修复犯罪伤害时提供支持。”
VOM调解程序以当事人的自愿参加为前提,主要适用于第一次或第二次犯罪的青少年犯人中,也有些项目适用于杀人、抢劫、强奸等重罪案件,但是对于一些毒品、腐败和针对国家的犯罪等“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并不适用。近年来,VOM调解模式仅在美国就处理了16,500件案件,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125个项目; 并且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可,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新西兰毛利人的会商模式(Conference)
在新西兰,毛利人(Maori)有着自己传统的内在的独特刑事司法制度,尽管新西兰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法律受到英国的深刻影响,但毛利人的恢复性司法依然存在,形成了两种司法模式并存“一国两制”情况。
在毛利人地区,一些像盗窃、袭击之类的轻罪和一些更严重的性犯罪等都被交由当地的年长者处理,只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案件才找到警察。大概的程序是一方召集家庭成员在一起进行讨论,双方被邀请参加一个“会”(hui),被告人需要作有罪答辩并且不能隐瞒事实,年长者进行教育,对犯罪人及其家庭施加耻辱,经常达到使其流泪的程度。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医治创伤和使事情恢复到“正常”状态。被偷的东西予以返还或者进行赔偿,损坏的东西予以修复,刑罚经常包括犯罪人要进行一定的强制工作等。比如下面的这个案例就体现了该程序的完整过程:
在一个强奸未遂的案件中,一名17岁的男孩在被指称脱掉了一名16岁女孩的内衣裤之后才终止行为。当地毛利人的酋长兰格蒂勒就组织了一个“会”(hui),这名16岁的少女还有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和叔叔、阿姨等都参加了,他们坐在那名17岁男孩的对面。当这名男孩作有罪答辩后,主持会议的一名老年妇女就开始发言了,她痛斥这个男孩行为的罪恶,说他侵犯一名年轻的女子,既触犯了神的禁忌,也给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带来了耻辱。不一会,这名男孩和他的家人都流泪了。
接下来,对这名男孩的惩罚就是要求在12个月内无论何时有婚宴,该男孩的家庭都要供应肉和蔬菜。此外,他还必须把该会议室粉刷一遍,更换已经不能用的护墙板和瓦楞铁。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该会议室属于他们共有,这名女孩和其家庭成员就在男孩家庭人员工作的时候为其提供饭菜。两方走在一起显示出和解的倾向。最后,他们平静下来一起修理餐厅和周围的栅栏。整个程序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上述毛利人司法的事例中,没有警察的介入,这名女孩在程序中受到正当的对待,其创伤受到医治,那名男孩也没留下犯罪记录,体现了一种恢复、治疗和协商的精神。 “建立毛利人司法是为了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它不是对犯罪人落井下石,而是重视受到伤害的人——它谴责那些说社会是被害人的人。是我,而不是社会受到伤害。毛利人司法减轻被害人的责任,而将其施之于应该承担责任的犯罪人。” 毛利人司法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为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提供帮助与治疗。
3. 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模式(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s,简称VORP)
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VORP)是让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协调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恢复性程序,会议的通常结果是达成一份犯罪人以某种方式赔偿被害人的协议。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从与被害人的会见中受益。美国的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模式产生于安大略省,与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和教友派信徒(Quakers)相联系,被称为是“宗教性浪漫”。 在一些司法区,被害人-犯罪人和解项目的参与工作地如此的好,以致成为缓刑或者假释的一项条件。
4.青少年犯罪的恢复性项目
青少年犯罪是恢复性司法重点救助的对象之一,代表性的项目有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模式(Family Group Conference,简称FGC模式),和英国最近的犯罪座谈小组(Youth Offender Panels,简称YOPs)。
在新西兰,1989年通过了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法(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ct),进行了深入的司法改革,在阿尔提拉(Aotearon)地区兴起了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团体会议模式(FGC)。在家庭团体会议中,由一名协调人主持,地点通常由犯罪人的家庭来定,但有时也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朋友的家里或教堂等。在大多数案件中,一旦青少年犯罪人被警察逮捕或指控,他们就可以适用非正式程序。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对各国的恢复性司法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家庭团体会议经常首先由犯罪人的家庭启动,先是进行祈祷,接着由协调者介绍当事人,宣读警察提供的事实概要,这可以为被告方提出质疑和当场予以修正。如果被告人否认指控的内容,那么案件就会被转移到少年法院举行听证,当然一般来说被告人是承认有罪的。接着由被害人陈述,通常是阐述犯罪对其生活造成的严重不良影响,这通常会令犯罪人感到吃惊,使其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生活产生的严重妨碍。这种眼球对眼球(eyeball to eyeball)的见面是非常重要的,它使青少年犯罪人不再冷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被害人;也为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以及接触社区,掌握对程序的一定控制权。
犯罪人在认识到自己造成损害后,通常会自责和道歉。接下来讨论合适的惩罚问题,这时被害人的观点又是很重要的,他们拥有否决的权利。被害人一般会选择要求改正错误、修复损害、道歉和让犯罪人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做一定的工作。警察和协调人接着会陈述他们认为合适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阶段家庭成员是退场的。当家庭成员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家庭的代表站出来宣布就惩罚问题的决定,一般来说都会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在该会议中,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他们对程序的感受和与他们分享思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通常都会说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犯罪人。
家庭团体会议将对案件决定的权力由国家转移给了当事人及其家庭,让犯罪人对其自己的行为直接承担责任,让被害人参与到程序中来,并对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被害人被鼓励参加团体会议,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讨论决定适当的惩罚措施,这对被害人从被害状态中的康复具有重要作用。
同样,在英国,针对报应型司法的失败,兴起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 1998年通过了犯罪和无秩序法(Crime and Disorder Act),接着成立了青少年司法委员会(Youth Justice Board)和青少年犯罪组(Youth Offending Teams);1999年工党政府通过了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成立了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uth Offender Panels,即YOPs),在青少年恢复性司法上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s)会议的地点通常在离犯罪人和座谈小组成员住所都比较近的地方举行,至少包括两名经过青少年犯罪组(YOT)训练的社区志愿者参加,其中一名来主持会议。在法院发出命令后的15个工作日之内要举行第一次YOP座谈会议,年龄在16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者及其父母,还有被害人及其父母,社区成员等都参加座谈,程序不像法院的那么正式。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通常会和犯罪人达成一项协议,要求其为被害人和社区服务和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继续犯罪。如果达不成协议或者犯罪人拒绝签署协议,那么他将会被送回法院重新审判。青少年犯罪座谈小组(YOP)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并且负责监督犯罪人遵守和履行协议,如果规定的期限达到后没有违反的情况,那么按照1974年犯罪归复法的规定他将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二)主要特征
从上面列举的几种代表性恢复性司法项目中,我们可以发现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有如下几点共同规律:
第一,恢复性司法项目的运作都是由一名作为第三方的调解者主持。这些调解者一般来自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社区,是自愿者性质的,他们往往经过一定的训练,也有些调解者是恢复性项目的职员。整个会议讨论的进行,由这名中立的调解者主持,保持讨论集中不偏离主题,当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并且负责监督各方的行为。
第二,把纠纷诉诸社区而不是国家。尽管大部分恢复性司法项目处理的案件是由检察院、法院等刑事司法机构介绍或者引进的,但纠纷的解决都在社区,它是一种“邻里纠纷解决”(neighborhood dispute resolution)。社区介入恢复性司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社区的代表直接介入,例如作为家庭团体会议的调解者、青少年司法座谈小组的成员等参与进来,这样被害人与犯罪人纠纷的解决就不仅诉诸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庭,而延伸到整个社区;二是非直接的形式,即社区是每一具体犯罪的非直接受害人,整个社区作为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进来。
第三,被害人与犯罪人通常是相互认识的。他们经常是邻居、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即使是商店老板和顾客也可利用这样的项目),纠纷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彼此熟悉,这种相互熟悉对于达成一个妥协协议是有益的。
第四,遵循自愿性原则。一是程序的启动要求被害人和犯罪人完全自愿,纠纷双方必须同意通过该项目来处理问题,如果一方拒绝参加,那么该纠纷就会回到更正式的法律诉讼领域;二是结果的自愿,基于双方的同意产生结果,在调解者的帮助下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的决定,当讨论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案件将会被送回到法院处理。
最后,程序的非专业性和非正式性。程序不是由法官引导,也没有律师的参与,没有法律的职业化色彩;程序没有固定的模式,正当程序的概念和证据规则都不适用,调解者可以按照他或她认为适合的方式自由地举行每次会议,“该程序提倡讨论而不是严格的事实发现” 。
二、 从复仇到和解: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对一系列司法概念和哲学观点引起挑战,具体说来就是涉及到从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到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从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到社区司法(Community Justice),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Reintegrative Shaming),和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到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司法模式的转换。从整体上看,“我们需要发现一种哲学,能够从惩罚到和解,从对犯罪人报复到对被害人医治,从疏远和粗暴到社区与全体,从消极和破坏到治愈、宽恕与同情。该哲学基础就是恢复性司法。” 因此,恢复性司法的引入对于保护被害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系列理念的转变和一种新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从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到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
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就是追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效果,追求被害人复仇心理的实现和愤怒仇恨的宣泄,追求犯罪人被判处监禁刑罚,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但在整体上看,在报应性正义理念指导下的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是不成功的。因为:
首先,在报应正义观念的影响下,刑事司法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强调的是复仇(Vengeance)、该当(Desert)和刑罚(penalty)。这种报应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实现报应和惩罚为主要目标,认为“惩罚能有效地谴责犯罪行为和要求为其报偿.法院的量刑表达了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反对和决定对它的惩罚,” 因此,它本质是一种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
而惩罚是一种法律上的暴力,却不是唯一和最好的方式。“我们是一个惩罚性的民族,我们正被迫接受我们复仇愿望带来的结果。”“在目前的制度下,所有的权力被交给国家——法官、警察、监狱看守人。被害人和犯罪人被遗忘,他们感到无能力;因为被害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没有给犯罪人提供任何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和举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相反,现有的倾向仅仅是惩罚,承担责任和使事情再次变好这一对概念被忽略了。被害人和犯罪人被否定了权利和责任。” 犯罪人通过对国家承担抽象的刑事责任,而规避了对被害人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
其次,报应性司法的成本非常高昂。一方面整个刑事程序的成本很高,诉讼周期很长,比如为了追诉一个盗窃200美元的案件,可能要耗费5000美元的刑事司法资源,同时当事人请律师也要花很大的费用;另一方面是监狱的成本高昂,国家花了千百万的钱财建造新的监狱和维持旧的监狱,比如在新西兰,看管一个需要采取最大安全措施的犯人国家每年要花$70,000,即使对于需要采取最小安全措施的犯人每年也要花$24,000—$35,000,这相当于每周每个犯人要花$1500,也就是大约一天$200。 同样在美国,自1980年到1996年花费在监狱上的成本从每年70亿美元增加到了380亿美元,增加了4.43倍,从1992年开始有四个州花在监狱上的费用每年超过10亿。 可见报应型司法的成本是多么高昂,而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却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
再次,作为报应型司法主要体现的监禁刑流弊颇多,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监狱成为整个国家藏污纳垢的地方,按照1987年新西兰天主教教主会议的描述,监狱是“国家血液中的毒药”,“他们认为监禁是对人类尊严的公开侮辱,应该部分的或全部的,当前的或者永远的对那些受到破坏的犯人负责。他们发现很难想象出一种比这种花费公共资金更具有破坏性或浪费性的方法了。” 吉姆·康瑟丁(Jim Consedine)列举了监禁的十大毒害:(1)被监禁的大多是穷人;(2)监禁使人变的更残忍;(3)监禁破坏了犯人与家庭、社区的关系;(4)监狱内的吸毒问题严重;(5)监狱成为训练新犯罪成员的基地;(6)监禁达不到阻吓他人犯罪的效果;(7)犯罪与失业相联,并且是恶性循环; (8)程序是选择性的和歧视性的;(9)监狱内非常高的自杀率;(10)警察等刑事司法人员的腐败。康瑟丁甚至激烈地批评,认为“监狱是一个走到尽头的措施。从社会上、道德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它都是正在吞噬人类社区心脏的癌症。它像奴隶制度一样有害和陈旧。”
而监狱里面会形成一种亚文化,使人感到厌倦、烦闷、暴力、浪费和压制,“监狱可以改变人们,但可以使一些人变得更狡诈,由于其惩罚的性质,监狱除了将犯人变成社会的终身负担外无能为力。”而绝大多数犯人不是杀人犯、强奸犯或无可救药的坏人,他们主要涉及的是饮酒、毒品和汽车犯罪等,年龄大多30岁以下,未能完成学业,缺少与家庭和社区的强有力联系,急需要接受教育。
最后,报应性司法的实施效果有限,犯人重新犯罪率高。比如在新西兰,大概2/3的人在判刑两年之内又回到监狱。犯人的重复犯罪率高,其原因可能有:一是监狱完全封闭,与外界隔绝,内部条件恶劣,使犯人的心灵和精神扭曲,加强了思想畸形和对生活的不真实期待,从而再犯;二是犯人之间相互“学习”,交叉感染。“监狱长期以来被称作‘犯罪大学’,是训练新朋友和新的团伙成员,学习新的犯罪技术,以及作出新的犯罪计划的主要地方。”三是社会对犯罪人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不接受以前被监禁过的人,犯人被释放后60%处于失业状态,从而诱发新的犯罪。
而犯罪人重新犯罪率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被害人,更多的伤害,更多的痛苦和对一些人更多的恐惧。“恢复性司法的提议者不赞成更严厉和更肯定的处罚来威慑或者使重复犯罪者丧失能力。他们很可能相信,把犯罪者放进监狱加强了而不是阻止了其犯罪行为,并不能为犯罪者提供他们成功重新回到社会所需要的技能。”
可见,报应性司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惩罚,成本高昂,对犯人的改造非常不力,重新犯罪率高,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A Dead-End Street)。“报应和复仇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方法和刑罚的核心。他们在一个饥饿的国家形成了一种昂贵的、粗暴的、令人失望的和浪费的选择,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结构性的非正义。”因此,报应性司法的哲学基础是破产了,就像新西兰基督堂市律师Wolfgang Rosenberg所说:“……公众需要报偿,这说明我们仍接近于野蛮状态。当复仇终止的时候文明才开始。”
而与报应性正义相对称,笔者称之为“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在恢复性正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恢复性司法则强调对被害人、犯罪人进行修复和赔偿。可以说,报应性正义追求的是被害人复仇心理的实现,恢复性正义则体现的是被害人的宽恕心理和要求赔偿的心理;报应性司法关注的是“我们如何惩罚犯罪人?” 而恢复性司法则关注“我们如何修复犯罪造成的损害?”在恢复性司法那里,不仅要指出犯罪人的错误,而且要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协调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关系,重建社区的安宁与和谐。
1990年英国“犯罪,司法和保护公众”的白皮书中,就认识到了报应性司法的弊端和在发挥阻吓作用方面的局限性,该白皮书鼓励对被害人的赔偿,发展出一种单位罚金的制度,提高对监禁社区为基础的选择,“这比监禁刑对被害人、公众和犯罪人更有利”,“它给法院以新的权力,可以结合使用补偿、监督和罚金等刑罚,提升了社区服务命令和缓刑作为对监禁刑的替代。它要求法院在作出监禁刑之前必需确信罪行严重到相当的程度,监禁是为保护公众避免更严重的伤害所必需.法院也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 恢复性司法认为,对犯罪的正确反应不是报应和惩罚,而是恢复因犯罪而造成的各种伤害;真正的负责不是消极地接受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地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加强犯罪预防作用。
恢复性司法与报应性司法的主要区别有:
报应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
犯罪被认为是孤立的个人反对国家的斗争 犯罪被认为是个人对个人的侵犯
强调惩罚、谴责,关注的是“是不是他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罚”,因而是回顾性的 强调解决问题,关注的是“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如何消除犯罪造成的影响”,是前瞻性的
对抗型的关系和标准化的过程 合作型的关系和非正规的,具有很大弹性的过程
为了报应和威慑而强行处罚 为了和解与恢复而协商、赔偿
正义被定义为目标和过程,强调规则的公正 正义被理解为良好的关系和理想的结果,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
刑罚被认为是一种恶害,刑事司法是以恶制恶 具有建设性和恢复性的措施去修补犯罪造成的损害,以消除犯罪形成的恶
社区地位边缘化,在理论上被抽象的理解,为国家所代表 社区发挥主导作用,调解纠纷,消除犯罪的影响
鼓励对抗性、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和个人主义 弘扬社群主义,强调集体价值
司法过程体现为国家和被告人的关系,被害人没有主体地位,犯罪只是被动地接受刑罚 司法过程体现为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通过协商讨论对犯罪的解决办法,被害人的物质精神要求得到尊重和承认,犯罪人被鼓励积极地面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并尽力消除这种损害
犯罪人的责任被定义为接受刑罚处罚 犯罪人的责任被定义为理解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并使因犯罪而恶化的情况好转
犯罪仅被视为对法律的违反,全无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维度 犯罪被全面理解,包括道德、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
犯罪人对国家负有“债务” 犯罪人对被害人和社区负有责任
针对的是犯罪人的行为 针对的是犯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
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带来耻辱 通过鼓励犯罪人积极地承担责任而消除犯罪带来的耻辱
既不鼓励犯罪人悔罪,也不鼓励被害人谅解 鼓励犯罪人认罪和道歉,鼓励被害人谅解
依靠专业人员的运作 依靠当事方的积极参与
(二)从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到社区司法(Community Justice)
国家司法(State Justice)指的是以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为基础的刑事司法,这种刑事司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生纠纷后更多地诉诸社区和私力救济,国家远没有达到现在如此高的权威,按照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的观点,“综观西方的大部分历史,犯罪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犯,更像那些被视为‘民事’的冲突和错误。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候,人们认为主要的反映必须是如何使事情变得更好;赔偿和补偿非常普遍,或许是标准的形式。犯罪产生了义务和责任,这通常需要通过协商的程序予以承担。复仇的行为可能发生但并不是很经常,复仇的功能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被害人和犯罪人在这种程序负有责任,社区也要承担责任。国家也有作用但是受到限制的,只在必需时按照被害人的愿望发挥作用。” 那么是何因素促使社区司法让位于国家司法,国家取得了刑事司法的主导权呢?
对此,天主教大赦年文件中作出了阐释,认为直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君主制度的巩固之前,被害人经常是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诺曼第人入侵的时候发生了模式的转变。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子孙为维护政治权力必须与男爵和其他权威斗争,他们发现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法律程序在确立他们对一些长期事情上的主导权和增加政治权威上是一个高度有效的工具。为了达到该目的,威廉的儿子亨利一世在1116年发布了亨里西法(Leges Henrici),创造了“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这一理念,确立了王室对于违反该法的纵火、抢劫、谋杀、伪造货币和暴力犯罪等特定犯罪的管辖权。对于那些违反了“国王的和平”的人就是反对他们的人,因此国王就成为这种犯罪的主要被害人,就在法律上取代了实际被害人。实际的被害人在程序中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国家和犯罪人被留为主要的关注主体。
这种国家司法的观念,认为把刑事司法权交由国家进行垄断,有助于避免复仇和避免扩大社会暴力,刑事司法变成将来导向的,关心让犯罪人和潜在的犯罪人遵守法律,而不是让他们弥补过去的罪行。赔偿由于是过去导向的和关注于被害人,逐渐被废除;本应支付给被害人的金钱也被作为罚金支付给国家。这种完全忽视被害人的地位、视惩罚为主要意旨的国家司法,按照挪威犯罪学家尼尔·克里斯特(Nils Christie)的话说,国家通过法官、检察官等“治疗人员”和律师,“偷走了直接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不仅取走了被害人的直接补偿,而且剥夺了被害人及其社区参与、更充分理解和标准区分的机会”。
恢复性司法事实上对国家垄断权的合法性提出置疑,认为犯罪主要是对个人的侵犯和社区安宁的威胁,而社区在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回归社会上发挥至关重要的地位。这里就涉及到“国家”与“社区”的二分法问题,社区(community)又包括地域社区和熟人社区,前者指的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人们组成的一个小社会,后者指的是有共同兴趣和爱好,彼此熟悉的人们组成的交往圈。由此社区被纳入到恢复性司法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域社区因犯罪受到了影响;二是熟人社区与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关系特别,关系到恢复性司法的过程和结果。 在“社区”和“国家”之间暗含的区别贯穿于恢复性司法理论:国家司法是强制性司法、惩罚性司法和等级性司法;而社区司法是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包含了从国家权力向社区权力的转移,他们代表了一种向往,即通过社区提高市民权利和使司法变得更加可以接近、有效和公正,社区的福利和恢复到和平与和谐的状况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恢复性司法也就等同于社区司法。社区司法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取代犯罪概念中的国家司法形式,把一体化赔偿、协商、治疗和宽恕等理念融入到刑事司法中。与国家司法相比,社区司法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社区司法有助于恢复被害人和社区的良好关系,促进被害人的社会归复。让被害人、被害人的亲属,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社区成员参加进来,通过面对面的会谈和讨论,被害人能够收到关于犯罪的信息,表达自己因犯罪受到的影响,有效的控制程序的结果,从而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恢复。同时,社区成员有权利参与处理社区中发生的案件,可以使其避免对犯罪的恐惧,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增强集体感和荣誉感,有助于社区的团结安定。
其次,社区司法有助于节省国家司法资源,增加社区资本。与上文列举的报应性国家司法的昂贵成本相比,社区司法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如新西兰的家庭团体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e)导致了较低的法院出庭率——在1987年到1996年间几乎降低了2/3,较低的监禁率——在1987年到1996年间,降低了50%以上;犯罪人如能合作和履行社区服务,就可完全避免被监禁,从而大大降低了监狱的成本;被害人、犯罪人不需要请律师,也节省了律师费用等。
最后,社区司法有助于犯罪人的改造。在社区成员和犯罪人、被害人家庭成员及其亲属的参加下,犯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时,经常会倍感耻辱,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当看到被害人的伤痛和凄苦时,犯罪人经常后悔不已,主动进行赔偿;在看到社区成员对自己的宽容和支持后,犯罪人则经常深受感动,表示积极为社区做有益的事情,从而使犯罪问题在社区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三)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
重新融合性耻辱(Reintegrative Shaming)是指在惩罚谴责犯罪人,让其承担耻辱性后果的同时又保持着对犯罪人的尊重,它是把犯罪人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来对待的,注重犯罪人与社区的联系,在宽恕、协商的氛围中达到犯罪人的社会归复;而烙印型耻辱(Stigmatic Shaming)追求的是惩罚,通过肉体的或人身自由的限制(如监禁)将污名烙在犯罪人身上,使犯罪人与普通社区成员相区分,从而使犯罪人的社会归复非常困难。从整体上看,重新融合性耻辱与恢复性司法相联,而烙印型耻辱则是传统报应性司法的核心要素。
按照马凯(Makkai)、托尼(Toni)和布雷斯韦特(Braithwaite)的观点,重新融合性耻辱具有以下四项特征:一是在保持对行为尊重的同时谴责错误的行为本身,并且和谴责相伴随的是对犯罪人的支持、关心和帮助;二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使行为人感受到社区对他的行为的态度和评价,并且这种形式越郑重,参加越多,犯罪人感受到道德压力就越大,来自犯罪人熟悉和信任的人的谴责越多,犯罪人越容易产生耻辱感;三是在谴责的同时包含着鼓励和接纳,支持行为人改正错误,作一个积极的成员融入社区;四是避免给行为人贴上恶人、犯罪人的标签,不将行为人类型化为社区的破坏者,而是承认每一个人身上都蕴涵着积极的价值,都可以对社区,对他人有所贡献。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1995年举行了融合性耻辱实验项目(Reintegrative Shaming Experiment——RISE) ,在被害人方面访问了232个人,一部分是18岁以下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的有个体被害人的财产犯罪,二是30岁以下的犯罪人实施的暴力犯罪,对于严重的可起诉的犯罪,性犯罪和家庭暴力被排除。采取调解形式,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召开讨论会,通过让犯罪人直面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促使其产生耻辱感。这些主体一半被分配到恢复性司法组,一半被分到法院组按照传统刑事司法程序进行,最后分配到恢复性司法组的人员产生了较为积极的结果。
(四)刑事司法模式的变革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是以保护被告人为中心的模式,强调正当程序,强调对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和不受非法搜查、扣押的权利等一系列宪法性权利的保护,被告人由于其处境劣势的弱者地位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司法的关注。
然而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模式下,推崇国家的权威,由于它关心法律为什么被破坏和如何阻止其再次被破坏,所以它主要集中于犯罪人而不是被害人。被害人被完全边缘化,成为无足轻重的普通证人,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叫被害人作为证人,被害人就完全被刑事司法程序遗忘了。被害人充满巨大的痛苦而没有治疗,仅仅被作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这完全是一种国家决定型的犯罪处理方式。
而恢复性司法则使被害人成为司法体制的中心,强调被害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维护被害人的尊严,被害人对于最终结果拥有完全的否决权。它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其背后的理念是让对立的双方一起设计出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合适方案,这有利于改善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消除犯罪的不良影响 。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零和理论”问题。所谓“零和理论”(zero-sum),就是指一方的损失造成另一方的获益,或者说一方的获益是另一方的损失产生的,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那么,在被害人的权利和被告人的权利之间,能否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或者说形成一种双赢(win/win)的局面呢?调查结果显示,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普遍的。
例如,被害人对部分事实的承认,有可能就是被告人的获益,被告人与原告人面对面的诚实的对话和协商,完全可以使纠纷在协议的范围内解决。斯辰芝(Strang)建议在恢复性司法中,举行一种议程是很宽的程序,试图使其中一方的所得也有利于另一方;她把成对的问题相对比——例如犯罪人理解其他人是怎么感受的吗/被害人感到道歉是真诚的吗?——如果两者大多数回答是积极的,这被分类为双赢。大多数情况是如此的,比如在感情上,4/5的家庭会议都比法院在提高移情作用上明显的高(因为恢复性司法完全考虑感情,而法院则倾向于排除感情或者仅仅是利用感情来作为试图确保或避免定罪的工具),同时在信任警察和尊敬法律方面也都明显好于法院,在只关于协商会的问题上,大多数的问题也显示超过70%或80%的双赢,由此她得出结论说,“恢复性司法理论在所有法院受到强有力支持,在家庭会议上双赢是普遍的,而在法院司法上双输(lose/lose)是普遍的。”
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与被告人的权利可以完好的协调,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它提供一个更人性化,“更温暖的纠纷解决方式”,体现了一种建立“社会化法院”的努力;恢复性司法不仅是以被害人权利为中心的司法,它还是一种完全“当事人主义化”的,有利于诉讼各方的新型司法。
可见,从总体上来看,恢复性司法被认为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制度:被害人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赔偿获得补偿,在案件的处理中可以发表意见,成为处理犯罪人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犯罪人被认为要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并且要服从一切可能的处理,他们作出改进并被提供协助,以便减少将来再犯的机会;社区也可以通过犯罪人支付或者服务的方式获得补偿,同时社区还可以被用来协助被害人,让犯罪者工作和寻求消除犯罪的原因;国家采取这种方式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协助,将会对所有各方提供公正和衡平的程序。在本质上,“恢复性司法寻求把所有各方放到相互协助的谈判桌上。每个人怀着需求而来,带着某种程度的满足而归。”
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恢复性正义,而不是报应性正义,它是一种社区司法,而非国家司法,通过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使犯罪人得到教育,被害人得到康复和赔偿。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图表显示:
A.恢复性正义 恢复性司法 社区司法 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 被害人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 | | | |
B.报应性正义 报应性司法 国家司法 烙印型耻辱理论 被告人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出处:原载于作者个人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