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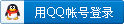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王超 周菁
案情简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弃置的微型面包车内发现了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的干警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的尸体。而此刻正在焦急寻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经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经过70余天的侦查和刑讯之后,杜培武终于招供,并“揣摩”审讯者的意图编好了杀人现场,但是作案的凶器——王俊波携带的一支七七式手枪却一直没有下落。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权利终身。经过二审,云南省高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0年6月17日,杀害“二王”的真凶杨天勇在另一案件中落网,而那把作为杀人凶器的手枪也赫然出现……
这起举国震惊的冤假错案虽然随着对肇事者的处理[ii]已经真相大白,但其蕴含着丰富的法律问题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笔者单从证据学的角度对本案引发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镜头一:测谎
在杜培武招供之前,也就是1998年6月30日,他被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检测,“中院一个20出头的小女孩,当时因为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伸手就扇了他两耳光”。在这种情况下,杜培武坦然面对测试,但在经过一整天的测试之后,却得出了“说谎”的结论。于是,案件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思考一: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中,杜培武之所以被屈打成招乃至酿成惊世冤案,可以说测谎仪“功不可没”。有人甚至尖刻地指出测谎仪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iii]杜培武案无疑再次给那些对测谎仪仍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测谎仪虽然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但发展速度相当快。据悉,自从90年代初研制出了第一台测谎仪之后,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北京、上海、云南等20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配置了各种类型的心理测试仪100多台,总计办案达1000余起。尽管如此,究竟如何评价测谎结果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争论迄今为止也从未停止过。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仪属于技术侦查手段,测谎结果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分析通过仪器记录的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所做出的判断结论,应具有证据能力,因而可以作为诉讼证据适用。[iv]其次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结果不是独立的诉讼证据。因为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形式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是与案件的事实有客观、直接的联系,而测谎仪是对涉案人身体的各种生理参量的测试,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v]最后是“有限肯定说”。该观点虽然反对将测谎结果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认为只要正确运用测谎结果,就能相对缩小侦查范围,赢得侦查时间,及时获得其它证据,为采取其它侦查措施提供有力支持。[vi]
尽管从对多种生理参数的收集看,测谎仪是一种科学的仪器,测谎证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测谎仪的运用要受到四个主观因素的影响:操作员的经验、科学的程序、嫌疑犯的个性因素、测谎时的周围环境。例如,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测试对象有时可能对测谎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导。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所言:“最难以对付的是找出那些惊惶失措的怀疑对象,而他们恰恰又是没有说谎的人。”[vii]尤其是对测量结果或图谱的分析以及测谎过程中问题的设计等,都必须依靠测谎人员,而测谎人员的经验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测谎结果的好与坏。但是,即使最有经验的测谎员也会产生错误,如1979年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弗罗德?费谋杀案。[viii]由此可见,测试结果并不象迷信者认为的那样神奇,测谎证据的作用只不过是表明被测试人说了真话还是撒了谎而已,并不能回答被测试人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了被控罪行,所以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戴维?莱恩说:“测谎器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测验本身可能引起的表面心情激动和情绪不安,这同主持测验的人想要得到的结果几乎毫不相干。”故测谎证据必须与其它证据结合起来进行审查判断。否则,它在测试别人是否说谎的同时,它自己可能也在“撒谎”。
因此,我们对测谎仪的功能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该持慎重的态度,而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某种不恰当的期待。正因为如此,测谎仪大行其道的美国最近也不得不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今后可以不将测谎结果作为证据使用,也可以宣布对测谎结果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在德国,最高法院也曾就刑事诉讼中能否应用测谎仪作出裁决:测谎仪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ix]
然而测谎仪的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恰当地被放大,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测谎仪屡建奇功的报道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一旦有了这种先进技术,撒谎者便遇上了克星,违法犯罪分子再也休想瞒天过海,大有一测即灵的架势。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无论测谎仪有多先进,都难以有效的区分惊惶失措的无辜者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测谎者。其次,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测谎结果即使证明测试对象在说谎,也并不必然反推其真正实施了犯罪行为。再次,测谎结果属于或然性判断,一旦对其奉若神明,则将冒极大风险。最后,测谎仪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无论是经验方面,还是技术条件方面,甚至理论方面均存在不足,贸然推行测谎仪可能对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镜头二:逼供
从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思考二: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的良方?
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有关刑讯逼供的报道屡见不鲜,杜培武案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在本案中,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这同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
首先是立法上的原因。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对其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⑵我国法律没有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而有效的规定。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而我国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因为果实虽系毒树所生,但不能因此殃及池鱼从而否定果实的价值。正是由于我国对果实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暧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3)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一些关键性救济权利,如沉默权、律师讯问在场权等,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薄弱可能导致刑讯逼供乘虚而入。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的原因。⑴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⑵长期以来,公检法三机关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导致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相互独立、互不隶属,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难以建立,法院的权威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使审前程序脱离法院的司法审查轨道。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让法院严格依照法律对刑讯逼供进行公正处理还存在极大障碍。⑶我国侦审中断式的诉讼模式[x]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般情形下,程序的连贯性表明,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程序无效或者程序正义性和合法性的缺失。但是在侦审中断式的诉讼模式的指导下往往导致侦查程序的严重失控,而侦查恰恰是诉讼程序中最需要控制的。缺乏控制的侦查程序极易产生刑讯逼供。
最后是其他原因。如:⑴我国某些侦查、审判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固有惯性使他们常常坚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如果对这个公式缺乏相关证据足以认定,刑讯逼供便是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并对其进行定罪的捷径。⑵我国公安机关往往以破案率等数字化的形式来对侦查活动进行评价,这往往给侦查人员带来了极大压力,导致一些急功近利的侦查人员做出刑讯逼供的行为。⑶社会治安状况的压力常常迫使公安机关加快办案力度以保“一方平安”,[xi]公安机关在“逼急了”的情况下可能不惜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多种非法手段加快办案进度以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
针对上述原因,为防治刑讯逼供,应进行“综合治理”。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并且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其中最根本的便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砍掉“毒树”,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其次,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将侦查的重心放在收集证明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上,而不能放在收集被告人的口供上,实行“由供到证”。再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应的“对抗”侦查的权力,例如沉默权、律师讯问在场权、对通过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的质证权等等。最后,做好警察培训工作,把好警察入口关,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
镜头三:警察作证
在昆明中院的第一次庭审中,控方出示了用“高科技”手段取得的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并且指派了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思考三:警察能否出庭作证?
对此,在国外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xii],因为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均像其他证人一样在法庭上宣誓、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然而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少见,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刑侦队或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报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等”[xiii]。即便偶尔有辩护律师坚持要求法院通知警察出庭的,法官要么以“没有先例”搪塞,要么不习惯甚至不太敢“通知”警察出庭作证,难怪龙宗智教授将警察不作证列入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黑名单”之中[xiv]。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杜培武案庭审过程中,控方超乎寻常地指派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可以说是本案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亮点。
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xv]。证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xvi]。首先,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证人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最后,证人是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机关团体、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与其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xvii]那么,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答案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
首先,我国证据立法并未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主要取决于警察是否知道案情。而知道案情有事先与事后知道之分,那么具备证人条件的应是哪一种情况呢?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以及学理上通常将其理解为“事后知道”,因此,他们普遍反对将负责办案的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参加诉讼。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学理上的解释,缺乏法律效力,以此作为执法依据是不恰当的。所以警察出庭作证并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
其次,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0条[xviii]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0条的规定[xix],公诉人应当就物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让辩方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一旦发生争议,根据《规则》第341条的规定[xx],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笔录仍存在争议,公诉人根据需要,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xxi]另外,《解释》第138条亦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然,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
最后,非法证据能否得到排除需要警察出庭作证。《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的规定均表明,我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xxii]但是在庭审之中如何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我们认为,让警察出庭作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因此,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
镜头四:翻供
在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的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思考四: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应当如何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极不统一。如有的法官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法官无奈之下要么自行调查,要么责令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冤假错案。那么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应当如何进行?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回答依赖于对翻供问题的辩证认识,尤其是要正确鉴别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证明力与可靠性。从理论上讲,当庭供述的效力明显优于庭前形成的书面供证。首先,根据直接言词原则,被告人的当庭供述更易于发现真实。其次,从供述形成的条件和环境来看。庭前供述一般是在秘密的、双方非平等对抗的侦查阶段形成的,因此,其真实可靠性要大打折扣。而被告人的当庭供述,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模式至少在形式上更有利于被告人说出真话,再加上有辩护律师“撑腰”,被告人当庭供述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真实基础的。
但是理论上的推论与现实总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效力大小不应一概而论。被告人在侦查审讯阶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其意志最为薄弱的时候,心理防线容易被突破,加之“趋利避害”是人的固有天性,他可能会供认,以求得到宽大处理。但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可能出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或害怕惩罚的心态而翻供。因此,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当庭翻供,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其关键是要从其翻供有无合理性上进行考量,而不能仅从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只关注这种翻供是否有利于控诉的顺利进行。
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应当认为,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休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具体来说,在审查后应当作出如下处理:
1、应当先对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如果其他证据是客观真实的、并能够形成证据链,达到证明标准的,可以利用其他证据直接定案。
2、如果法庭认为其他证据有可能是伪造或者是根据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制作”的[xxiii]或者是非法的,应当责令控方就该证据是否合法进行证明,如果控方不能证明,则应当作出不利于控诉方的推定。
3、如果经过审查之后,控方的其他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且控方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庭前供述和当庭供述的效力大小,即当当庭供述与其庭前供述的效力大小难以评判时,法庭可以根据无罪推定的精神,采纳被告人的当庭供述。
镜头五:举证责任
庭审过程中,当杜培武以刑讯逼供为由进行翻供时,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思考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极不统一。为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均规定:当刑事被告人基于合理的理由提出控方的证据系非法手段取得时,控方就必须举出证据证明控方的证据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的,否则,法官就可以推定控方的证据系非法的而将其排除。如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二、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下获得的——(一)逼供;或者(二)基于他人的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由此可能作出的任何供述,法庭不应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公诉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供述可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上述情形下获得的。三、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法庭可以主动要求公诉方证明该供述不是第二款所述情形下获得的,作为允许公诉方这么做的一个条件……”[xxiv]在日本,法律虽然原则上规定“控辩双方对各自请求调查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均负有举证责任。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固然有责任对其请求调查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证明,被告人对于认定本方请求调查的证据具有能力的事实同样负有举证责任” [xxv],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法律却规定“一旦证据物的收集程序违法已由被告人一方提出时,对搜查、扣押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就落在控方一方”[xxvi]。
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规定的内容并未得到贯彻落实。对此,有人深刻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xxvii]所以,我国亟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由控方即检察机关承担。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诉讼平等的体现。现代刑事诉讼对公正的追求首先体现在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程序框架上。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基础是控辩双方力量上的平等。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机关代表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上讲都远远超过作为公民个人的辩方,因此,为促使双方力量尽可能地接近,立法者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往往需要为控方规定更多的诉讼义务而赋予辩方更多的诉讼权利,而让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
其次,诉讼法理的要求。众所周知,古罗马时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规则一直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原则。该原则表明,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否定的一方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且,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不仅要运用证据证明其实体主张是成立的,而且要运用证据证明其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否则,其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控诉被告人有罪,显系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因而它应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最后,诉讼特点的需要。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不难发现,侦查机关的大多数取证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仅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犯罪嫌疑人无法参与其中,就连拥有一定调查权的辩护律师也不能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实施有效的制约。因此,在取证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让被告人承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是很不公平的。相反,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法律监督权,不仅有义务而且相对有能力证明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是否合法。 注释:
杜培武案件的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郭国松、曾民:《“死囚”遗书》,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23日;段文:《杜培武:我的生活已经全部毁掉了》,载《北京法制报》2001年8月6日焦点周刊。
[ii] 据悉,2001年8月3日,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办理杜培武案的昆明市公安局侦查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期1年、1零6个月缓期2年。
[iii] 参见盛大林:《当心!“测谎仪”可能沦为刑讯逼供的帮凶》,载《检察日报》2001年8月22日第6版。
[iv] 参见宋英辉:《关于测谎证据的有关问题的探讨》,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11期,第20页;王戬:《论测谎证据》,载《法学》2000年第5期,第19-21页。
[v]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李忠诚:《如何看待“测谎仪”》,载陈光中主编:《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9年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第234-235页。
[vi] 参见周智良:《从测谎技术的应用谈“心身证据”》,载《人民检察》,1999第1期,第15页。
[vii] 万扬、杨柳青:《测谎仪:误解与真相》,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23日第13版。
[viii] 当时嫌疑犯弗罗德?费因被测谎仪测出说谎而被以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两年之后,真凶被捕归案。在该案中,五位有经验的测谎专家其中有两位认为他有罪、一位认为不能确定有罪,一个认为这个实验无效,还有一位认为弗洛德说的都是真话,但是少数测谎专家的意见却被采纳,弗洛德被认为有罪。
[ix] 李忠诚:《如何看待“测谎仪”》,载陈光中主编:《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9年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第236页。
[x] 侦审中断式是指侦查和审判分离的、中断的,侦查行为的违法对审判没有任何的影响,也就是侦查的效力减退并必然导致审判效力的折损。
[xi] 例如在杜培武案之前,昆明已连续发生几起枪杀案且多未告破,昆明马上又要举行“99世博会”,从“安定”的大局出发,这起“涉枪涉警”大案再不告破,官方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无疑为刑讯逼供的产生埋下了潜在的伏笔。
[xii] 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xiii]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xiv]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xv]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xvi] 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xvii]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xviii] 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xix] 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xx] 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xxi] 《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xxii] 该两条司法解释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xxiii] 根据供述“制作”证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云南省富源县1995年发生的姚泽昆等四青年被刑讯逼供案便是如此,公安机关在刑讯取得口供后,又制造证据使四人被定罪的案件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xxiv]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xxv] 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xxvi] 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xxvii]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
240331
王超 周菁
案情简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弃置的微型面包车内发现了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的干警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的尸体。而此刻正在焦急寻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经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经过70余天的侦查和刑讯之后,杜培武终于招供,并“揣摩”审讯者的意图编好了杀人现场,但是作案的凶器——王俊波携带的一支七七式手枪却一直没有下落。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权利终身。经过二审,云南省高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0年6月17日,杀害“二王”的真凶杨天勇在另一案件中落网,而那把作为杀人凶器的手枪也赫然出现……[i]
这起举国震惊的冤假错案虽然随着对肇事者的处理[ii]已经真相大白,但其蕴含着丰富的法律问题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笔者单从证据学的角度对本案引发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镜头一:测谎
在杜培武招供之前,也就是1998年6月30日,他被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检测,“中院一个20出头的小女孩,当时因为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伸手就扇了他两耳光”。在这种情况下,杜培武坦然面对测试,但在经过一整天的测试之后,却得出了“说谎”的结论。于是,案件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思考一: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中,杜培武之所以被屈打成招乃至酿成惊世冤案,可以说测谎仪“功不可没”。有人甚至尖刻地指出测谎仪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iii]杜培武案无疑再次给那些对测谎仪仍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测谎仪虽然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但发展速度相当快。据悉,自从90年代初研制出了第一台测谎仪之后,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北京、上海、云南等20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配置了各种类型的心理测试仪100多台,总计办案达1000余起。尽管如此,究竟如何评价测谎结果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争论迄今为止也从未停止过。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仪属于技术侦查手段,测谎结果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分析通过仪器记录的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所做出的判断结论,应具有证据能力,因而可以作为诉讼证据适用。[iv]其次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测谎结果不是独立的诉讼证据。因为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形式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是与案件的事实有客观、直接的联系,而测谎仪是对涉案人身体的各种生理参量的测试,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v]最后是“有限肯定说”。该观点虽然反对将测谎结果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认为只要正确运用测谎结果,就能相对缩小侦查范围,赢得侦查时间,及时获得其它证据,为采取其它侦查措施提供有力支持。[vi]
尽管从对多种生理参数的收集看,测谎仪是一种科学的仪器,测谎证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测谎仪的运用要受到四个主观因素的影响:操作员的经验、科学的程序、嫌疑犯的个性因素、测谎时的周围环境。例如,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测试对象有时可能对测谎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导。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所言:“最难以对付的是找出那些惊惶失措的怀疑对象,而他们恰恰又是没有说谎的人。”[vii]尤其是对测量结果或图谱的分析以及测谎过程中问题的设计等,都必须依靠测谎人员,而测谎人员的经验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测谎结果的好与坏。但是,即使最有经验的测谎员也会产生错误,如1979年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弗罗德?费谋杀案。[viii]由此可见,测试结果并不象迷信者认为的那样神奇,测谎证据的作用只不过是表明被测试人说了真话还是撒了谎而已,并不能回答被测试人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了被控罪行,所以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戴维?莱恩说:“测谎器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测验本身可能引起的表面心情激动和情绪不安,这同主持测验的人想要得到的结果几乎毫不相干。”故测谎证据必须与其它证据结合起来进行审查判断。否则,它在测试别人是否说谎的同时,它自己可能也在“撒谎”。
因此,我们对测谎仪的功能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该持慎重的态度,而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某种不恰当的期待。正因为如此,测谎仪大行其道的美国最近也不得不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今后可以不将测谎结果作为证据使用,也可以宣布对测谎结果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在德国,最高法院也曾就刑事诉讼中能否应用测谎仪作出裁决:测谎仪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ix]
然而测谎仪的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恰当地被放大,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测谎仪屡建奇功的报道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一旦有了这种先进技术,撒谎者便遇上了克星,违法犯罪分子再也休想瞒天过海,大有一测即灵的架势。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无论测谎仪有多先进,都难以有效的区分惊惶失措的无辜者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测谎者。其次,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测谎结果即使证明测试对象在说谎,也并不必然反推其真正实施了犯罪行为。再次,测谎结果属于或然性判断,一旦对其奉若神明,则将冒极大风险。最后,测谎仪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无论是经验方面,还是技术条件方面,甚至理论方面均存在不足,贸然推行测谎仪可能对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镜头二:逼供
从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思考二: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的良方?
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有关刑讯逼供的报道屡见不鲜,杜培武案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在本案中,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这同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
首先是立法上的原因。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对其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⑵我国法律没有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而有效的规定。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而我国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因为果实虽系毒树所生,但不能因此殃及池鱼从而否定果实的价值。正是由于我国对果实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暧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3)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一些关键性救济权利,如沉默权、律师讯问在场权等,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薄弱可能导致刑讯逼供乘虚而入。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的原因。⑴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⑵长期以来,公检法三机关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导致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相互独立、互不隶属,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难以建立,法院的权威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使审前程序脱离法院的司法审查轨道。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让法院严格依照法律对刑讯逼供进行公正处理还存在极大障碍。⑶我国侦审中断式的诉讼模式[x]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般情形下,程序的连贯性表明,程序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程序无效或者程序正义性和合法性的缺失。但是在侦审中断式的诉讼模式的指导下往往导致侦查程序的严重失控,而侦查恰恰是诉讼程序中最需要控制的。缺乏控制的侦查程序极易产生刑讯逼供。
最后是其他原因。如:⑴我国某些侦查、审判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固有惯性使他们常常坚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如果对这个公式缺乏相关证据足以认定,刑讯逼供便是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并对其进行定罪的捷径。⑵我国公安机关往往以破案率等数字化的形式来对侦查活动进行评价,这往往给侦查人员带来了极大压力,导致一些急功近利的侦查人员做出刑讯逼供的行为。⑶社会治安状况的压力常常迫使公安机关加快办案力度以保“一方平安”,[xi]公安机关在“逼急了”的情况下可能不惜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多种非法手段加快办案进度以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
针对上述原因,为防治刑讯逼供,应进行“综合治理”。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并且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其中最根本的便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砍掉“毒树”,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其次,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将侦查的重心放在收集证明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上,而不能放在收集被告人的口供上,实行“由供到证”。再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应的“对抗”侦查的权力,例如沉默权、律师讯问在场权、对通过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的质证权等等。最后,做好警察培训工作,把好警察入口关,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
镜头三:警察作证
在昆明中院的第一次庭审中,控方出示了用“高科技”手段取得的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并且指派了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思考三:警察能否出庭作证?
对此,在国外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xii],因为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均像其他证人一样在法庭上宣誓、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然而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少见,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刑侦队或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报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等”[xiii]。即便偶尔有辩护律师坚持要求法院通知警察出庭的,法官要么以“没有先例”搪塞,要么不习惯甚至不太敢“通知”警察出庭作证,难怪龙宗智教授将警察不作证列入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黑名单”之中[xiv]。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杜培武案庭审过程中,控方超乎寻常地指派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可以说是本案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亮点。
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xv]。证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xvi]。首先,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证人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最后,证人是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机关团体、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与其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xvii]那么,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答案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
首先,我国证据立法并未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主要取决于警察是否知道案情。而知道案情有事先与事后知道之分,那么具备证人条件的应是哪一种情况呢?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以及学理上通常将其理解为“事后知道”,因此,他们普遍反对将负责办案的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参加诉讼。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学理上的解释,缺乏法律效力,以此作为执法依据是不恰当的。所以警察出庭作证并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
其次,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0条[xviii]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0条的规定[xix],公诉人应当就物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让辩方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一旦发生争议,根据《规则》第341条的规定[xx],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笔录仍存在争议,公诉人根据需要,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xxi]另外,《解释》第138条亦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然,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
最后,非法证据能否得到排除需要警察出庭作证。《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的规定均表明,我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xxii]但是在庭审之中如何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我们认为,让警察出庭作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因此,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
镜头四:翻供
在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的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思考四: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应当如何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极不统一。如有的法官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法官无奈之下要么自行调查,要么责令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冤假错案。那么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应当如何进行?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回答依赖于对翻供问题的辩证认识,尤其是要正确鉴别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证明力与可靠性。从理论上讲,当庭供述的效力明显优于庭前形成的书面供证。首先,根据直接言词原则,被告人的当庭供述更易于发现真实。其次,从供述形成的条件和环境来看。庭前供述一般是在秘密的、双方非平等对抗的侦查阶段形成的,因此,其真实可靠性要大打折扣。而被告人的当庭供述,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模式至少在形式上更有利于被告人说出真话,再加上有辩护律师“撑腰”,被告人当庭供述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真实基础的。
但是理论上的推论与现实总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效力大小不应一概而论。被告人在侦查审讯阶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其意志最为薄弱的时候,心理防线容易被突破,加之“趋利避害”是人的固有天性,他可能会供认,以求得到宽大处理。但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可能出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或害怕惩罚的心态而翻供。因此,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当庭翻供,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其关键是要从其翻供有无合理性上进行考量,而不能仅从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只关注这种翻供是否有利于控诉的顺利进行。
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应当认为,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休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具体来说,在审查后应当作出如下处理:
1、应当先对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如果其他证据是客观真实的、并能够形成证据链,达到证明标准的,可以利用其他证据直接定案。
2、如果法庭认为其他证据有可能是伪造或者是根据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制作”的[xxiii]或者是非法的,应当责令控方就该证据是否合法进行证明,如果控方不能证明,则应当作出不利于控诉方的推定。
3、如果经过审查之后,控方的其他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且控方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庭前供述和当庭供述的效力大小,即当当庭供述与其庭前供述的效力大小难以评判时,法庭可以根据无罪推定的精神,采纳被告人的当庭供述。
镜头五:举证责任
庭审过程中,当杜培武以刑讯逼供为由进行翻供时,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思考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极不统一。为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落实,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均规定:当刑事被告人基于合理的理由提出控方的证据系非法手段取得时,控方就必须举出证据证明控方的证据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的,否则,法官就可以推定控方的证据系非法的而将其排除。如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二、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下获得的——(一)逼供;或者(二)基于他人的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由此可能作出的任何供述,法庭不应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公诉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供述可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上述情形下获得的。三、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法庭可以主动要求公诉方证明该供述不是第二款所述情形下获得的,作为允许公诉方这么做的一个条件……”[xxiv]在日本,法律虽然原则上规定“控辩双方对各自请求调查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均负有举证责任。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固然有责任对其请求调查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证明,被告人对于认定本方请求调查的证据具有能力的事实同样负有举证责任” [xxv],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法律却规定“一旦证据物的收集程序违法已由被告人一方提出时,对搜查、扣押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就落在控方一方”[xxvi]。
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规定的内容并未得到贯彻落实。对此,有人深刻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xxvii]所以,我国亟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由控方即检察机关承担。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诉讼平等的体现。现代刑事诉讼对公正的追求首先体现在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程序框架上。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基础是控辩双方力量上的平等。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机关代表的检察机关的力量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上讲都远远超过作为公民个人的辩方,因此,为促使双方力量尽可能地接近,立法者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往往需要为控方规定更多的诉讼义务而赋予辩方更多的诉讼权利,而让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
其次,诉讼法理的要求。众所周知,古罗马时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规则一直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原则。该原则表明,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否定的一方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且,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不仅要运用证据证明其实体主张是成立的,而且要运用证据证明其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否则,其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控诉被告人有罪,显系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因而它应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最后,诉讼特点的需要。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不难发现,侦查机关的大多数取证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仅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犯罪嫌疑人无法参与其中,就连拥有一定调查权的辩护律师也不能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实施有效的制约。因此,在取证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让被告人承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是很不公平的。相反,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法律监督权,不仅有义务而且相对有能力证明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是否合法。 注释:
[i] 杜培武案件的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郭国松、曾民:《“死囚”遗书》,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23日;段文:《杜培武:我的生活已经全部毁掉了》,载《北京法制报》2001年8月6日焦点周刊。
[ii] 据悉,2001年8月3日,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办理杜培武案的昆明市公安局侦查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期1年、1零6个月缓期2年。
[iii] 参见盛大林:《当心!“测谎仪”可能沦为刑讯逼供的帮凶》,载《检察日报》2001年8月22日第6版。
[iv] 参见宋英辉:《关于测谎证据的有关问题的探讨》,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11期,第20页;王戬:《论测谎证据》,载《法学》2000年第5期,第19-21页。
[v]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李忠诚:《如何看待“测谎仪”》,载陈光中主编:《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9年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第234-235页。
[vi] 参见周智良:《从测谎技术的应用谈“心身证据”》,载《人民检察》,1999第1期,第15页。
[vii] 万扬、杨柳青:《测谎仪:误解与真相》,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23日第13版。
[viii] 当时嫌疑犯弗罗德?费因被测谎仪测出说谎而被以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两年之后,真凶被捕归案。在该案中,五位有经验的测谎专家其中有两位认为他有罪、一位认为不能确定有罪,一个认为这个实验无效,还有一位认为弗洛德说的都是真话,但是少数测谎专家的意见却被采纳,弗洛德被认为有罪。
[ix] 李忠诚:《如何看待“测谎仪”》,载陈光中主编:《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9年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第236页。
[x] 侦审中断式是指侦查和审判分离的、中断的,侦查行为的违法对审判没有任何的影响,也就是侦查的效力减退并必然导致审判效力的折损。
[xi] 例如在杜培武案之前,昆明已连续发生几起枪杀案且多未告破,昆明马上又要举行“99世博会”,从“安定”的大局出发,这起“涉枪涉警”大案再不告破,官方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无疑为刑讯逼供的产生埋下了潜在的伏笔。
[xii] 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xiii]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xiv]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xv]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xvi] 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xvii]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xviii] 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xix] 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xx] 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xxi] 《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xxii] 该两条司法解释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xxiii] 根据供述“制作”证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云南省富源县1995年发生的姚泽昆等四青年被刑讯逼供案便是如此,公安机关在刑讯取得口供后,又制造证据使四人被定罪的案件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xxiv]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xxv] 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xxvi] 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xxvii]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