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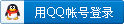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原作者:苗壮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生联合导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邓小平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发1983年1号文件当它(社会)形成一个发达的法典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需要什么,以及这些力量是否想使该法典强固到足以忽视可能遇到的任何阻力的地步。----霍姆斯 是历史建立了这一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相伴随的法律……土地转让的限制、绝对所有权的暂停、不确定继承、诸多将来履行的财产遗赠、私人信托和慈善委托,所有这些法律的名目都只有在历史之光的照耀下才能理解。它们都是从历史中获得动力且必定会影响它们此后的发展。----卡多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本文运用历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过程、约束条件和改革方式,以总结改革的经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改革的理论,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迁必然引发其它相关制度的变迁。同任何深刻的制度变迁一样,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它不但初步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及城乡关系制度改革,并引起了人们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曾经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都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其根本解决也离不开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温故而知新。回顾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是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的,包含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信息。虽然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改革的约束条件也大不相同,从而改革的过程和方式各有特色,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制度及其变迁毕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改革的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也大体相同,因此,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正如本文所归纳、总结的那样,中国的城乡改革与对外开放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合同到政策,从政策到法律的过程,都采取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诱发性改革与强制性改革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局部/部分改革到全局/整体改革,从边际/增量改革到总量/存量改革的方式。因此,总结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总结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在方法上,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类似,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主流方法也是均衡/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之所以如此,理论上的原因主要在于,静态分析更便于利用数学工具;实践上的原因主要在于,至少从现代起,西方社会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基本经济制度大体上是一个给定的体系;其中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大体上是在体制内进行的。这样的现实状况,加上主流方法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及其主要来源—新制度经济学,都偏重于研究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功能,而不是法律/制度变迁的过程/动力。这样的学术倾向,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将批判地吸收、借鉴历史法学、社会法学以及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经济分析法学的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均衡/动态分析的逻辑框架,进而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可以说是本文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改革过程(上):国家与农民的社会博弈1956-1957年,1961-1962年以及1978-1984年,中国农村曾发生过三次包产到户浪潮。这三次浪潮的起点模式都是人民公社制度,目标模式都是承包经营制度。比较研究这三次改革的过程,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改革的规律。人民公社制度的前身是土地改革所确立的土地个体所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对其家庭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及其相关的经营、核算、流通、分配等制度。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国家就开始引导农民发展互助组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是在承认和保护农民个体土地所有权和个体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过渡时期(1953-1956年),国家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经过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入股和土地分红,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按劳分配。到1958年,最终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和演进过程,是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进行限制、剥夺的过程,也是农民对这种限制、剥夺进行抵制和抗争,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并迫使国家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调整的过程,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博弈过程。早在1956年高级社建立之初,四川江津、安徽芜湖、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民就掀起了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浪潮。农民的改革实践还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包产到户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是“非法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和支持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制裁。高昂的改革成本使得包产到户的第一次浪潮迅速退潮。人民公社制度使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限制、剥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范围达到了公社一级(相当于乡级),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联社一级(相当于县级)。不少官员甚至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全民所有制,至少是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按劳分配也受到冲击,不少地方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农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和消费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剥夺。随着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限制、剥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对这种限制、剥夺的抵制和抗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表现为大量的瞒产私分和普遍的消极怠工。1959—1961年,部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主要由于农民的消极怠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引起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大饥荒。国家与农民都在这场负和博弈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国家与农民都开始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反思,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由于农民的抵制和抗争及其严重后果,国家不得不向农民做出让步。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60条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取消了按需分配,解散了公共食堂。此外,还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等。然而农民,至少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显然不满足于国家的让步和调整。1961年初,安徽农民掀起了第二次包产到户的浪潮。农民的改革实践得到了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例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不但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改革的试点、推广。在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到1961年底,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并免去了曾希圣的职务。虽然如此,由于成效显著,包产到户已成燎原之势,就连毛泽东家乡的农民也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中,全国约有3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这时,许多中央官员,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富春、邓子恢等领导干部都支持包产到户,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则表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时,形势已经非常接近1980年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重要谈话时的情况,包产到户的合法化与推广似乎只需要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表态。毛泽东最终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击退了包产到户的第二次浪潮。1962年7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严厉批判包产到户。毛泽东指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搞不搞包产到户,关系到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正式宣告包产到户“非法”)。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单干风”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会后,许多支持包产到户的各级官员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和制裁,改革迅速退潮。二、改革过程(下):国家与农民的社会博弈第三次浪潮似乎是第二次浪潮的重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亿多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相当多农民处于贫困状态。这不但严重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邓小平事后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国家与农民都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调整和改革。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国家主动采取了放权让利、休养生息的政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根据该草案,从1979年起,稳定并减少农产品统购指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这些政策使农民获得了很大的实惠,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草案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该草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60条的翻版。根据该草案,应继续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强调要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该草案还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该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换句话说,包产到户是“不合法”的。不过,该草案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有一定的松动,允许包工、包产到组。然而,同第二次浪潮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至少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同样不满足于国家的放权让利;包产到户的第一推动力同样是农民,首先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并且同样经历了一个农民推动地方,地方推动中央的过程。1978年9月,安徽省肥西县黄花大队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同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包干到户,拉开了第三次浪潮的序幕。在此前后,安徽省的许多生产队自发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工到户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产到户首先得到了所属公社与县级官员的支持。例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不但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改革的试点、推广。在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而且允许某些例外。但在原则上,包产到户仍然是不合法的。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实践又一次突破了中央的政策界限。到1979年底,安徽全省农村普遍实行了责任制,实行不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38.4%,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61.1%;在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10%,实行其它形式联产责任制的占11.3%。由于成效显著,包产到户迅速向其它地区,主要是贫困地区扩散,如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山东等地。至此,包产到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表态。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其崇高威望有力推动了第三次浪潮。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针对“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强调,“关键是发展生产力”,“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他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谈话不但从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从理论上论述了改革的目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原则(“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等重大政策问题,鼓励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试验。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谈话发表后,中央的政策进一步松动。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关于包产到户,该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这样,包产到户就由原则上不合法成为局部合法。同以往一样,中央的政策每松动一小步,基层的实践就前进一大步。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2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1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50%左右。这就意味着,包产到户已经大大突破了“落后地区”的政策界限。至此,改革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临界点。实行包产到户的广大农民和地方官员强烈要求中央将包产到户完全合法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央于1981年底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政策问题。在此之前,中央派出了17个联合调查组,历时近两个月,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问题。从各地传来的信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包工不如包产,包产不如包干。事实胜于雄辩,与会者很快取得共识: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个社会主义的“户口”。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年1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包产到户就由局部合法成为完全合法。1982年底,全国共有8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83年和1984年,中央又连续下发了两个1号文件,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将包产到户稳定化、合理化、长期化、规范化。83年的1号文件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包产到户的合理性,称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针对土地承包期过短,土地调整频繁等问题,为了稳定农民的预期,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84年的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长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还确立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并有条件地允许转包。1983年底和1984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部生产队的比重分别达到97.9%和99%。1993年,在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为了指导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文件进一步延长了土地承包期:在原定的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该文件还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并有条件地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土地承包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从1993年到1999年,各地先后开展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在第三次浪潮中,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法律手段确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调整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例如,1986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除了确认和保护个人或者集体的承包经营权以外,还进一步明确了承包方的权利,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有条件的转包权和转让权、优先承包权、继承人继续承包权。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了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条件和程序。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总之,在包产到户普遍推行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逐渐获得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保护、调整、规范,土地承包制度逐渐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并不断完善。为了更好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调整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根据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法的核心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明确成为国家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即物权。承包法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承包法还具体规定了承包的原则和程序,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流转、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等等。关于承包期限,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它方式流转”。承包法的制定,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法律体系的基本完善。三、约束条件(上):利益关系包产到户三次浪潮的历史说明,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是国家与农民(包括地方官员、社队干部)、农们与农民等改革主体之间集体谈判、公共选择或社会博弈的过程,是其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其进行制度选择、制度生产和制度交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逐渐形成、扩散、完善,并逐步从合同向政策,从政策向法律转换。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交易的过程,新的制度均衡不过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科学地解释这个过程,离不开对制度变迁约束条件的分析。改革的必要条件是,新制度的预期净收益大于旧制度的预期净收益。换句话说,存在着改革的预期收益。这就意味着,旧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有关个人、团体、集团就会产生改革的动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队是最为基本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按劳分配,都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包产到户的实行之所以引起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就是因为农民家庭经营替代了生产队集体经营,从而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农民的包产到户改革,首先并且主要是在生产队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可以从生产队这个基础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队生产理论,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状态。生产队集体经营就是把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不同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的生产。给定土地和资本,生产队的效率就成为劳动与管理的函数。首先分析劳动。给定劳动时间(T),再给定技术水平,实际发挥作用的劳动(L)就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e, 即,L=eT。经验表明,一般劳动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劳动者的效用函数是max U (V, e)。其中,U为个人效用,V为收入或其它收益,e为劳动努力程度。U (V, e)的意思是,(1)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收入或其它收益越高,个人效用越大;(2)假定其它因素不变,劳动努力程度越小,或者说闲暇越大,个人效用越大。给定劳动者对闲暇的偏好,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是否相关以及相关程度。收入或其它收益是闲暇的机会成本。如果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无关(“按需分配”),闲暇的机会成本就等于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劳动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那么,他就会最大化闲暇,直到劳动努力程度接近甚至等于零的地步(“出工不出力”)。如果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相关(“按劳分配”),那么,闲暇的机会成本大于零,从而劳动努力程度大于零。相关程度越高,闲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从而劳动努力程度越大。例如,同样是按劳分配,计件工资制(“包工、包产、包干”)下的劳动努力程度就大于计时工资制(“工分制”)下的劳动努力程度,因为前者的相关程度高于后者。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还取决于预期偷懒成本。预期偷懒成本等于偷懒的惩罚力度(降低收入、解雇等)乘以偷懒的发现概率。偷懒的惩罚力度越大,偷懒的发现概率越大,预期偷懒成本就越高,从而劳动努力程度越大。 劳动努力程度的这两个制约因素(“奖勤罚懒”)实际上就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制度约束条件。首先,在生产队集体经营体制下,对劳动者普遍实行计时工资制(工分制),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相关程度低,闲暇的机会成本低,从而劳动努力程度低。其次,劳动者名义上是但事实上又不是所有者。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者,所以劳动者并不关心集体生产的净收益;因为名义上是所有者,所以劳动者享有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解雇。除了收入以外,劳动者还享有其它收益。这部分收益属于劳动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劳动者的这部分收益类似于就业权,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降低。这样一来,即使被发现,偷懒的惩罚力度很低。相比之下,偷懒而不能被解雇的负效应最大。它不仅降低了偷懒者本人的劳动努力程度,而且对其他劳动者产生了负的示范效应,从而降低了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努力程度。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第三,在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提高了管理者的监督成本,降低了劳动者偷懒被发现的概率。何况,在农业生产中,管理者并不是无处不在。在管理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偷懒的发现概率几乎等于零。这样一来,偷懒的惩罚力度和发现概率低,预期偷懒成本就低,从而劳动努力程度低。 劳动者偷懒的发现概率和惩罚力度,从而预期偷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给定管理时间(T),再给定技术水平,实际发挥作用的管理(M)就取决于管理努力程度e, 即,M=eT。经验表明,一般管理者的行为目的同样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类似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是max U (V, e)。其中,U为个人效用,V为收入或其它收益,e为管理努力程度。U (V, e)的意思是,(1)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收入或其它收益越高,个人效用越大;(2)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管理努力程度越小,或者说闲暇越大,个人效用越大。 注释:
邓小平:《改革的步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p238
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 版,p146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p32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p40
许人峻:《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百年潮》,2002年第2期,p23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 版,p65-6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p370
同注4,p131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p315、316
邓英淘等:《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p42、43
同注10,p42
同注10,p43
事实上,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很小,考虑到人口的变化更是如此。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把二者作为常量处理。
出于与前注类似的考虑,我们也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水平作为常量处理。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1版,p314、321
生产队之所以普遍实行计时工资制,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外,技术上的原因是,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手工作业。在手工作业条件下,计件的操作成本较高(不是不能操作)。
同样,在手工作业条件下,偷懒的发现成本较高(同样,不是不能发现)。
出于与注13、14类似的考虑,我们也把管理时间和技术水平作为常量处理。
同注15。
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
240331
原作者:苗壮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生联合导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邓小平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发1983年1号文件当它(社会)形成一个发达的法典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需要什么,以及这些力量是否想使该法典强固到足以忽视可能遇到的任何阻力的地步。----霍姆斯 是历史建立了这一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相伴随的法律……土地转让的限制、绝对所有权的暂停、不确定继承、诸多将来履行的财产遗赠、私人信托和慈善委托,所有这些法律的名目都只有在历史之光的照耀下才能理解。它们都是从历史中获得动力且必定会影响它们此后的发展。----卡多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本文运用历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过程、约束条件和改革方式,以总结改革的经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改革的理论,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迁必然引发其它相关制度的变迁。同任何深刻的制度变迁一样,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它不但初步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及城乡关系制度改革,并引起了人们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曾经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都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其根本解决也离不开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温故而知新。回顾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是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的,包含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信息。虽然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改革的约束条件也大不相同,从而改革的过程和方式各有特色,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制度及其变迁毕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改革的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也大体相同,因此,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正如本文所归纳、总结的那样,中国的城乡改革与对外开放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合同到政策,从政策到法律的过程,都采取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诱发性改革与强制性改革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局部/部分改革到全局/整体改革,从边际/增量改革到总量/存量改革的方式。因此,总结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我们总结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在方法上,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类似,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主流方法也是均衡/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之所以如此,理论上的原因主要在于,静态分析更便于利用数学工具;实践上的原因主要在于,至少从现代起,西方社会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基本经济制度大体上是一个给定的体系;其中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大体上是在体制内进行的。这样的现实状况,加上主流方法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及其主要来源—新制度经济学,都偏重于研究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功能,而不是法律/制度变迁的过程/动力。这样的学术倾向,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将批判地吸收、借鉴历史法学、社会法学以及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经济分析法学的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均衡/动态分析的逻辑框架,进而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可以说是本文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改革过程(上):国家与农民的社会博弈1956-1957年,1961-1962年以及1978-1984年,中国农村曾发生过三次包产到户浪潮。这三次浪潮的起点模式都是人民公社制度,目标模式都是承包经营制度。比较研究这三次改革的过程,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改革的规律。人民公社制度的前身是土地改革所确立的土地个体所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对其家庭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及其相关的经营、核算、流通、分配等制度。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国家就开始引导农民发展互助组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是在承认和保护农民个体土地所有权和个体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过渡时期(1953-1956年),国家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经过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入股和土地分红,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按劳分配。到1958年,最终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和演进过程,是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进行限制、剥夺的过程,也是农民对这种限制、剥夺进行抵制和抗争,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并迫使国家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调整的过程,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博弈过程。早在1956年高级社建立之初,四川江津、安徽芜湖、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民就掀起了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浪潮。农民的改革实践还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包产到户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是“非法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和支持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制裁。高昂的改革成本使得包产到户的第一次浪潮迅速退潮。人民公社制度使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限制、剥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范围达到了公社一级(相当于乡级),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联社一级(相当于县级)。不少官员甚至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全民所有制,至少是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按劳分配也受到冲击,不少地方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农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和消费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剥夺。随着国家对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限制、剥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对这种限制、剥夺的抵制和抗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表现为大量的瞒产私分和普遍的消极怠工。1959—1961年,部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主要由于农民的消极怠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引起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大饥荒。国家与农民都在这场负和博弈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国家与农民都开始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反思,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由于农民的抵制和抗争及其严重后果,国家不得不向农民做出让步。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60条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取消了按需分配,解散了公共食堂。此外,还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等。然而农民,至少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显然不满足于国家的让步和调整。1961年初,安徽农民掀起了第二次包产到户的浪潮。农民的改革实践得到了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例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不但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改革的试点、推广。在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到1961年底,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并免去了曾希圣的职务。虽然如此,由于成效显著,包产到户已成燎原之势,就连毛泽东家乡的农民也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中,全国约有3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这时,许多中央官员,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富春、邓子恢等领导干部都支持包产到户,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则表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时,形势已经非常接近1980年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重要谈话时的情况,包产到户的合法化与推广似乎只需要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表态。毛泽东最终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击退了包产到户的第二次浪潮。1962年7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严厉批判包产到户。毛泽东指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搞不搞包产到户,关系到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正式宣告包产到户“非法”)。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单干风”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会后,许多支持包产到户的各级官员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和制裁,改革迅速退潮。二、改革过程(下):国家与农民的社会博弈第三次浪潮似乎是第二次浪潮的重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亿多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相当多农民处于贫困状态。这不但严重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邓小平事后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国家与农民都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调整和改革。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国家主动采取了放权让利、休养生息的政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根据该草案,从1979年起,稳定并减少农产品统购指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这些政策使农民获得了很大的实惠,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草案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该草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60条的翻版。根据该草案,应继续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强调要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该草案还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该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换句话说,包产到户是“不合法”的。不过,该草案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有一定的松动,允许包工、包产到组。然而,同第二次浪潮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至少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同样不满足于国家的放权让利;包产到户的第一推动力同样是农民,首先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并且同样经历了一个农民推动地方,地方推动中央的过程。1978年9月,安徽省肥西县黄花大队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同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包干到户,拉开了第三次浪潮的序幕。在此前后,安徽省的许多生产队自发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工到户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产到户首先得到了所属公社与县级官员的支持。例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不但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改革的试点、推广。在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而且允许某些例外。但在原则上,包产到户仍然是不合法的。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实践又一次突破了中央的政策界限。到1979年底,安徽全省农村普遍实行了责任制,实行不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38.4%,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61.1%;在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10%,实行其它形式联产责任制的占11.3%。由于成效显著,包产到户迅速向其它地区,主要是贫困地区扩散,如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山东等地。至此,包产到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表态。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其崇高威望有力推动了第三次浪潮。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针对“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强调,“关键是发展生产力”,“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他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谈话不但从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改革实践,而且从理论上论述了改革的目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原则(“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等重大政策问题,鼓励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试验。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谈话发表后,中央的政策进一步松动。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关于包产到户,该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这样,包产到户就由原则上不合法成为局部合法。同以往一样,中央的政策每松动一小步,基层的实践就前进一大步。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2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1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50%左右。这就意味着,包产到户已经大大突破了“落后地区”的政策界限。至此,改革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临界点。实行包产到户的广大农民和地方官员强烈要求中央将包产到户完全合法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央于1981年底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政策问题。在此之前,中央派出了17个联合调查组,历时近两个月,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问题。从各地传来的信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包工不如包产,包产不如包干。事实胜于雄辩,与会者很快取得共识: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个社会主义的“户口”。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年1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包产到户就由局部合法成为完全合法。1982年底,全国共有8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83年和1984年,中央又连续下发了两个1号文件,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将包产到户稳定化、合理化、长期化、规范化。83年的1号文件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包产到户的合理性,称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针对土地承包期过短,土地调整频繁等问题,为了稳定农民的预期,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84年的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长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还确立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并有条件地允许转包。1983年底和1984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部生产队的比重分别达到97.9%和99%。1993年,在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为了指导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文件进一步延长了土地承包期:在原定的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该文件还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并有条件地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土地承包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从1993年到1999年,各地先后开展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在第三次浪潮中,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法律手段确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调整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例如,1986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除了确认和保护个人或者集体的承包经营权以外,还进一步明确了承包方的权利,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有条件的转包权和转让权、优先承包权、继承人继续承包权。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了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条件和程序。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总之,在包产到户普遍推行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逐渐获得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保护、调整、规范,土地承包制度逐渐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并不断完善。为了更好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调整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根据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法的核心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明确成为国家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即物权。承包法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承包法还具体规定了承包的原则和程序,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流转、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等等。关于承包期限,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它方式流转”。承包法的制定,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法律体系的基本完善。三、约束条件(上):利益关系包产到户三次浪潮的历史说明,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是国家与农民(包括地方官员、社队干部)、农们与农民等改革主体之间集体谈判、公共选择或社会博弈的过程,是其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其进行制度选择、制度生产和制度交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逐渐形成、扩散、完善,并逐步从合同向政策,从政策向法律转换。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交易的过程,新的制度均衡不过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科学地解释这个过程,离不开对制度变迁约束条件的分析。改革的必要条件是,新制度的预期净收益大于旧制度的预期净收益。换句话说,存在着改革的预期收益。这就意味着,旧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有关个人、团体、集团就会产生改革的动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队是最为基本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按劳分配,都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包产到户的实行之所以引起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就是因为农民家庭经营替代了生产队集体经营,从而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农民的包产到户改革,首先并且主要是在生产队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可以从生产队这个基础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队生产理论,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状态。生产队集体经营就是把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不同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的生产。给定土地和资本,生产队的效率就成为劳动与管理的函数。首先分析劳动。给定劳动时间(T),再给定技术水平,实际发挥作用的劳动(L)就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e, 即,L=eT。经验表明,一般劳动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劳动者的效用函数是max U (V, e)。其中,U为个人效用,V为收入或其它收益,e为劳动努力程度。U (V, e)的意思是,(1)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收入或其它收益越高,个人效用越大;(2)假定其它因素不变,劳动努力程度越小,或者说闲暇越大,个人效用越大。给定劳动者对闲暇的偏好,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是否相关以及相关程度。收入或其它收益是闲暇的机会成本。如果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无关(“按需分配”),闲暇的机会成本就等于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劳动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那么,他就会最大化闲暇,直到劳动努力程度接近甚至等于零的地步(“出工不出力”)。如果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相关(“按劳分配”),那么,闲暇的机会成本大于零,从而劳动努力程度大于零。相关程度越高,闲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从而劳动努力程度越大。例如,同样是按劳分配,计件工资制(“包工、包产、包干”)下的劳动努力程度就大于计时工资制(“工分制”)下的劳动努力程度,因为前者的相关程度高于后者。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还取决于预期偷懒成本。预期偷懒成本等于偷懒的惩罚力度(降低收入、解雇等)乘以偷懒的发现概率。偷懒的惩罚力度越大,偷懒的发现概率越大,预期偷懒成本就越高,从而劳动努力程度越大。 劳动努力程度的这两个制约因素(“奖勤罚懒”)实际上就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制度约束条件。首先,在生产队集体经营体制下,对劳动者普遍实行计时工资制(工分制),劳动努力程度与收入相关程度低,闲暇的机会成本低,从而劳动努力程度低。其次,劳动者名义上是但事实上又不是所有者。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者,所以劳动者并不关心集体生产的净收益;因为名义上是所有者,所以劳动者享有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解雇。除了收入以外,劳动者还享有其它收益。这部分收益属于劳动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劳动者的这部分收益类似于就业权,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降低。这样一来,即使被发现,偷懒的惩罚力度很低。相比之下,偷懒而不能被解雇的负效应最大。它不仅降低了偷懒者本人的劳动努力程度,而且对其他劳动者产生了负的示范效应,从而降低了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努力程度。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第三,在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提高了管理者的监督成本,降低了劳动者偷懒被发现的概率。何况,在农业生产中,管理者并不是无处不在。在管理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偷懒的发现概率几乎等于零。这样一来,偷懒的惩罚力度和发现概率低,预期偷懒成本就低,从而劳动努力程度低。 劳动者偷懒的发现概率和惩罚力度,从而预期偷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给定管理时间(T),再给定技术水平,实际发挥作用的管理(M)就取决于管理努力程度e, 即,M=eT。经验表明,一般管理者的行为目的同样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类似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是max U (V, e)。其中,U为个人效用,V为收入或其它收益,e为管理努力程度。U (V, e)的意思是,(1)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收入或其它收益越高,个人效用越大;(2)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管理努力程度越小,或者说闲暇越大,个人效用越大。 注释:
邓小平:《改革的步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p238
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 版,p146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p32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p40
许人峻:《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百年潮》,2002年第2期,p23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 版,p65-6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p370
同注4,p131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p315、316
邓英淘等:《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p42、43
同注10,p42
同注10,p43
事实上,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很小,考虑到人口的变化更是如此。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把二者作为常量处理。
出于与前注类似的考虑,我们也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水平作为常量处理。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1版,p314、321
生产队之所以普遍实行计时工资制,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外,技术上的原因是,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手工作业。在手工作业条件下,计件的操作成本较高(不是不能操作)。
同样,在手工作业条件下,偷懒的发现成本较高(同样,不是不能发现)。
出于与注13、14类似的考虑,我们也把管理时间和技术水平作为常量处理。
同注15。
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