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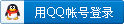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谢有树要求镇江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案探析
──兼议对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行为的界定
马龙喜、吴成
某房屋开发公司经拍卖程序取得镇江市针织厂的土地使用权,拟在该地块建造商品房。在镇江市规划局为其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针织厂原有的一处配电房被列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开发公司直到1999年开发完成后,也未将配电房拆除,而是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酒店。原告谢有树的居所紧邻该配电房,他以酒店的噪音和油烟影响其生活为由起诉规划局,要求被告按《镇江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镇江规划规定》)的要求履行其法定职责,限令开发公司拆除该违章建筑。规划局则辩称该房为应当拆迁却未实际拆除之建筑,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所确定的违章建筑,而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的调整对象,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该地块上连同配电房在内的原针织厂所有房屋的产权证均已在1999年被房管局收回作废。
对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赞同规划局的观点,认为原告起诉规划局行政不作为缺乏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房原先虽有合法的产权证,但此证现已作废。既然其已被纳入拆迁红线范围内就理应拆除,否则就属违章建筑。《规划法》对此所作规定虽然不太明显,但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以下简称《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规划局应将其作为“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违章建筑来查处。鉴于规划局未履行该法定职责,故原告的起诉理由成立,其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探讨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规划法》的规定,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是规划局的一项法定职责。从中可以看出,本案被告履行这一职责必须以开发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行为”为前提条件。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合行政违法的四个构成要件(1、主体要件;2、行为要件;3、后果要件;4、主观要件)来谈,能够认定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确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其中1、4要件不难分析,关键在于对2、3要件应如何正确理解。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阐述。
(一)、开发公司具有违反《规划法》的行为。
本案中配电房的性质比较特殊,《规划法》确实未将这样的建筑明确界定为违章建筑。故规划局认为其对该房已履行了规划拆除的职责,而责令拆除该房的义务应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拆迁办)来履行。但《拆迁条例》亦未明确规定拆迁办可对此进行查处。这样一来该配电房在法律上似乎处于真空地带,既然规划局和拆迁办都管不到它,那它便能得以“合法”存在,而这样的推断结果显然不合情理。笔者尝试从不同的法理角度比较《规划法》和《拆迁条例》之差异,可以揭示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是《规划法》,而非《拆迁条例》。
1、二者在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方面的比较。
《规划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法律手段,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整,使之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而国务院制定《拆迁条例》是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立法目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立法内容也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对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作出规定(见《规划法》第二~五章,全文共六章);后者则对房屋拆迁的法定程序和补偿、安置办法进行了阐述(见《拆迁条例》第二~四章,全文共六章)。而立法内容的不同又导致二者在立法技术上必然存在偏差:前者侧重于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涉及不多;后者则强调行政管理相对方(特别是拆迁人)应履行的义务,对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极少[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拆迁办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拆迁人的拆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合理的安置和补偿,并在此基础上督促被拆迁人将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本案中拆迁办已经依法履行了上述管理职责,至此房屋拆迁管理法律关系中的法律目的已然得到实现。此后实际拆除配电房的权利便由拆迁人获得,而其怠于行使该权利的行为无需由拆迁办来监督。因为该行为既未妨碍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也未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根本就不属于违反《拆迁条例》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在《拆迁条例》的罚则中,确实也找不到拆迁办可对该行为进行处罚的相关条款,原因在于拆迁办根本就不具备此项管理职能。
同一行为当由规划局来处理时,其行为性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规划局虽然已将配电房纳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局已经履行了其全部的规划职责。因为该地块上原有建筑被拆除后,规划局还要对新建工程制定规划方案,此时若原有的部分建筑仍然存在显然不符合新规划方案的要求。本案中遗留的配电房破坏了新建住宅小区的整体规划,与《规划法》的立法目的背道而弛,所以应认定其性质为违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其次从立法技术来看,《规划法》着重要求规划部门去主动履行其管理职责,而管理相对方则应被动地接受管理,严格按照规划部门制定的规划方案进行施工建设,即“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一旦发现管理相对方履行该义务的行为不符合规划要求,规划局就必须对该行为加以纠正。这就是说,规划局不仅要负责规划的制定,而且更要监督规划的实施,否则再完美的规划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对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以规划局对该违法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
2、二者所调整的权利关系的性质比较。
《拆迁条例》调整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私权关系(即与私人的直接利益有着联系的那些关系形式);而《规划法》调整的则是国家管理城市建设的公权关系(即关系到公共关系的那些关系形态)[2]。所以二者所针对的被管理对象其法律性质亦不相同:前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较为特定,仅指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而后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具有不特定性,任何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的单位或个人,都会成为被管理的对象。虽然对于管理相对方来说,搞施工建设是其私权,该权利的行使不一定会直接侵害其他私人或集体的利益,但很可能会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妨碍,这时它侵犯的就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即公权利。本案中开发公司未按规定拆除配电房的行为,侵害的显然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被拆迁人的直接私人利益,所以从这一点来分析,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也是《规划法》,而不是《拆迁条例》。
(二)、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造成了侵害后果。
行政法意义上的侵害后果是指对行政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损害或消极影响。《规划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对城市规划的管理关系,对被管理人而言,就意味着其行为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本案中配电房的继续存在不仅与居民小区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有碍观瞻,而且位置正好在小区的出入口处,妨碍居民出入及过路人的正常通行,明显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其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该房亦与城市建筑的主流发展方向不符,不能适应今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届时其侵害的可能就是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了。再次该房的存在还间接地侵害了原告的私人利益,因为开发公司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饭店,该店产生的油烟和噪音不可能不对原告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侵害了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其造成的侵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
本案中规划局对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放任不管的行为危及的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它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原告的个人利益,但该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可见原告起诉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保护因规划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而受损的公众的利益,所以该诉讼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其实质为诉讼主体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从而保护各种公、私利益[3]。有权利必有救济,有侵害也必需救济,这是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规划局应对城市建设中的这类违法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当其不能依法作出回应时,寻求司法救济理应成为原告最终的维权机会[4]。
二、原告要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有无法律依据?
以上论证从法理角度证明了开发公司的行为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根据规定规划局对“违法建设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不过此处的“义务”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能将其与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混为一谈。法定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应当要履行的具体义务,其特征为该义务必须要在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所以原告起诉要求规划局履行行政职责,应有具体的法律条款为依据,否则其起诉理由依然无法成立。因为本案系行政案件,而非民商案件,前者定案的证据标准远比后者要严格,通过法理分析得出的这一结论不足以给本案定性。
在《规划法》中,我们确实找不到规划局的这一法定义务,但在《江苏规划办法》中,这一义务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得不太明确而已。该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规划部门对于五项违法建设行为应予查处,其中一至四项违法行为所指对象均系新建筑,其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用积极的方式故意违反规划规定以完成新工程项目的建设(如在未取得规划许可证或该证失效等情况下违规进行建设的行为)。而本案的配电房属于旧建筑,开发公司未将其拆除的行为与上述任何一项违法情形都不相符,该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以消极的方式阻碍规划方案的实施。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既可由积极的行为方式构成,也可由消极的行为方式构成,尽管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其行为方式较为特殊,但究其本质仍应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因为城市建设有建就必有拆,新建项目怎么建固然应符合规划要求,但旧房若不拆除新房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且类似配电房这样应拆而未拆的旧房还可能由其它的一些客观原因而形成,如因开发公司资金不足或公司被依法注销等原因。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完全将其排除,若规划部门对此放任不管,那么这些产权证已被注销的旧建筑将会长久存在,这样的建筑难道不属于违章建筑吗?
可见,《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至四项规定涵盖不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违法建设行为”,针对实践中“违法建设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可预见性,该条款增加了第五项规定:规划部门对于“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也应查处。笔者认为,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应归类为“其它违法建设行为”,规划局对开发公司的这一违法行为理应进行查处,所以此项规定正是判定本案被告负有行政作为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这一兜底条款从其文字表述内容来看确实不很明确,甚至可以用“模糊”来形容,但在具体适用时,其法律效力却毋庸置疑,这是立法上有意采用“模糊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神奇效果。
此外探讨本案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镇江规划规定》,该规定第七十三条列举了“违法建设行为”的九项情形,其中第五项规定:“临时性建设工程逾期未拆除或建设用地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设到期未拆除的”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形”,规划部门应予查处。依照此规定,配电房当属违章建筑无疑,这一规定也是原告起诉时援引的直接法律依据。不过由于镇江市不属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并无制定地方性行政规章的立法权限(江苏省内仅南京、苏州、无锡、徐州等四城市有此立法权),故其制订的《镇江规划规定》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依据。但该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五项的内容不仅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与《规划法》及《江苏规划办法》的立法精神也相一致,所以它在帮助我们理解“违法建设行为”的丰富内涵时不无裨益。
以上论述证明,本案被告规划局对于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负有责令开发公司限期拆除的行政职责,由于行政权属于法定权,具有不可自由处置性,亦不能自由转让[5],所以规划局怠于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行为。
[1]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58-59页。
[2]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60页。
[3]强雨、周刚:《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9期,第56页。
[4]戴建志:《关于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件的对话》,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第19页。
[5]杨解军:《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引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第95页。 |
240331
谢有树要求镇江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案探析
──兼议对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行为的界定
马龙喜、吴成
某房屋开发公司经拍卖程序取得镇江市针织厂的土地使用权,拟在该地块建造商品房。在镇江市规划局为其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针织厂原有的一处配电房被列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开发公司直到1999年开发完成后,也未将配电房拆除,而是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酒店。原告谢有树的居所紧邻该配电房,他以酒店的噪音和油烟影响其生活为由起诉规划局,要求被告按《镇江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镇江规划规定》)的要求履行其法定职责,限令开发公司拆除该违章建筑。规划局则辩称该房为应当拆迁却未实际拆除之建筑,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所确定的违章建筑,而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的调整对象,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该地块上连同配电房在内的原针织厂所有房屋的产权证均已在1999年被房管局收回作废。
对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赞同规划局的观点,认为原告起诉规划局行政不作为缺乏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房原先虽有合法的产权证,但此证现已作废。既然其已被纳入拆迁红线范围内就理应拆除,否则就属违章建筑。《规划法》对此所作规定虽然不太明显,但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以下简称《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规划局应将其作为“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违章建筑来查处。鉴于规划局未履行该法定职责,故原告的起诉理由成立,其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探讨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规划法》的规定,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是规划局的一项法定职责。从中可以看出,本案被告履行这一职责必须以开发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行为”为前提条件。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合行政违法的四个构成要件(1、主体要件;2、行为要件;3、后果要件;4、主观要件)来谈,能够认定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确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其中1、4要件不难分析,关键在于对2、3要件应如何正确理解。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阐述。
(一)、开发公司具有违反《规划法》的行为。
本案中配电房的性质比较特殊,《规划法》确实未将这样的建筑明确界定为违章建筑。故规划局认为其对该房已履行了规划拆除的职责,而责令拆除该房的义务应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拆迁办)来履行。但《拆迁条例》亦未明确规定拆迁办可对此进行查处。这样一来该配电房在法律上似乎处于真空地带,既然规划局和拆迁办都管不到它,那它便能得以“合法”存在,而这样的推断结果显然不合情理。笔者尝试从不同的法理角度比较《规划法》和《拆迁条例》之差异,可以揭示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是《规划法》,而非《拆迁条例》。
1、二者在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方面的比较。
《规划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法律手段,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整,使之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而国务院制定《拆迁条例》是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立法目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立法内容也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对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作出规定(见《规划法》第二~五章,全文共六章);后者则对房屋拆迁的法定程序和补偿、安置办法进行了阐述(见《拆迁条例》第二~四章,全文共六章)。而立法内容的不同又导致二者在立法技术上必然存在偏差:前者侧重于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涉及不多;后者则强调行政管理相对方(特别是拆迁人)应履行的义务,对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极少[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拆迁办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拆迁人的拆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合理的安置和补偿,并在此基础上督促被拆迁人将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本案中拆迁办已经依法履行了上述管理职责,至此房屋拆迁管理法律关系中的法律目的已然得到实现。此后实际拆除配电房的权利便由拆迁人获得,而其怠于行使该权利的行为无需由拆迁办来监督。因为该行为既未妨碍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也未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根本就不属于违反《拆迁条例》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在《拆迁条例》的罚则中,确实也找不到拆迁办可对该行为进行处罚的相关条款,原因在于拆迁办根本就不具备此项管理职能。
同一行为当由规划局来处理时,其行为性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规划局虽然已将配电房纳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局已经履行了其全部的规划职责。因为该地块上原有建筑被拆除后,规划局还要对新建工程制定规划方案,此时若原有的部分建筑仍然存在显然不符合新规划方案的要求。本案中遗留的配电房破坏了新建住宅小区的整体规划,与《规划法》的立法目的背道而弛,所以应认定其性质为违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其次从立法技术来看,《规划法》着重要求规划部门去主动履行其管理职责,而管理相对方则应被动地接受管理,严格按照规划部门制定的规划方案进行施工建设,即“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一旦发现管理相对方履行该义务的行为不符合规划要求,规划局就必须对该行为加以纠正。这就是说,规划局不仅要负责规划的制定,而且更要监督规划的实施,否则再完美的规划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对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以规划局对该违法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
2、二者所调整的权利关系的性质比较。
《拆迁条例》调整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私权关系(即与私人的直接利益有着联系的那些关系形式);而《规划法》调整的则是国家管理城市建设的公权关系(即关系到公共关系的那些关系形态)[2]。所以二者所针对的被管理对象其法律性质亦不相同:前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较为特定,仅指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而后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具有不特定性,任何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的单位或个人,都会成为被管理的对象。虽然对于管理相对方来说,搞施工建设是其私权,该权利的行使不一定会直接侵害其他私人或集体的利益,但很可能会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妨碍,这时它侵犯的就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即公权利。本案中开发公司未按规定拆除配电房的行为,侵害的显然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被拆迁人的直接私人利益,所以从这一点来分析,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也是《规划法》,而不是《拆迁条例》。
(二)、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造成了侵害后果。
行政法意义上的侵害后果是指对行政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损害或消极影响。《规划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对城市规划的管理关系,对被管理人而言,就意味着其行为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本案中配电房的继续存在不仅与居民小区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有碍观瞻,而且位置正好在小区的出入口处,妨碍居民出入及过路人的正常通行,明显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其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该房亦与城市建筑的主流发展方向不符,不能适应今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届时其侵害的可能就是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了。再次该房的存在还间接地侵害了原告的私人利益,因为开发公司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饭店,该店产生的油烟和噪音不可能不对原告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侵害了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其造成的侵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
本案中规划局对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放任不管的行为危及的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它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原告的个人利益,但该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可见原告起诉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保护因规划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而受损的公众的利益,所以该诉讼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其实质为诉讼主体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从而保护各种公、私利益[3]。有权利必有救济,有侵害也必需救济,这是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规划局应对城市建设中的这类违法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当其不能依法作出回应时,寻求司法救济理应成为原告最终的维权机会[4]。
二、原告要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有无法律依据?
以上论证从法理角度证明了开发公司的行为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根据规定规划局对“违法建设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不过此处的“义务”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能将其与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混为一谈。法定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应当要履行的具体义务,其特征为该义务必须要在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所以原告起诉要求规划局履行行政职责,应有具体的法律条款为依据,否则其起诉理由依然无法成立。因为本案系行政案件,而非民商案件,前者定案的证据标准远比后者要严格,通过法理分析得出的这一结论不足以给本案定性。
在《规划法》中,我们确实找不到规划局的这一法定义务,但在《江苏规划办法》中,这一义务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得不太明确而已。该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规划部门对于五项违法建设行为应予查处,其中一至四项违法行为所指对象均系新建筑,其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用积极的方式故意违反规划规定以完成新工程项目的建设(如在未取得规划许可证或该证失效等情况下违规进行建设的行为)。而本案的配电房属于旧建筑,开发公司未将其拆除的行为与上述任何一项违法情形都不相符,该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以消极的方式阻碍规划方案的实施。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既可由积极的行为方式构成,也可由消极的行为方式构成,尽管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其行为方式较为特殊,但究其本质仍应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因为城市建设有建就必有拆,新建项目怎么建固然应符合规划要求,但旧房若不拆除新房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且类似配电房这样应拆而未拆的旧房还可能由其它的一些客观原因而形成,如因开发公司资金不足或公司被依法注销等原因。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完全将其排除,若规划部门对此放任不管,那么这些产权证已被注销的旧建筑将会长久存在,这样的建筑难道不属于违章建筑吗?
可见,《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至四项规定涵盖不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违法建设行为”,针对实践中“违法建设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可预见性,该条款增加了第五项规定:规划部门对于“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也应查处。笔者认为,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应归类为“其它违法建设行为”,规划局对开发公司的这一违法行为理应进行查处,所以此项规定正是判定本案被告负有行政作为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这一兜底条款从其文字表述内容来看确实不很明确,甚至可以用“模糊”来形容,但在具体适用时,其法律效力却毋庸置疑,这是立法上有意采用“模糊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神奇效果。
此外探讨本案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镇江规划规定》,该规定第七十三条列举了“违法建设行为”的九项情形,其中第五项规定:“临时性建设工程逾期未拆除或建设用地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设到期未拆除的”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形”,规划部门应予查处。依照此规定,配电房当属违章建筑无疑,这一规定也是原告起诉时援引的直接法律依据。不过由于镇江市不属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并无制定地方性行政规章的立法权限(江苏省内仅南京、苏州、无锡、徐州等四城市有此立法权),故其制订的《镇江规划规定》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依据。但该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五项的内容不仅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与《规划法》及《江苏规划办法》的立法精神也相一致,所以它在帮助我们理解“违法建设行为”的丰富内涵时不无裨益。
以上论述证明,本案被告规划局对于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负有责令开发公司限期拆除的行政职责,由于行政权属于法定权,具有不可自由处置性,亦不能自由转让[5],所以规划局怠于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行为。
[1]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58-59页。
[2]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60页。
[3]强雨、周刚:《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9期,第56页。
[4]戴建志:《关于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件的对话》,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第19页。
[5]杨解军:《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引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