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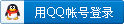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原作者:王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
前 言 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四大基本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道路通车里程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道路交通环境日益恶化,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已成为交通系统中的两大问题。而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四分之三为行人、乘客及非机动车驾驶人等交通弱者。根据2006年召开的首届商用车发展高峰论坛,2006年客运方式运载乘客人数超过169亿,占整个人流的91%,而交通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道路交通运输发展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公路客运量占整个客运体系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2%左右,另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客运车辆事故在特大交通事故中所占比重近70%。可见,公路客运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方式,而将公路客运中的交通事故纠纷类型化并探讨其法律解决方案,现实意义就极为迫切。 就目前立法来看,虽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第17章对运输合同专章规定,但其规定较为简单,各国法律规定均较为简单,已成通例,但是承运人与乘客间的权利义务却颇为重要。就理论研究来看,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可能因为考虑到运输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领域合同制度的特殊性质,运输合同的具体制度一直很少被人涉足。” 笔者主要以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人民法院案例选》及中国交通安全网总结整理的相关70余个案例为对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主要是经由这些权威数据库、网站、案例选分类整理的真实判决书、对判决的简述或者生活事例,本文在选取时尽量选取真实完整的判决书作为实证分析对象,这样就减少了对二手资料做二手分析(secondary analysis)时对资料本身可信度的查证。初步接纳已有分类标准并对资料做细致的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在个案解释(idiographic)之上做一些类型化的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探讨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个由可定义的多样因素合成的最复杂的一般概念,单凭这种抽象的一般概念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的多样表现形态并对人们的行为做相对确定的指引,此时类型化的方法就成为沟通抽象概念与具体个案的桥梁。而类型化方法本身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为弥补其个别化方法的缺陷而对自然科学普遍化方法做的有益借鉴。 在已有理论预设分类标准的基础上,从个案到类型,笔者总结了新的类型化标准,并以之拟定本文的论题和篇章架构。实务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类案件中:第一、好意同乘中对同乘人的致害事件,第二、完全归因于承运人驾车过失的致害事件,第三、完全归因于车外第三方的致害事件,第四、承运人与车外第三方共同致害事件,第五、承运人违反救助义务时对乘客的致害事件。责任主体、责任形态、安全运送义务、救助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等一系列问题则贯穿前述论题之中。本文以公路客运合同为分析模型,研究客运合同中上述几类共同性问题。
第1章 好意同乘中的车主责任问题1.1讨论好意同乘问题的意义 在当前交通拥挤及汽车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好意同乘现象日渐普遍, 2007年12月28日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在《“节能减排,从我做起”倡议书》中也提出了“为减少机动车排放,提倡从住宅到单位的私家车主动安排车牌单双号分日行驶,停驶日和行驶日的车主相互搭乘”的行动方案。实际上,不管是出于环保的还是日常生活便利的考虑,相互搭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提倡的出行方式。在有的国家,顺路搭乘甚至成为一种常态的主要交通方式。人类是自私的,但好意同乘说明在没有利益关系下,人们也会关心其他人的生活和福祉,虽然这种关心不是经常性的;而互相搭乘说明人类找到了一种更高级的将利他和利己有机结合起来的行为方式。 与此同时,近年来好意同乘纠纷越来越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好意同乘到底是纯粹的生活事实还是民事法律事实?好意同乘与无偿客运合同的关系是什么?发生事故时车主对同乘人是否是一律“适当补偿”?在讨论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时,上述问题难以回避,尤其是好意同乘问题和客运合同中的无偿客运合同又交织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这属于事实上的客运合同关系,有学者认为属于无偿客运合同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属于无名合同、可以类推适用客运合同的规定。1.2好意同乘的概念、特点及性质1.2.1好意同乘的概念和特点 好意同乘是指乘车人在运行供用者好意并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下同乘于运行供用者之车的现象。好意同乘是一种典型的生活互助行为,这种行为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好意同乘是理论界的通用说法,在实践中也称为“搭便车”、“搭顺风车”、“免费搭乘”等等,笔者认为“免费搭乘”的说法容易与无偿客运合同混淆,本文的立场之一就是区分两者,故不采“免费搭乘”的说法,仍用“好意同乘”的表述。 好意同乘中提供便利方的行为动机是出于情谊,也就是为了增进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和搭乘人的情谊,给予搭乘人一定的便利。好意同乘关系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无偿性,即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不直接或者间接追求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放弃经济利益,单方面提供方便;第二、好意性,即提供方便的一方伴随着利他性动机,是一种利己的过程中伴随利他的行为;第三、不具有契约性,即双方之间的好意协定关系是一种非法律行为的协定关系,在当事人之间没有法律性的意思表示,因而也不具有规范性的约束力,即使有给付行为的外观,也不具有合同意义上的债务履行,而只是任意的给付。上述特点必须同时具备,而核心特点是不具有契约性。不能单纯以无偿性推论系属好意同乘,而非法律行为,因为法律上也承认无偿客运合同的存在。 就好意同乘的概念应该明确的是:第一、好意同乘不以一方主动提供为限,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搭乘人主动请求对方给予便利的现象颇为常见,其与主动邀请同乘不应有法律评价上的不同。我国司法实务中也是采取类似态度。第二、好意同乘不能包括强行性乘坐,也不能包括无偿偷坐。 “经验的现实证明自身是一种茫无边际的杂多”,基于事实特征的此种无限性与人们对事实认知有限性的矛盾,人们所采用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属于“带有开放结构的语言”,概念的核心地带意义是清晰的,而越趋边缘地带意义越为模糊。好意同乘概念亦然。符合前面三项特点的属于“没有疑问的”好意同乘,结合前述特点,有如下“模棱两可的”情形应予说明:第一、好意同乘在搭乘者支付或者分担汽油费的情况下是否就成为有偿客运合同?对此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争议很大,但是多数观点采否定说,主张此时仍然属于好意同乘。这种情形下,分担油费等形式只是象征性地补偿,不构成对价给付,对驾车人的劳务仍属免费,仍然构成好意同乘。第二、好意同乘是否需要具备顺路同乘的特点?即是否以搭乘人与司机或者车主的目的地相同而顺路搭乘为必要?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要去的目的地不是搭乘人事先指定的,是否就不构成好意同乘?有学者就认为此时应该以无偿委托合同认定。笔者认为此种专程运送仍然属于单方施惠,除非双方明示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否则不能当然地认为构成事实上的契约关系。1.2.2好意同乘的性质 上述对好意同乘的分析一直是对此种生活现象的基本描述,而任何分析描述不论多么详尽都不能穷尽现实在内容上的多样性。好意同乘实质上的法律性质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实际上对好意同乘中车主责任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好意同乘行为民法定性的基础上的。明确了好意同乘的民法性质,才能恰当地处理纠纷,学界对此虽然讨论不多,但是对此前提性问题还是具有普遍共识的。1.2.2.1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 好意同乘是情谊行为的一种。实际上情谊行为也不是一个非常准确和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它产生于德国判例,在《德国民法典》上对其无明文规定,是一种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的行为,不能依法产生后果,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社会层面上的行为”,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好意施惠关系”或者“施惠关系”,其名异而实同。 作为情谊行为的好意同乘并不是一种法律行为,也就不可能构成客运合同。其主要原因是法律行为乃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核心是意思表示,而好意同乘中的一方是处于增进相互间的情谊而提供搭乘的方便,情谊增进是其行为的动机。“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效果意思)是构成合同的实质性因素,并非所有的协议都是合同”。而如前所述,虽然一方有邀请或者允许的表示,但是情谊的考虑是其出发点。在事实层面上,同乘人和车主之间存在一项合意,但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意,只是生活意义上的合意。此种合意不具有意思表示中基本的构成要素——效果意思,即没有受其拘束的意思,可见并不能构成法律行为。司法实务上对法律行为和没有拘束力的情谊行为的区分也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判断标准的。“一项情谊行为,只有在给付者具有法律上受约束的意思时,才具有法律行为的性质。这种意思,表现为给付者有意使他的行为获得法律行为上的效力……,亦即他想引起某种法律约束力……,而且受领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受领这种给付的。如果不存在这种意思,则不得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来评价这种行为。”好意同乘只是基于情谊而发生的一般社会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可见并非所有的合意都构成合同行为,实际上合同内容也不一定均须合意达成,只是合同中的要素须此而已。合同与合意并非完全一致,有法律意义的合意方可能构成合同。 因为好意同乘根本不构成一项法律行为,那么主张好意同乘关系类推适用客运合同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我国《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可见,只有无名合同才可能适用与其最相类似的相应有名合同的规定,好意同乘中不存在一项合同,甚至连法律行为都不成立,这项非法律行为和客运合同不具有基本的性质上的类似性。类推适用说是没有根据的。 有观点认为好意同乘构成事实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一旦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不管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确立、变更或者消灭某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都会基于法律的规定,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事实行为与好意同乘、乃至与情谊行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具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事实行为而言,其法律效果的发生不问是否为当事人所意欲,法律对其采取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但在好意同乘关系中,法律并没有对当事人之间的此种关系配置任何权利义务,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于此等行为,当事人既无受其拘束的意思,不能由之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可见,法律对好意同乘行为与事实行为采取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既然好意同乘根本不属于事实行为,主张好意同乘属于无因管理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提供搭乘者根本不具有发生法律行为的意思,法律对其也保持沉默,此时更谈不上管理意思的存在了。不能因为好意同乘与无因管理同具有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特点,就理所当然地将其在性质上归为一类。 以上是从概念和规范出发对好意同乘性质做的逻辑分析。更进一步看,好意同乘的性质本身属于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因为讨论能否将好意同乘这一生活事实上升为民事法律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面向生活世界进行民法解释的过程”,此种本体论解释结论的不同直接影响对好意同乘的性质界定,而不同的解释结论直接关系到将好意同乘放在民法层面规范还是交由交往道德规范,这就“直接涉及当事人之间利益安排”。 好意同乘关系虽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至少就今天的价值取向来说,该种社会关系“不具有可诉性”,也就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好意同乘这一生活事实也不能上升为民事法律事实。可诉性究竟是做出这一价值判断结论的依据还是该结论的当然结果,尚存疑问,这也显示了探讨价值判断问题时避免循环论证的难度。一个更现实的路径是交由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基于其所处社会的价值取向遵循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做出决定。这一方法既可以弥补可诉性标准循环论证之弊,又可以因应道德规则本身的变动性及其与法律规则边界的变动性。1.2.2.2好意同乘并非一概属于“法外空间” 上文对将好意同乘定性为情谊行为,并论证其不属于法律行为、不构成客运合同;不属于事实行为,也不构成无因管理。但好意同乘是否只能“由当事人的私人友谊调整”,“不由法律调整”,“不能由法律救济”呢?好意同乘关系中的双方不会对法律约束作实际思考,除非出了麻烦,麻烦一般出在同乘人在同乘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情形。 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不会支持受惠方行使合同中的给付请求权;施惠方也不会产生像无因管理中管理人要求本人偿还管理费用的问题;受惠方受有利益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也不会出现施惠方向受惠方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情形。但是在同乘过程中一旦施惠方对受惠方有加害行为,则可能出现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虽然法律规范调整的事项限于人际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有些人际关系只能交由道德习俗去调整。就民法来看,民事法律事实只不过是立法者将生活事实中无规范意义的部分剪裁掉并将剩余部分运用民法语言加以转述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民事法律事实不过是对生活事实进行的一场“圈地运动”。民事法律事实也就是在法律评价的指引下对生活事实的一部分的撷取。诚如狄尔泰所言:“人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总是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创造出来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好意同乘本身而言,施惠者基于增进情谊的考虑给予受惠者便利。就法律对好意同乘的评价而言,立法者对好意同乘行为的态度也反应了这一问题在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属于情谊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立法者对其在法律评价上的结论是该生活事实不适合用法律来调整,而只能归由道德习俗调整,他律性的调整方式只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时时受监视的状态。法律的沉默不语是对生活的最大尊重,也是立法者对自己理性有限性的最好理解。我们上文分析的好意同乘关系不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结论也是针对常态情形而言的,而且以考查其是否构成合同法律行为为重点。结论是在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属于“法外空间”。 好意同乘中“施惠方的承诺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对其承诺的不实现或不完全实现均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而仅仅是道德义务而已。但是,施惠方一旦开始进行施惠行为,他就必然负有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注意和保护义务,这是与主行为附随而来的义务,并不因施惠行为的好意、无偿的性质而得免除或减轻。”因此施惠方违反注意义务导致受惠方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施惠方的行为就可能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成为侵权行为。此时好意同乘就受法律调整,就成为法内空间了。至于此时的归责原则问题将在下文好意同乘的法律效力部分分析。 可见,对好意同乘关系的法律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常态与非常态,区分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正如以上分析,对好意同乘关系的定性是要做类型化讨论的,没法一概而论。同时,基于其可能的性质均能在现有的法内或者法外空间找到归宿,所以本文不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对好意同乘关系“法律完全不愿涉足”的观点。1.3对好意同乘法律效力的分析1.3.1好意同乘中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前所述,学界通说认为好意同乘关系中施惠方与受惠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受惠方对施惠方不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同时,受惠方的获益也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施惠方明知自己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仍然提供搭乘的便利,其对受惠方不得请求不当得利返还。 基于前述,受惠方对施惠方不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在施惠方违反先前的承诺,不提供搭乘的便利时,受惠方也不得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增进情谊的社交行为不宜置于法律的严密监督之下。问题是受惠方是否可以请求赔偿自己的信赖利益的损失乃至纯粹经济损失?学者一般认为此时的确可能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该项请求权的成立以施惠方的行为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故意悖于善良风俗原则加损害为必要,在此不赘。1.3.2好意同乘中的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生活中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时有发生,好意同乘中归因于施惠方的人身致害行为常常是双方事前预料不到的,良好情谊因此而破裂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受惠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根据在于同乘过程中施惠方对受惠方的人身存在一项注意义务,此时实际上已经存在一项潜在的“稀薄的法律关系”,一旦施惠方违反此项注意义务,则其好意同乘关系便进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第2次)重述第323条,如果行为人在不承担法定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基于自愿而对他人提供有偿或者无偿的服务,则在提供此种服务时应对他人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他如果违反此种义务并因此而引起他人损害,即应承担责任。可以说施惠者邀请或者允许搭乘的先行行为导致了其对受惠者的人身安全应该负担一项注意义务。 施惠方对其故意致害应该负责赔偿,这没有疑问。问题是施惠方注意义务的程度如何?也就是说施惠方究竟是应该对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负责?对此梅迪库斯教授并未予以区分,而是同意“受到伤害的搭车人有权要求驾车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王泽鉴教授也认为“尚难就现行规定导出无偿好意施惠者,仅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负责的一般原则。”“在搭便车的情形,好意施惠之人原则上仍应就其‘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对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其为好意施惠而为减轻,将其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可见,施惠方不能因为自己处于情谊施惠就可以减轻对同乘受惠方的注意义务,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仍然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包括故意和一般过失。 好意同乘中此种一般过错责任在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发展变迁过程。根据早期美国汽车客人规则(Automobile Guest Statutes),施惠关系中无偿搭车的客人可以基于司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请求损害赔偿。但是后来该规则广受质疑,被认为违反宪法平等权原则,目前美国大多数州“废除或者修改了限制加害人责任的准则……驾驶人对通常的过失也要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在讨论好意同乘中的施惠方责任时并未主张严格责任,实际上,同乘者与车外人作为受害人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上是不同的。同乘者基于其与驾驶人的特殊关系(合同关系或者好意施惠关系等等),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像车外行人等那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归责原则。1.3.3好意同乘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过错侵权责任赔偿范围实行全面赔偿原则。但是好意同乘中对施惠方在责任的范围上是否一律如此严格?何种情形下可能减轻? 根据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侵权行为法编第1979条的规定,“无偿搭乘他人的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交通工具提供者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目前实务界也多主张“无偿的同乘人遭受损害事故,基本规则是车主应当适当补偿,而不是赔偿。”笔者认为过错责任原则下不能对赔偿范围一概而论。 如果受惠方在同乘中对车辆的运行支配起了一定的影响力,就应该根据其影响力的比例,相应减轻施惠方的责任,此时可以视为同乘人存在与有过失。另外,在受惠方与有过失时,施惠方的责任也相应予以减轻。比如说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无照驾驶,搭乘醉汉驾驶的机动车,明知机动车有机械故障、车灯不亮等不适于行使的情形,搭乘人未系安全带等等,此时“其本身已属违反应注意照顾自己之法益之不真正义务,如因而发生车祸时,则搭乘人即为与有过失,”应该根据其与事故发生间的原因力的比例相应减轻施惠的驾车人的责任。实际上前述情形中都一定程度上有受惠方自甘冒险的因素,因为好意同乘中遵循的是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所以“虽然被害人明知危险而故犯之,也不宜使加害人完全免责,否则即有轻重失调之弊。”但是好意同乘本身不属于与有过失,须结合前述同乘的经过、同乘人在同乘中举动等予以综合认定,一旦构成与有过失,即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1条及法释[2003]20号第2条第1款的规定进行过失相抵。 最后,在坚持上述所有标准的前提下,还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衡平减轻施惠方的侵权责任,毕竟同乘人无偿受惠,判决施惠方全赔,在诚实信用和伦理感情上有失妥当性。但是这是在全面赔偿基础上的适当减轻,而非前述有观点主张的适当补偿。至于这种酌情减轻的幅度还应当总结审判经验,由最高法院统一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防止各地法院操作中差别过于悬殊。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出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因为如果一概过错全赔,施惠方就会不堪承受其重,会影响人们提供搭乘方便的互助积极性,反倒不利于这种绿色环保出行方式的推行。当然长远看,应当使“车上人员险”涵盖同乘人,同时同乘人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化解好意同乘中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 总之,对好意同乘行为我们应该妥善理清其中可能涉及的各种关系,划清其与无偿客运合同的区别。实务中纠纷处理结果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好意同乘的定性问题。
第2章 归因于承运人驾车过失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2.1对《合同法》第290条中承运人安全运送义务的理解 《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这一条包括了客运合同中对承运人安全及时运送义务的要求。可见客运合同的标的是运送旅客的行为,这也就是承运人的给付行为,而且承运人的这一给付具有运送行为和运送结果的双重要求。即不仅仅要有运送行为,这一运送行为还必须满足安全、及时的要求。 《合同法》第17章在这一一般规定之后又在客运合同专节规定中将承运人的上述给付义务具体化。比如第299条是对承运人及时运送义务的具体规定,而第301、302条对承运人救助义务和旅客伤亡责任承担的规定则是对安全运送义务的具体规定。 本文主要讨论承运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安全运送义务,对乘客人身权造成损害时,乘客所享有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通过对实务案例的总结,该问题具体地可以类型化为:第一、承运人驾车过失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二、归因于车外第三方的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承运人与车外第三方共同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四、承运人违反救助义务的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2.2承运人的营运资格、违规营运、责任主体等问题 诸如承运人的营运资格等边缘问题,影响到对客运合同的准确认定。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上文中讨论的好意同乘不属于《合同法》第302条第2款规定的无偿客运合同,除了前述施惠方和受惠方不具有订立合同的效果意思等形式原因以及根据社会一般价值取向好意同乘关系不属于可诉性民事法律关系等实质原因之外,“客运合同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设置都是针对营运性车辆而言的”。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10条也专门规定了客运经营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和许可程序。问题是:不具备此种经营许可证是否会影响客运合同的效力?乘客受伤害时是否仍能主张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司法实务中多主张此时客运合同无效,但是存在事实上的客运合同关系,并认为仍然适用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既然合同无效,就不应该适用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法院的此种做法造成了裁判推理的不通畅。笔者认为,上述行政法规对承运人营运资格的要求对应的是合同法上的管理性禁止性法规,其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对特定市场主体准入资格的控制,达到交通管理部门对营运活动的监管,以维护正常安全的营运秩序。不具备营运资格而从事营运活动只是会导致相应行政处罚等公法上的责任,并以此禁止其未来进一步从事营运活动,但是对已有的运输合同,法律并不否定其行为效力。因此营运资格的欠缺不能构成否定客运合同效力的理由,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10条也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所引致的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行政法规。 与此相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35条有客运机动车不得超载、货运车不得载客的规定,也属于此类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均不能据此否认客运合同的效力。实务中也有判决承认货运合同中客运合同的存在,实际上此时完全可以根据无名合同中合同联立的原理,认为分别存在一个货运合同和不具备营运资格的客运合同,对其分别适用法律,这样也就不会否定客运合同的存在。 可见,在道路交通运输领域,此类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并不对应乘客的请求权而产生,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范产生,这些规范不管规定于何部法律之中,基本上都是公法性的规范,是为配合公权主体对交通安全监督管制需要而设置的。乘客不享有一项请求承运人有章营运、不得超载等的权利,乘客只是在承运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自身损害时方可基于相应的归责原则请求损害赔偿。 经常引起争议的另一类问题是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认定。应该说明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对方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对方是不同的,对于违约责任应该严格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能向作为合同对方的承运人主张或者未取得营运资格但从事着营运业务的实际承运人主张。在违约责任中不能向承运人的司机等其他非合同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中对挂靠关系的处理也只能向作为合同主体的承运人主张,其具体的所有权人究竟是谁,对违约责任的追究不产生影响。2.3承运人驾车过失中的责任竞合问题2.3.1归责原则问题 客运合同中的责任竞合问题牵涉到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共同课题,为其交叉领域。法律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影响着其相邻的领域,承运人的驾车过失致乘客人身损害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合同法上规定的承运人的安全运送义务本来就是一项法定的义务,该义务不必明示于合同之中,而是自然订入客运合同,作为其内容。同时该法定义务是为保护乘客人身安全所设,根据《合同法》第53条,客运合同中免除造成乘客人身伤害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可以说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具有双重性质,其既可以作为合同上的法定义务,又是对合同相对人的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此时就可能构成请求权竞合。一般来说,违反此种义务,既导致了相对方履行利益的落空又产生了承运人对乘客合法的固有(既有)利益的责任问题。同样,“对合同相对人既有利益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性质差别问题进行讨论是有益的,而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也许最少。” 就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已如前述,《合同法》第302条在营运性车辆的违约责任问题上不区分有偿或者无偿,均一律适用对违约方的严格责任,该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也予以较好的贯彻,营运性车辆的运行过程中,“承运人同意他人搭乘,本身就负有安全将他人送到目的地的义务,而乘车人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其自愿承担风险,承运人同样不能置乘车人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不得以有偿无偿搭乘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顺便明确一点,合同法对营运车辆中乘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的归责原则是否区分有偿、无偿客运合同而做不同处理呢?有观点认为,根据体系解释,《合同法》第302条明确规定承运人的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合同,而第303条却没有类似于第302条第2款那样的准用条款,因此根据本章原则上调整有偿营利性客运合同的原则,第303条不能适用于无偿的客运合同。笔者认为该体系解释的结论值得商榷,第303条规定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对乘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责任,并没有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合同,过错责任属于归责原则之一般情形,除非法律明示,否则应该一律适用;同时过错责任又是最低限度的归责原则,对无偿客运合同也没法再规定更低的标准。承运人违约人身损害赔偿严格责任之根据何在?首先,承运人营利性营运(间或的无偿搭载不影响对其整体营利的判断),因利益驱动常常会不顾乘客的人身安全,其责任心应特别加重;其次,承运人是风险的制造者和最佳控制者,利之所归,害亦相随;最后,承运人和乘客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尤其是谈判能力差别悬殊,对乘客理应倾斜保护。 值得讨论的是承运人对乘客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什么?是否与违约人身损害赔偿一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民事责任中规定的受害人是“他人”,而且本条规定的适用情形是该作业“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车内乘客该条并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的也是“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可见该条项的归责原则也不适用于对车内乘客的赔偿。诚如学者所言:“道路机动车辆严格责任的核心领域都是对第三人的责任,即对非致损车辆内的人的责任。”已如上文所述,承运人的安全运送义务对应的是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所确认。可见承运人对乘客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为一般的过错责任。 总之,在归责原则问题上,好意同乘中施惠方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仅适用一般的过失责任。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对乘客违约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对乘客侵权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一般的过错责任。机动车对一般行人的侵权损害赔偿为过错推定责任。这种不同情形不同处理的做法是对当事人利益合理衡量的结果,符合区分车方与乘方、车方与行人及好意同乘方与客运乘客方等不同类型并做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原则。加藤一郎就曾说过:“交通事故中被害者是乘客还是乘客以外的第三者,利益关系就有不同”,理应不同对待。
2.3.2责任竞合及诉讼实现 《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学者认为该条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局限于违约造成侵权后果的情况”,因此适用本条时应该必要时进行目的性扩张的解释,使涵盖侵权造成违约的情况。在承运人驾车过失致乘客受害时,承运人违反了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造成对乘客履行利益以外的固有利益的侵害,为一项加害给付行为,同时构成了侵权。至于乘客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笔者认为其具体的规范基础为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1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有学者认为该条“仅针对不作为侵权做出了规定,因此在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不作为侵权时,就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该条第2款仅针对经营者不作为侵权,但是第1款只是一般适用于不作为侵权,其并不能完全排除对作为侵权的适用。在承运人驾车过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乘客受害时,理应同样适用该条。 责任竞合情形下,乘客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和赔偿范围均有所不同。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乘客单独选择一个请求权并不能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如我国现行法下,违约责任中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乘客又只有一次诉讼主张的机会,如何缓解此种紧张局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30条,乘客享有一个相对充分的选择机会,乘客在一审开庭前仍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34条第3款乘客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实际上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解决全部赔偿的问题。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虽然对承运人致害事实在法律上出现侵权法律关系和违约法律关系的双重评价,但是作为该法律关系基础的法律事实是单一的。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以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为标准的做法,在民事责任竞合领域不能避免重复诉讼的出现,从实体上也不符合“任何人不得通过损害他人而获利”的法谚。这时理论上可能的解决途径有二:第一,修改大陆法系的诉讼标的理论,采纳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事实出发型诉讼模式,基于案件的自然事实的同一性,只应以一个案件来对待,即“以案件事实的同一性或者诉因同一性为识别或者确定诉讼标的的标准。”第二、在坚持大陆法系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前提下,对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学说做出修正,采取请求权规范竞合说,认为“同一事实同时具备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之要件且均以损害赔偿为给付内容时,仅产生一项请求权,具有两个法律基础,其内容系结合两项基础规范而决定之。”在修正的请求权竞合学说之下,“请求权是单一的,其诉讼标的也是单一的……在此学说下,诉讼标的的单复数问题及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笔者认为大陆法系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仍可予以坚持,从实体法角度引入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即可完满解决问题,不管基于何种主张,乘客在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竞合时只能在一次诉讼中解决。2.4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规范及辅助性规范 根据学者的总结,请求权的规范体系为:请求权基础规范、请求权辅助规范及请求权对立规范。请求权基础规范是指涉及到如何规定请求权产生和取得的规范。请求权辅助规范主要是细化请求权基础规范中的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部分的规范。请求权对立规范是能够引起对立效果的规范。就乘客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其基础规范为《合同法》第302条、第113条;其对立规范为《合同法》第302条第1款后句:“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对赔偿项目,第113条只是做了概括的规定,其具体的细化需要参照辅助规范来完成,实务中对赔偿项目一般参照法释[2003]20号第17条以下的相应规定,通说也认为该司法解释所对应的能够转化为金钱可以计算的财产损失的项目,可以基于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实现。当然这些不同的请求权规范类型对应了不同的举证责任的配置:请求权基础规范需要由乘客主张,辅助规范亦然,对立规范则只能由承运人主张。 虽然解决了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的协调问题,尊重了既判力理论下“一事不再理”的消极效果。但是对一次诉讼中全面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相比,违约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个重大的差别是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前述辅助规范中的对应的法释[2003]20号第18条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在违约损害赔偿中实现。这种做法也加大了当事人在两种违约和侵权两种规范之间选择的可能代价。为此,有观点主张加大竞合情形下法官的释明权,在进行诉讼中充分告知当事人利弊,促使其理智选择。笔者认为这仍然是诉讼法上的权宜之计,仍非治本之策。一个积极的正面应对姿态应该是承认某些合同违约中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旅客运输合同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大”,有观点认为此时仍然只能选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来解决,而诚如有学者所言“一旦遇到某种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却并不同时构成侵权时,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说明责任竞合制度并非万能。”从比较法上看,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353条就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应予排除,除非违约同时导致身体伤害,以及合同或者违约属于易于产生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的类型。”英国判例法实践也总结了几种违约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第一、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享受快乐;第二、合同的目的就是要解除痛苦和麻烦;第三、因违约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直接造成的精神痛苦。”所以就客运合同而言,要求过失驾驶的承运人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有利于对乘客的全面赔偿。同时,人们认为“法律不应当试图在契约领域对侵权责任设置新的障碍,相反,他们应当逐渐消除契约与侵权救济的规则之间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区别”,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即为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德国民法典》2002年修改后将抚慰金条款从第847条提升到第253条第2款,这就使得其适用范围从侵权行为领域扩展到合同领域,此种深思熟虑又意味深长的做法向我们展示了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其传统做法的重大调整,值得借鉴。 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中的精神损害部分一般不予支持,法释[2001]7号也成为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障碍,亟待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总结审判经验,对客运合同以及其他极易导致合同相对人精神损害的合同予以类型化,并逐步上升为立法规定。 最后需要说明机动车自身原因造成乘客人身伤亡(如刹车失灵等),与承运人驾车过失属于同一情形,前者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规定的驾前安全技术性能检查义务,后者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的安全文明驾驶义务。相对于乘客而言,均属于出于承运人一方的过错致害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应采同一态度,所以本文对前者不单独分析,该部分的分析一并适用之。至于刹车失灵时可能存在的承运人对机动车出卖方的追偿责任问题,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暂不予涉及。 注释:
参见张丽彩、张永杰:“山东省交通事故现状分析及改善对策探讨”,载《山东交通科技》2007年第1期。
参见龚标、王长君、郑煜:“客运车辆特大事故特征及原因分析”,载《中国公共安全(综合版)》2006年第6期。
郑翔、张长青编著:《运输合同签订与风险控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第1版,前言部分。
二手分析是指某人所收集和加工的资料被另一个人所用——经常是处于不同的目的。参见[美]艾尔·巴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有学者将这种方法称为诉讼档案出发型的研究方法,并认为“法官的判决行动回应的是可以编辑的现实的生活情致”,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历史实践”,载《青年人大》2008年3月18日B8版。
通则式的解释是指试图解释某一类的情形或者事物,而不是某个个案。参见[美]艾尔·巴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第23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37页。
参见[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页。
郭力、史哲:“揭开古巴的面纱”,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参见任俊兵、岳燕林:“搭便车遇车祸引发的官司”,载《生活日报》1999年05月02日。张勇:“顺风车搭出的官司”,载《农村天地》2004年第6期。章法、桂明:“好意施惠者该不该为情谊买单”,载《法庭内外》2007年第12期。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13页。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42年(1967年)9月29日判决(判例时报497号第41页),转引自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00-101页。
在“刘建清、刘义宗、袁素、袁玖芳诉周木平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死者袁大成要求搭乘被告周木平的船只,周木平碍于情面,只好准许,法院认定本案构成好意同乘。参见(2002)广海法初字第357号。
参见冯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12期。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第30页。
参见[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E P. Dwyer Jr.,Automobiles: Guest Statutes: Proposal to Share Expenses of Social Trip, Michigan Law Review ? 1942.P157-159。另见BGHZ80,303,转引自[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相反的观点有:王泽鉴先生认为共同分担油费、邻居数人约定轮流开车上班等有偿情形属于契约,而非好意同乘,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参见臧恩富、许莹:“无偿搭车人身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载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7254。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199页。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在李赛娥与杨粤顺风车纠纷案中,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就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二审益阳市人民法院则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搭顺风车致残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参见张勇:“顺风车搭出的官司”,载《农村天地》2004年第6期。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21卷,第102、196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3页。
相同的观点参见洪彩霞:“论好意施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参见刘彤海、张辉:“好意同乘民事责任初探”,载http://www.law-thinker.com/news.php?id=1741。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无因管理说的主张参见周健美:“好意施惠行为及相关的责任承担”,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本部分论述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7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在讨论哪些社会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哪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过程中,民法学者及民事诉讼法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可诉性”这一标准,如“平等主体间可诉性的社会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纠纷的可诉性就是看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民事法律关系是可诉性的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可见在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属于民事纠纷这类重大的价值判断问题上,民法学界和民事诉讼法学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沟通不足及循环论证之嫌。另参见刘敏:“论纠纷的可诉性”,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此种程序的论证方法有着一定的理论背景。诚如阿列克西先生所言,实在法问题不可能避免价值判断问题,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而对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又难以避免无穷递归、循环论证或者武断终止等三重困境。此时通过程序规则的设计来寻求克服困境的途径,并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就颇为必要。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代译序第1-8页。
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法律管不着的,或不需要用法律,或不适宜用法律来规范的事项,构成一个所谓的“法外空间”。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杨婵:“好意施惠关系中的责任承担——从的个案角度分析”,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张平华:“民法中的四种行为范畴关系分析——以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为中心”,载《长江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参见邹海林:“我国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载《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0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200页。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323 (196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8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201页。
[美]爱德华·J·柯恩卡(EDWARD J. KIONKA):《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Andrew Kull,The Common Law Basis of Automobile Guest Statut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 1976.
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与交通灾害的消灭》,载张新宝主编《侵权法评论》2004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疑难问题暨司法解释适用研讨会综述”,载王利明、公丕祥主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问题释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另参见黄文娟:“驾车人‘好意同乘’出事故,法院判决担轻责”,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86080。
詹森林:《民事法理与判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解元利:“搭车出祸判赔119万,便车还敢让搭吗?”,载《大河报》2007年10月25日。
司法实务中也多承认好意同乘中过失相抵的存在,参见在“刘建清、刘义宗、袁素、袁玖芳诉周木平水 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案”,(2002)广海法初字第357号。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03页。
此种做法类似于社会学解释方法,偏重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及其目的的考量,司法裁判中也将社会效果作为重要的裁判考量因素。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8页。《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4条即规定:“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因该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应当酌情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另外参见孔祥武:“给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一个说法”,载《人民日报》2008年3月24日,第11版。
解元利:“搭车出祸判赔119万,便车还敢让搭吗?”,载《大河报》2007年10月25日。
参见陈界融:“客运合同中交通事故若干法律问题解析”,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参见“上诉人梁细初与被上诉人李文浩、李芬芳、李芷芳、李章达、李运明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759号。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另外参见:对《关于请明确对未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实施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函》的复函,国法函[2005]432号;《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明确对未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实施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复函的通知》,交公路发[2005]468号。
参见“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00)玉红民初字第108号。
参见“陈洪贝、陈子扬诉瑞昌市美茂出租车有限公司、程厚彪出租客运合同纠纷案”,(2005)瑞民初字第21号。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与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应,是因其从事一定的营业而应承担的防范危险的义务。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笔者不同意安全保障义务仅属于不作为侵权(消极侵权)行为作为义务来源的观点,详见下文论述。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参见“吴文仙等诉周卫明客运合同案”,(2002)金中一终字第599号。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89页。
参见白景富:“关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1期。有学者更加全面地总结修正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在机动车致行人交通事故案件采取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加10% 的无过错责任,参见王胜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制度的演变和立法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11期,2008年1月4日。
转引自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王利明:“再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2期。
周友军:“社会安全义务理论及其借鉴”,载《民商法论丛》(第34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有学者就正确地指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多为不作为,但没有一概否弃作为侵权,参见刘士国主编:《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关于请求权规范分类的相关问题,可参见朱岩:“论请求权”,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见“刘乾优诉刘宜执客运合同纠纷上诉案”,(2006)赣中民一终字第154号。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
如在“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承运人抗辩乘客“将右手搭放在车窗外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参见“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00)玉红民初字第108号。
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第168-169页。
黄金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CentralTrust v. Rafuse(1986)2SCR 147.
参见“金晓霞诉台州市城市环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2004)路民一初字第854号。 出处:《民商法论丛》2009年8月第1版 |
240331
原作者:王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
前 言 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四大基本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道路通车里程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道路交通环境日益恶化,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已成为交通系统中的两大问题。而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四分之三为行人、乘客及非机动车驾驶人等交通弱者。根据2006年召开的首届商用车发展高峰论坛,2006年客运方式运载乘客人数超过169亿,占整个人流的91%,而交通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道路交通运输发展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公路客运量占整个客运体系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2%左右,另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客运车辆事故在特大交通事故中所占比重近70%。可见,公路客运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方式,而将公路客运中的交通事故纠纷类型化并探讨其法律解决方案,现实意义就极为迫切。 就目前立法来看,虽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第17章对运输合同专章规定,但其规定较为简单,各国法律规定均较为简单,已成通例,但是承运人与乘客间的权利义务却颇为重要。就理论研究来看,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可能因为考虑到运输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领域合同制度的特殊性质,运输合同的具体制度一直很少被人涉足。” 笔者主要以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人民法院案例选》及中国交通安全网总结整理的相关70余个案例为对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主要是经由这些权威数据库、网站、案例选分类整理的真实判决书、对判决的简述或者生活事例,本文在选取时尽量选取真实完整的判决书作为实证分析对象,这样就减少了对二手资料做二手分析(secondary analysis)时对资料本身可信度的查证。初步接纳已有分类标准并对资料做细致的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在个案解释(idiographic)之上做一些类型化的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探讨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个由可定义的多样因素合成的最复杂的一般概念,单凭这种抽象的一般概念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的多样表现形态并对人们的行为做相对确定的指引,此时类型化的方法就成为沟通抽象概念与具体个案的桥梁。而类型化方法本身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为弥补其个别化方法的缺陷而对自然科学普遍化方法做的有益借鉴。 在已有理论预设分类标准的基础上,从个案到类型,笔者总结了新的类型化标准,并以之拟定本文的论题和篇章架构。实务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类案件中:第一、好意同乘中对同乘人的致害事件,第二、完全归因于承运人驾车过失的致害事件,第三、完全归因于车外第三方的致害事件,第四、承运人与车外第三方共同致害事件,第五、承运人违反救助义务时对乘客的致害事件。责任主体、责任形态、安全运送义务、救助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等一系列问题则贯穿前述论题之中。本文以公路客运合同为分析模型,研究客运合同中上述几类共同性问题。
第1章 好意同乘中的车主责任问题1.1讨论好意同乘问题的意义 在当前交通拥挤及汽车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好意同乘现象日渐普遍, 2007年12月28日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在《“节能减排,从我做起”倡议书》中也提出了“为减少机动车排放,提倡从住宅到单位的私家车主动安排车牌单双号分日行驶,停驶日和行驶日的车主相互搭乘”的行动方案。实际上,不管是出于环保的还是日常生活便利的考虑,相互搭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提倡的出行方式。在有的国家,顺路搭乘甚至成为一种常态的主要交通方式。人类是自私的,但好意同乘说明在没有利益关系下,人们也会关心其他人的生活和福祉,虽然这种关心不是经常性的;而互相搭乘说明人类找到了一种更高级的将利他和利己有机结合起来的行为方式。 与此同时,近年来好意同乘纠纷越来越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好意同乘到底是纯粹的生活事实还是民事法律事实?好意同乘与无偿客运合同的关系是什么?发生事故时车主对同乘人是否是一律“适当补偿”?在讨论客运合同中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时,上述问题难以回避,尤其是好意同乘问题和客运合同中的无偿客运合同又交织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这属于事实上的客运合同关系,有学者认为属于无偿客运合同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属于无名合同、可以类推适用客运合同的规定。1.2好意同乘的概念、特点及性质1.2.1好意同乘的概念和特点 好意同乘是指乘车人在运行供用者好意并无偿地邀请或允许下同乘于运行供用者之车的现象。好意同乘是一种典型的生活互助行为,这种行为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好意同乘是理论界的通用说法,在实践中也称为“搭便车”、“搭顺风车”、“免费搭乘”等等,笔者认为“免费搭乘”的说法容易与无偿客运合同混淆,本文的立场之一就是区分两者,故不采“免费搭乘”的说法,仍用“好意同乘”的表述。 好意同乘中提供便利方的行为动机是出于情谊,也就是为了增进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和搭乘人的情谊,给予搭乘人一定的便利。好意同乘关系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无偿性,即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不直接或者间接追求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放弃经济利益,单方面提供方便;第二、好意性,即提供方便的一方伴随着利他性动机,是一种利己的过程中伴随利他的行为;第三、不具有契约性,即双方之间的好意协定关系是一种非法律行为的协定关系,在当事人之间没有法律性的意思表示,因而也不具有规范性的约束力,即使有给付行为的外观,也不具有合同意义上的债务履行,而只是任意的给付。上述特点必须同时具备,而核心特点是不具有契约性。不能单纯以无偿性推论系属好意同乘,而非法律行为,因为法律上也承认无偿客运合同的存在。 就好意同乘的概念应该明确的是:第一、好意同乘不以一方主动提供为限,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搭乘人主动请求对方给予便利的现象颇为常见,其与主动邀请同乘不应有法律评价上的不同。我国司法实务中也是采取类似态度。第二、好意同乘不能包括强行性乘坐,也不能包括无偿偷坐。 “经验的现实证明自身是一种茫无边际的杂多”,基于事实特征的此种无限性与人们对事实认知有限性的矛盾,人们所采用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属于“带有开放结构的语言”,概念的核心地带意义是清晰的,而越趋边缘地带意义越为模糊。好意同乘概念亦然。符合前面三项特点的属于“没有疑问的”好意同乘,结合前述特点,有如下“模棱两可的”情形应予说明:第一、好意同乘在搭乘者支付或者分担汽油费的情况下是否就成为有偿客运合同?对此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争议很大,但是多数观点采否定说,主张此时仍然属于好意同乘。这种情形下,分担油费等形式只是象征性地补偿,不构成对价给付,对驾车人的劳务仍属免费,仍然构成好意同乘。第二、好意同乘是否需要具备顺路同乘的特点?即是否以搭乘人与司机或者车主的目的地相同而顺路搭乘为必要?车主或者实际驾驶人要去的目的地不是搭乘人事先指定的,是否就不构成好意同乘?有学者就认为此时应该以无偿委托合同认定。笔者认为此种专程运送仍然属于单方施惠,除非双方明示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否则不能当然地认为构成事实上的契约关系。1.2.2好意同乘的性质 上述对好意同乘的分析一直是对此种生活现象的基本描述,而任何分析描述不论多么详尽都不能穷尽现实在内容上的多样性。好意同乘实质上的法律性质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实际上对好意同乘中车主责任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好意同乘行为民法定性的基础上的。明确了好意同乘的民法性质,才能恰当地处理纠纷,学界对此虽然讨论不多,但是对此前提性问题还是具有普遍共识的。1.2.2.1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 好意同乘是情谊行为的一种。实际上情谊行为也不是一个非常准确和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它产生于德国判例,在《德国民法典》上对其无明文规定,是一种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的行为,不能依法产生后果,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社会层面上的行为”,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好意施惠关系”或者“施惠关系”,其名异而实同。 作为情谊行为的好意同乘并不是一种法律行为,也就不可能构成客运合同。其主要原因是法律行为乃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核心是意思表示,而好意同乘中的一方是处于增进相互间的情谊而提供搭乘的方便,情谊增进是其行为的动机。“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效果意思)是构成合同的实质性因素,并非所有的协议都是合同”。而如前所述,虽然一方有邀请或者允许的表示,但是情谊的考虑是其出发点。在事实层面上,同乘人和车主之间存在一项合意,但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意,只是生活意义上的合意。此种合意不具有意思表示中基本的构成要素——效果意思,即没有受其拘束的意思,可见并不能构成法律行为。司法实务上对法律行为和没有拘束力的情谊行为的区分也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判断标准的。“一项情谊行为,只有在给付者具有法律上受约束的意思时,才具有法律行为的性质。这种意思,表现为给付者有意使他的行为获得法律行为上的效力……,亦即他想引起某种法律约束力……,而且受领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受领这种给付的。如果不存在这种意思,则不得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来评价这种行为。”好意同乘只是基于情谊而发生的一般社会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可见并非所有的合意都构成合同行为,实际上合同内容也不一定均须合意达成,只是合同中的要素须此而已。合同与合意并非完全一致,有法律意义的合意方可能构成合同。 因为好意同乘根本不构成一项法律行为,那么主张好意同乘关系类推适用客运合同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我国《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可见,只有无名合同才可能适用与其最相类似的相应有名合同的规定,好意同乘中不存在一项合同,甚至连法律行为都不成立,这项非法律行为和客运合同不具有基本的性质上的类似性。类推适用说是没有根据的。 有观点认为好意同乘构成事实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一旦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不管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确立、变更或者消灭某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都会基于法律的规定,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事实行为与好意同乘、乃至与情谊行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具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事实行为而言,其法律效果的发生不问是否为当事人所意欲,法律对其采取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但在好意同乘关系中,法律并没有对当事人之间的此种关系配置任何权利义务,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于此等行为,当事人既无受其拘束的意思,不能由之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可见,法律对好意同乘行为与事实行为采取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既然好意同乘根本不属于事实行为,主张好意同乘属于无因管理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提供搭乘者根本不具有发生法律行为的意思,法律对其也保持沉默,此时更谈不上管理意思的存在了。不能因为好意同乘与无因管理同具有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特点,就理所当然地将其在性质上归为一类。 以上是从概念和规范出发对好意同乘性质做的逻辑分析。更进一步看,好意同乘的性质本身属于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因为讨论能否将好意同乘这一生活事实上升为民事法律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面向生活世界进行民法解释的过程”,此种本体论解释结论的不同直接影响对好意同乘的性质界定,而不同的解释结论直接关系到将好意同乘放在民法层面规范还是交由交往道德规范,这就“直接涉及当事人之间利益安排”。 好意同乘关系虽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至少就今天的价值取向来说,该种社会关系“不具有可诉性”,也就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好意同乘这一生活事实也不能上升为民事法律事实。可诉性究竟是做出这一价值判断结论的依据还是该结论的当然结果,尚存疑问,这也显示了探讨价值判断问题时避免循环论证的难度。一个更现实的路径是交由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基于其所处社会的价值取向遵循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做出决定。这一方法既可以弥补可诉性标准循环论证之弊,又可以因应道德规则本身的变动性及其与法律规则边界的变动性。1.2.2.2好意同乘并非一概属于“法外空间” 上文对将好意同乘定性为情谊行为,并论证其不属于法律行为、不构成客运合同;不属于事实行为,也不构成无因管理。但好意同乘是否只能“由当事人的私人友谊调整”,“不由法律调整”,“不能由法律救济”呢?好意同乘关系中的双方不会对法律约束作实际思考,除非出了麻烦,麻烦一般出在同乘人在同乘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情形。 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不会支持受惠方行使合同中的给付请求权;施惠方也不会产生像无因管理中管理人要求本人偿还管理费用的问题;受惠方受有利益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也不会出现施惠方向受惠方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情形。但是在同乘过程中一旦施惠方对受惠方有加害行为,则可能出现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虽然法律规范调整的事项限于人际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有些人际关系只能交由道德习俗去调整。就民法来看,民事法律事实只不过是立法者将生活事实中无规范意义的部分剪裁掉并将剩余部分运用民法语言加以转述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民事法律事实不过是对生活事实进行的一场“圈地运动”。民事法律事实也就是在法律评价的指引下对生活事实的一部分的撷取。诚如狄尔泰所言:“人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总是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创造出来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好意同乘本身而言,施惠者基于增进情谊的考虑给予受惠者便利。就法律对好意同乘的评价而言,立法者对好意同乘行为的态度也反应了这一问题在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属于情谊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立法者对其在法律评价上的结论是该生活事实不适合用法律来调整,而只能归由道德习俗调整,他律性的调整方式只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时时受监视的状态。法律的沉默不语是对生活的最大尊重,也是立法者对自己理性有限性的最好理解。我们上文分析的好意同乘关系不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结论也是针对常态情形而言的,而且以考查其是否构成合同法律行为为重点。结论是在常态下的好意同乘行为属于“法外空间”。 好意同乘中“施惠方的承诺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对其承诺的不实现或不完全实现均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而仅仅是道德义务而已。但是,施惠方一旦开始进行施惠行为,他就必然负有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注意和保护义务,这是与主行为附随而来的义务,并不因施惠行为的好意、无偿的性质而得免除或减轻。”因此施惠方违反注意义务导致受惠方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施惠方的行为就可能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成为侵权行为。此时好意同乘就受法律调整,就成为法内空间了。至于此时的归责原则问题将在下文好意同乘的法律效力部分分析。 可见,对好意同乘关系的法律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常态与非常态,区分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正如以上分析,对好意同乘关系的定性是要做类型化讨论的,没法一概而论。同时,基于其可能的性质均能在现有的法内或者法外空间找到归宿,所以本文不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对好意同乘关系“法律完全不愿涉足”的观点。1.3对好意同乘法律效力的分析1.3.1好意同乘中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前所述,学界通说认为好意同乘关系中施惠方与受惠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受惠方对施惠方不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同时,受惠方的获益也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施惠方明知自己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仍然提供搭乘的便利,其对受惠方不得请求不当得利返还。 基于前述,受惠方对施惠方不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在施惠方违反先前的承诺,不提供搭乘的便利时,受惠方也不得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增进情谊的社交行为不宜置于法律的严密监督之下。问题是受惠方是否可以请求赔偿自己的信赖利益的损失乃至纯粹经济损失?学者一般认为此时的确可能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该项请求权的成立以施惠方的行为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故意悖于善良风俗原则加损害为必要,在此不赘。1.3.2好意同乘中的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生活中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时有发生,好意同乘中归因于施惠方的人身致害行为常常是双方事前预料不到的,良好情谊因此而破裂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受惠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根据在于同乘过程中施惠方对受惠方的人身存在一项注意义务,此时实际上已经存在一项潜在的“稀薄的法律关系”,一旦施惠方违反此项注意义务,则其好意同乘关系便进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第2次)重述第323条,如果行为人在不承担法定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基于自愿而对他人提供有偿或者无偿的服务,则在提供此种服务时应对他人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他如果违反此种义务并因此而引起他人损害,即应承担责任。可以说施惠者邀请或者允许搭乘的先行行为导致了其对受惠者的人身安全应该负担一项注意义务。 施惠方对其故意致害应该负责赔偿,这没有疑问。问题是施惠方注意义务的程度如何?也就是说施惠方究竟是应该对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负责?对此梅迪库斯教授并未予以区分,而是同意“受到伤害的搭车人有权要求驾车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王泽鉴教授也认为“尚难就现行规定导出无偿好意施惠者,仅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负责的一般原则。”“在搭便车的情形,好意施惠之人原则上仍应就其‘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对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其为好意施惠而为减轻,将其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可见,施惠方不能因为自己处于情谊施惠就可以减轻对同乘受惠方的注意义务,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仍然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包括故意和一般过失。 好意同乘中此种一般过错责任在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发展变迁过程。根据早期美国汽车客人规则(Automobile Guest Statutes),施惠关系中无偿搭车的客人可以基于司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请求损害赔偿。但是后来该规则广受质疑,被认为违反宪法平等权原则,目前美国大多数州“废除或者修改了限制加害人责任的准则……驾驶人对通常的过失也要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在讨论好意同乘中的施惠方责任时并未主张严格责任,实际上,同乘者与车外人作为受害人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上是不同的。同乘者基于其与驾驶人的特殊关系(合同关系或者好意施惠关系等等),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像车外行人等那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归责原则。1.3.3好意同乘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过错侵权责任赔偿范围实行全面赔偿原则。但是好意同乘中对施惠方在责任的范围上是否一律如此严格?何种情形下可能减轻? 根据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侵权行为法编第1979条的规定,“无偿搭乘他人的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交通工具提供者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目前实务界也多主张“无偿的同乘人遭受损害事故,基本规则是车主应当适当补偿,而不是赔偿。”笔者认为过错责任原则下不能对赔偿范围一概而论。 如果受惠方在同乘中对车辆的运行支配起了一定的影响力,就应该根据其影响力的比例,相应减轻施惠方的责任,此时可以视为同乘人存在与有过失。另外,在受惠方与有过失时,施惠方的责任也相应予以减轻。比如说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无照驾驶,搭乘醉汉驾驶的机动车,明知机动车有机械故障、车灯不亮等不适于行使的情形,搭乘人未系安全带等等,此时“其本身已属违反应注意照顾自己之法益之不真正义务,如因而发生车祸时,则搭乘人即为与有过失,”应该根据其与事故发生间的原因力的比例相应减轻施惠的驾车人的责任。实际上前述情形中都一定程度上有受惠方自甘冒险的因素,因为好意同乘中遵循的是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所以“虽然被害人明知危险而故犯之,也不宜使加害人完全免责,否则即有轻重失调之弊。”但是好意同乘本身不属于与有过失,须结合前述同乘的经过、同乘人在同乘中举动等予以综合认定,一旦构成与有过失,即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1条及法释[2003]20号第2条第1款的规定进行过失相抵。 最后,在坚持上述所有标准的前提下,还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衡平减轻施惠方的侵权责任,毕竟同乘人无偿受惠,判决施惠方全赔,在诚实信用和伦理感情上有失妥当性。但是这是在全面赔偿基础上的适当减轻,而非前述有观点主张的适当补偿。至于这种酌情减轻的幅度还应当总结审判经验,由最高法院统一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防止各地法院操作中差别过于悬殊。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出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因为如果一概过错全赔,施惠方就会不堪承受其重,会影响人们提供搭乘方便的互助积极性,反倒不利于这种绿色环保出行方式的推行。当然长远看,应当使“车上人员险”涵盖同乘人,同时同乘人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化解好意同乘中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 总之,对好意同乘行为我们应该妥善理清其中可能涉及的各种关系,划清其与无偿客运合同的区别。实务中纠纷处理结果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好意同乘的定性问题。
第2章 归因于承运人驾车过失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2.1对《合同法》第290条中承运人安全运送义务的理解 《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这一条包括了客运合同中对承运人安全及时运送义务的要求。可见客运合同的标的是运送旅客的行为,这也就是承运人的给付行为,而且承运人的这一给付具有运送行为和运送结果的双重要求。即不仅仅要有运送行为,这一运送行为还必须满足安全、及时的要求。 《合同法》第17章在这一一般规定之后又在客运合同专节规定中将承运人的上述给付义务具体化。比如第299条是对承运人及时运送义务的具体规定,而第301、302条对承运人救助义务和旅客伤亡责任承担的规定则是对安全运送义务的具体规定。 本文主要讨论承运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安全运送义务,对乘客人身权造成损害时,乘客所享有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诉讼实现。通过对实务案例的总结,该问题具体地可以类型化为:第一、承运人驾车过失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二、归因于车外第三方的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承运人与车外第三方共同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第四、承运人违反救助义务的致害事件中乘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2.2承运人的营运资格、违规营运、责任主体等问题 诸如承运人的营运资格等边缘问题,影响到对客运合同的准确认定。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上文中讨论的好意同乘不属于《合同法》第302条第2款规定的无偿客运合同,除了前述施惠方和受惠方不具有订立合同的效果意思等形式原因以及根据社会一般价值取向好意同乘关系不属于可诉性民事法律关系等实质原因之外,“客运合同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设置都是针对营运性车辆而言的”。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10条也专门规定了客运经营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和许可程序。问题是:不具备此种经营许可证是否会影响客运合同的效力?乘客受伤害时是否仍能主张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司法实务中多主张此时客运合同无效,但是存在事实上的客运合同关系,并认为仍然适用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既然合同无效,就不应该适用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法院的此种做法造成了裁判推理的不通畅。笔者认为,上述行政法规对承运人营运资格的要求对应的是合同法上的管理性禁止性法规,其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对特定市场主体准入资格的控制,达到交通管理部门对营运活动的监管,以维护正常安全的营运秩序。不具备营运资格而从事营运活动只是会导致相应行政处罚等公法上的责任,并以此禁止其未来进一步从事营运活动,但是对已有的运输合同,法律并不否定其行为效力。因此营运资格的欠缺不能构成否定客运合同效力的理由,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10条也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所引致的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行政法规。 与此相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35条有客运机动车不得超载、货运车不得载客的规定,也属于此类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均不能据此否认客运合同的效力。实务中也有判决承认货运合同中客运合同的存在,实际上此时完全可以根据无名合同中合同联立的原理,认为分别存在一个货运合同和不具备营运资格的客运合同,对其分别适用法律,这样也就不会否定客运合同的存在。 可见,在道路交通运输领域,此类管理性禁止性规范并不对应乘客的请求权而产生,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范产生,这些规范不管规定于何部法律之中,基本上都是公法性的规范,是为配合公权主体对交通安全监督管制需要而设置的。乘客不享有一项请求承运人有章营运、不得超载等的权利,乘客只是在承运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自身损害时方可基于相应的归责原则请求损害赔偿。 经常引起争议的另一类问题是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认定。应该说明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对方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对方是不同的,对于违约责任应该严格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能向作为合同对方的承运人主张或者未取得营运资格但从事着营运业务的实际承运人主张。在违约责任中不能向承运人的司机等其他非合同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中对挂靠关系的处理也只能向作为合同主体的承运人主张,其具体的所有权人究竟是谁,对违约责任的追究不产生影响。2.3承运人驾车过失中的责任竞合问题2.3.1归责原则问题 客运合同中的责任竞合问题牵涉到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共同课题,为其交叉领域。法律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影响着其相邻的领域,承运人的驾车过失致乘客人身损害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合同法上规定的承运人的安全运送义务本来就是一项法定的义务,该义务不必明示于合同之中,而是自然订入客运合同,作为其内容。同时该法定义务是为保护乘客人身安全所设,根据《合同法》第53条,客运合同中免除造成乘客人身伤害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可以说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具有双重性质,其既可以作为合同上的法定义务,又是对合同相对人的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此时就可能构成请求权竞合。一般来说,违反此种义务,既导致了相对方履行利益的落空又产生了承运人对乘客合法的固有(既有)利益的责任问题。同样,“对合同相对人既有利益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性质差别问题进行讨论是有益的,而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也许最少。” 就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已如前述,《合同法》第302条在营运性车辆的违约责任问题上不区分有偿或者无偿,均一律适用对违约方的严格责任,该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也予以较好的贯彻,营运性车辆的运行过程中,“承运人同意他人搭乘,本身就负有安全将他人送到目的地的义务,而乘车人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其自愿承担风险,承运人同样不能置乘车人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不得以有偿无偿搭乘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顺便明确一点,合同法对营运车辆中乘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的归责原则是否区分有偿、无偿客运合同而做不同处理呢?有观点认为,根据体系解释,《合同法》第302条明确规定承运人的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合同,而第303条却没有类似于第302条第2款那样的准用条款,因此根据本章原则上调整有偿营利性客运合同的原则,第303条不能适用于无偿的客运合同。笔者认为该体系解释的结论值得商榷,第303条规定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对乘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责任,并没有区分有偿还是无偿合同,过错责任属于归责原则之一般情形,除非法律明示,否则应该一律适用;同时过错责任又是最低限度的归责原则,对无偿客运合同也没法再规定更低的标准。承运人违约人身损害赔偿严格责任之根据何在?首先,承运人营利性营运(间或的无偿搭载不影响对其整体营利的判断),因利益驱动常常会不顾乘客的人身安全,其责任心应特别加重;其次,承运人是风险的制造者和最佳控制者,利之所归,害亦相随;最后,承运人和乘客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尤其是谈判能力差别悬殊,对乘客理应倾斜保护。 值得讨论的是承运人对乘客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什么?是否与违约人身损害赔偿一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民事责任中规定的受害人是“他人”,而且本条规定的适用情形是该作业“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车内乘客该条并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的也是“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可见该条项的归责原则也不适用于对车内乘客的赔偿。诚如学者所言:“道路机动车辆严格责任的核心领域都是对第三人的责任,即对非致损车辆内的人的责任。”已如上文所述,承运人的安全运送义务对应的是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所确认。可见承运人对乘客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为一般的过错责任。 总之,在归责原则问题上,好意同乘中施惠方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仅适用一般的过失责任。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对乘客违约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对乘客侵权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一般的过错责任。机动车对一般行人的侵权损害赔偿为过错推定责任。这种不同情形不同处理的做法是对当事人利益合理衡量的结果,符合区分车方与乘方、车方与行人及好意同乘方与客运乘客方等不同类型并做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原则。加藤一郎就曾说过:“交通事故中被害者是乘客还是乘客以外的第三者,利益关系就有不同”,理应不同对待。
2.3.2责任竞合及诉讼实现 《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学者认为该条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局限于违约造成侵权后果的情况”,因此适用本条时应该必要时进行目的性扩张的解释,使涵盖侵权造成违约的情况。在承运人驾车过失致乘客受害时,承运人违反了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造成对乘客履行利益以外的固有利益的侵害,为一项加害给付行为,同时构成了侵权。至于乘客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笔者认为其具体的规范基础为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1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有学者认为该条“仅针对不作为侵权做出了规定,因此在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不作为侵权时,就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该条第2款仅针对经营者不作为侵权,但是第1款只是一般适用于不作为侵权,其并不能完全排除对作为侵权的适用。在承运人驾车过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乘客受害时,理应同样适用该条。 责任竞合情形下,乘客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和赔偿范围均有所不同。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乘客单独选择一个请求权并不能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如我国现行法下,违约责任中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乘客又只有一次诉讼主张的机会,如何缓解此种紧张局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30条,乘客享有一个相对充分的选择机会,乘客在一审开庭前仍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34条第3款乘客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实际上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解决全部赔偿的问题。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虽然对承运人致害事实在法律上出现侵权法律关系和违约法律关系的双重评价,但是作为该法律关系基础的法律事实是单一的。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以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为标准的做法,在民事责任竞合领域不能避免重复诉讼的出现,从实体上也不符合“任何人不得通过损害他人而获利”的法谚。这时理论上可能的解决途径有二:第一,修改大陆法系的诉讼标的理论,采纳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事实出发型诉讼模式,基于案件的自然事实的同一性,只应以一个案件来对待,即“以案件事实的同一性或者诉因同一性为识别或者确定诉讼标的的标准。”第二、在坚持大陆法系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前提下,对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学说做出修正,采取请求权规范竞合说,认为“同一事实同时具备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之要件且均以损害赔偿为给付内容时,仅产生一项请求权,具有两个法律基础,其内容系结合两项基础规范而决定之。”在修正的请求权竞合学说之下,“请求权是单一的,其诉讼标的也是单一的……在此学说下,诉讼标的的单复数问题及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笔者认为大陆法系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仍可予以坚持,从实体法角度引入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即可完满解决问题,不管基于何种主张,乘客在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竞合时只能在一次诉讼中解决。2.4乘客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规范及辅助性规范 根据学者的总结,请求权的规范体系为:请求权基础规范、请求权辅助规范及请求权对立规范。请求权基础规范是指涉及到如何规定请求权产生和取得的规范。请求权辅助规范主要是细化请求权基础规范中的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部分的规范。请求权对立规范是能够引起对立效果的规范。就乘客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其基础规范为《合同法》第302条、第113条;其对立规范为《合同法》第302条第1款后句:“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对赔偿项目,第113条只是做了概括的规定,其具体的细化需要参照辅助规范来完成,实务中对赔偿项目一般参照法释[2003]20号第17条以下的相应规定,通说也认为该司法解释所对应的能够转化为金钱可以计算的财产损失的项目,可以基于违约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实现。当然这些不同的请求权规范类型对应了不同的举证责任的配置:请求权基础规范需要由乘客主张,辅助规范亦然,对立规范则只能由承运人主张。 虽然解决了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的协调问题,尊重了既判力理论下“一事不再理”的消极效果。但是对一次诉讼中全面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相比,违约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个重大的差别是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前述辅助规范中的对应的法释[2003]20号第18条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在违约损害赔偿中实现。这种做法也加大了当事人在两种违约和侵权两种规范之间选择的可能代价。为此,有观点主张加大竞合情形下法官的释明权,在进行诉讼中充分告知当事人利弊,促使其理智选择。笔者认为这仍然是诉讼法上的权宜之计,仍非治本之策。一个积极的正面应对姿态应该是承认某些合同违约中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旅客运输合同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大”,有观点认为此时仍然只能选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来解决,而诚如有学者所言“一旦遇到某种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却并不同时构成侵权时,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说明责任竞合制度并非万能。”从比较法上看,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353条就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应予排除,除非违约同时导致身体伤害,以及合同或者违约属于易于产生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的类型。”英国判例法实践也总结了几种违约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第一、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享受快乐;第二、合同的目的就是要解除痛苦和麻烦;第三、因违约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直接造成的精神痛苦。”所以就客运合同而言,要求过失驾驶的承运人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有利于对乘客的全面赔偿。同时,人们认为“法律不应当试图在契约领域对侵权责任设置新的障碍,相反,他们应当逐渐消除契约与侵权救济的规则之间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区别”,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即为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德国民法典》2002年修改后将抚慰金条款从第847条提升到第253条第2款,这就使得其适用范围从侵权行为领域扩展到合同领域,此种深思熟虑又意味深长的做法向我们展示了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其传统做法的重大调整,值得借鉴。 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中的精神损害部分一般不予支持,法释[2001]7号也成为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障碍,亟待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总结审判经验,对客运合同以及其他极易导致合同相对人精神损害的合同予以类型化,并逐步上升为立法规定。 最后需要说明机动车自身原因造成乘客人身伤亡(如刹车失灵等),与承运人驾车过失属于同一情形,前者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规定的驾前安全技术性能检查义务,后者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的安全文明驾驶义务。相对于乘客而言,均属于出于承运人一方的过错致害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应采同一态度,所以本文对前者不单独分析,该部分的分析一并适用之。至于刹车失灵时可能存在的承运人对机动车出卖方的追偿责任问题,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暂不予涉及。 注释:
参见张丽彩、张永杰:“山东省交通事故现状分析及改善对策探讨”,载《山东交通科技》2007年第1期。
参见龚标、王长君、郑煜:“客运车辆特大事故特征及原因分析”,载《中国公共安全(综合版)》2006年第6期。
郑翔、张长青编著:《运输合同签订与风险控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第1版,前言部分。
二手分析是指某人所收集和加工的资料被另一个人所用——经常是处于不同的目的。参见[美]艾尔·巴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有学者将这种方法称为诉讼档案出发型的研究方法,并认为“法官的判决行动回应的是可以编辑的现实的生活情致”,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历史实践”,载《青年人大》2008年3月18日B8版。
通则式的解释是指试图解释某一类的情形或者事物,而不是某个个案。参见[美]艾尔·巴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第23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37页。
参见[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页。
郭力、史哲:“揭开古巴的面纱”,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参见任俊兵、岳燕林:“搭便车遇车祸引发的官司”,载《生活日报》1999年05月02日。张勇:“顺风车搭出的官司”,载《农村天地》2004年第6期。章法、桂明:“好意施惠者该不该为情谊买单”,载《法庭内外》2007年第12期。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13页。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42年(1967年)9月29日判决(判例时报497号第41页),转引自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00-101页。
在“刘建清、刘义宗、袁素、袁玖芳诉周木平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死者袁大成要求搭乘被告周木平的船只,周木平碍于情面,只好准许,法院认定本案构成好意同乘。参见(2002)广海法初字第357号。
参见冯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12期。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涂纪亮译,第30页。
参见[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E P. Dwyer Jr.,Automobiles: Guest Statutes: Proposal to Share Expenses of Social Trip, Michigan Law Review ? 1942.P157-159。另见BGHZ80,303,转引自[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相反的观点有:王泽鉴先生认为共同分担油费、邻居数人约定轮流开车上班等有偿情形属于契约,而非好意同乘,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参见臧恩富、许莹:“无偿搭车人身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载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7254。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199页。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在李赛娥与杨粤顺风车纠纷案中,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就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二审益阳市人民法院则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搭顺风车致残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参见张勇:“顺风车搭出的官司”,载《农村天地》2004年第6期。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21卷,第102、196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3页。
相同的观点参见洪彩霞:“论好意施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参见刘彤海、张辉:“好意同乘民事责任初探”,载http://www.law-thinker.com/news.php?id=1741。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无因管理说的主张参见周健美:“好意施惠行为及相关的责任承担”,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本部分论述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7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在讨论哪些社会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哪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过程中,民法学者及民事诉讼法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可诉性”这一标准,如“平等主体间可诉性的社会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纠纷的可诉性就是看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民事法律关系是可诉性的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可见在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属于民事纠纷这类重大的价值判断问题上,民法学界和民事诉讼法学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沟通不足及循环论证之嫌。另参见刘敏:“论纠纷的可诉性”,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此种程序的论证方法有着一定的理论背景。诚如阿列克西先生所言,实在法问题不可能避免价值判断问题,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而对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又难以避免无穷递归、循环论证或者武断终止等三重困境。此时通过程序规则的设计来寻求克服困境的途径,并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就颇为必要。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代译序第1-8页。
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法律管不着的,或不需要用法律,或不适宜用法律来规范的事项,构成一个所谓的“法外空间”。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杨婵:“好意施惠关系中的责任承担——从的个案角度分析”,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张平华:“民法中的四种行为范畴关系分析——以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为中心”,载《长江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参见邹海林:“我国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载《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0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200页。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323 (196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第158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201页。
[美]爱德华·J·柯恩卡(EDWARD J. KIONKA):《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Andrew Kull,The Common Law Basis of Automobile Guest Statut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 1976.
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与交通灾害的消灭》,载张新宝主编《侵权法评论》2004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疑难问题暨司法解释适用研讨会综述”,载王利明、公丕祥主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问题释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另参见黄文娟:“驾车人‘好意同乘’出事故,法院判决担轻责”,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86080。
詹森林:《民事法理与判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解元利:“搭车出祸判赔119万,便车还敢让搭吗?”,载《大河报》2007年10月25日。
司法实务中也多承认好意同乘中过失相抵的存在,参见在“刘建清、刘义宗、袁素、袁玖芳诉周木平水 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案”,(2002)广海法初字第357号。
参见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第103页。
此种做法类似于社会学解释方法,偏重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及其目的的考量,司法裁判中也将社会效果作为重要的裁判考量因素。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8页。《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4条即规定:“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因该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应当酌情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另外参见孔祥武:“给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一个说法”,载《人民日报》2008年3月24日,第11版。
解元利:“搭车出祸判赔119万,便车还敢让搭吗?”,载《大河报》2007年10月25日。
参见陈界融:“客运合同中交通事故若干法律问题解析”,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参见“上诉人梁细初与被上诉人李文浩、李芬芳、李芷芳、李章达、李运明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759号。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另外参见:对《关于请明确对未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实施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函》的复函,国法函[2005]432号;《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明确对未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实施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复函的通知》,交公路发[2005]468号。
参见“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00)玉红民初字第108号。
参见“陈洪贝、陈子扬诉瑞昌市美茂出租车有限公司、程厚彪出租客运合同纠纷案”,(2005)瑞民初字第21号。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运送义务与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应,是因其从事一定的营业而应承担的防范危险的义务。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笔者不同意安全保障义务仅属于不作为侵权(消极侵权)行为作为义务来源的观点,详见下文论述。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参见“吴文仙等诉周卫明客运合同案”,(2002)金中一终字第599号。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89页。
参见白景富:“关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1期。有学者更加全面地总结修正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在机动车致行人交通事故案件采取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加10% 的无过错责任,参见王胜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制度的演变和立法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11期,2008年1月4日。
转引自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王利明:“再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2期。
周友军:“社会安全义务理论及其借鉴”,载《民商法论丛》(第34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有学者就正确地指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多为不作为,但没有一概否弃作为侵权,参见刘士国主编:《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关于请求权规范分类的相关问题,可参见朱岩:“论请求权”,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见“刘乾优诉刘宜执客运合同纠纷上诉案”,(2006)赣中民一终字第154号。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
如在“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承运人抗辩乘客“将右手搭放在车窗外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参见“陶双玉与周子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2000)玉红民初字第108号。
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第168-169页。
黄金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CentralTrust v. Rafuse(1986)2SCR 147.
参见“金晓霞诉台州市城市环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2004)路民一初字第854号。 出处:《民商法论丛》2009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