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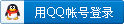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原作者:冯恺
五、对两类特别胎儿损害赔偿问题的评述
从胎儿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看,存在两类特别的情形:一类为夫妻由于身体、经济或工作等方面缘故不希望孩子出生而依医嘱采取了相应的避孕措施或请求医生实施了相应人流手术,但由于加害人的过错,致使避孕失败或流产无效而使胎儿出生,或由于医生过失未发现胎儿的异常而致生而残障等原因,而引发“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之诉。这类情形似乎与上文内容有所雷同,即胎儿是活着出生的。但实际上具有其独特的一面:胎儿或生而健康,或生而所具有的缺陷本身并非被告的过失导致,只不过这类出生违背了父母的真实意愿,从而被认为是“不当”的。另一类为父母是侵权主体的情形。基于该部分内容上的特殊性以及篇幅方面原因,笔者将其单列为一部分进行论述。
(一)“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
1、美国法态度
在美国实务中,孩子主张的索赔案通常被概括为“不当生命”之诉,即一个因被告过失生而具遗传缺陷的孩子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由孩子父母提起的该主张通常被冠以“不当出生”的称呼,这是由于被告的过失而致父母生出了一个具遗传病或其他先天缺陷的孩子而为该父母所提起的诉讼。而在类似上述Burke v.Rivo案中的诉讼主张通常被归于“不当怀孕”或“不当妊娠”,该主张基于因为绝育手术的疏忽操作或其他过失而致一个正常、健康孩子得以出生,如果没有以上过失,这个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就不会出生。
当然,也有少数法庭反对以上称谓。如审理Viccaro v. Milunsky案的法庭认为,这些称谓并不具指导性。任何“非法性”不在于生命、出生、妊娠或怀孕本身,而在于医生的过失。如果有损害的话,也并非出生本身,而是由于医生的过失使父母得以决定是否生育一个孩子或是否生育一个有遗传病或其他缺陷孩子的权利受到否定,从而给其带来身体、感情以及财政状况上的不利影响。法庭主张应避免使用诸如“不当生命”、“不当出生”或“不当怀孕”之类的称谓。
关于该类诉讼的争论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应否承认该类诉因?何种赔偿请求能受到支持?是否支持胎儿的抚养费请求?
(1)应否承认该类诉因?
美国超过40个之多的州允许就对造成一个孩子出生前侵害的侵权事实提起诉讼。加利福尼亚州甚至立法允许对未出生者进行补救:胎儿于出生前,“就其出生利益而言被视为现已存在之人。”但威斯康星州、爱达荷州、新汉普郡以及亚利桑那州等拒绝以医生在孩子出生前未能诊断其患有麻疹为理由代表孩子利益提起诉讼。特拉华州、纽约、西维吉尼亚州以及伊利诺斯州等也否决了基于不同的遗传缺陷而提出的诉讼主张。其他有几个州支持由某个生而残障的孩子提起的诉讼。
A、关于“不当出生”之诉
承认一个“不当出生”的诉因是相对近期的成就。曾一度阻碍着这一观点的公共政策在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审理的具里程碑意义的Gleitmanv.Cosgrove案中引起争议。这一案件中法庭否决了被告责任的承担。理由之一基于损害计算上的困难。为了决定对该案父母的损害赔偿数额,一个法官不得不估算基于成为父母而生的无形、不可计算、复杂的利益并将其与诉请的感情及金钱上的伤害相权衡。理由之二为:即使堕胎被实施而未触及刑事制裁,在政策上仍禁止就拒绝获得怀孕机会所进行的侵权损害赔偿。
但新泽西州法庭在Cleitman案判决12年后,声明仅仅因为损失难以精确计算便拒绝对父母伤害的赔偿是对司法基本原则的曲解。其他法院同样发觉对不同损害计算上的困难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度被认为在否决“不当出生”诉讼案中具说服力的争议逐渐失去了潜力。此外存在两种持相同论点的政策上的考虑:第一种考虑建立于发展医疗科技能力,以在怀孕或出生前预测出生缺陷,认为强加责任于医生表明了以减少基因缺陷为目的的社会利益。第二种考虑源于一般的侵权原则。一个因过失而剥夺了某位妇女决定是否流产的选择权的医生,应当就其前后引起的损害进行赔偿。社会具有既定的利益以减少与禁止出生缺陷,以及要求过错人就因每个违背适当的照顾责任而自然导致的具充分赔偿依据的后果进行赔偿,这种视不当出生为一项求偿主张的做法得到了法庭的一致认可,并最终被所有考虑这一问题的十三个管辖区认可。
如在俄克拉荷马州发生的Dupl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案中,法庭发现Tinker空军基地的OB/GYN诊所的医生与护士在对Duplan太太的出生前照护工作中有玩忽职守的表现。该玩忽职守行为发生于1992年6月对CMV(一种疾病)进行的实验测试中。尽管CMV的感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无害处,但Duplan太太知道一旦被一个孕妇所感染,将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Duplan太太工作于一个儿童日托中心,她知道自己出于感染CMV的特殊危险中,因此要求诊所对其进行CMV感染检查。 经过多次请求后,Duplan太太最终接受了CMV测试。测试结果表明:Duplan太太在其怀孕的前三个月初步感染了CMV。尽管实际测试已表明了可能的结果,诊所的护士却告诉她对CMV具有免疫能力。不合标准的照护继续进行。医生没有同Duplan夫妇谈论CMV的感染问题,也没有跟踪检查病毒是否正在破坏他们的未出生胎儿。Duplan夫妇证实: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存在一种能导致高度出生缺陷危险的活性感染的话,他们会采取堕胎措施。法庭特别指出:针对美国政府提起的这一诉讼并非建立在医生有义务同Duplan太太探讨堕胎问题的观念之上。相反,法庭将其判决建立于它所发现的以下事实基础上:医生有法定义务为Duplan太太提供关于其胎儿危险性的充分信息,以使其能够对是否考虑堕胎作出明智的判断,但医生违背了这一义务。至于护士,“国家的一般照护标准规定护士不得向病人解释检查结果。”但是,当一个护士进行了解释时,该规定要求其给出的是准确信息。法庭发现本案中该护士违反了照护标准要求的义务,由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B、关于“不当生命”之诉
与“不当出生”相反,除了几个例外的审判例,法庭普遍拒绝承认“不当生命”为侵权诉因,即使是在那些生而有缺陷孩子提起的最令人同情的诉讼中。这一司法上的谨慎态度部分上源于,从理论上讲它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否定的事实。“不当生命”之诉中的原告主张并非是他们不应当被有缺陷地出生,而是他们压根就不应当出生。这一主张的本质是:孩子的生命是“不当的”。审理前述Blake v. Cruz一案的法庭也拒绝接受承认如此一个诉因,认为 Dessie Blake 并未遭受任何基于出生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上可认知的“不法性”。即使认为在爱达荷州“不当生命”是一种司法上可认知的侵害,损害赔偿额的不可计算性在任何情形下将排斥对该诉因的认可。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的Wilkins法官提出了孩子能否就其被出生的状况提起诉讼的问题,认为对其回答应是否定的。因为正如其父母主张的:如果没有被告的疏忽,孩子不会被生养。那么,如果他被允许向被告提起过失侵权之诉,将会出现逻辑上的根本矛盾。这个国家最普遍的规则是:医生不应对因其过失而生的孩子承担责任。在Payto v. Abbott Labs一案中,法庭面临一个具某些相似性却又不同的问题。在该案中,法庭阻止一个认为如果其母亲不使用被告提供的药品就不会生下自己的妇女就其经受的因其母亲服药而引起其身体与精神上的损害赔偿要求。法庭认为:“使原告存在的可信方法的提供者,不应对该方法不可避免的伴生后果承担责任。”
在盐湖城提起的一个案件在犹他州最高法院得以立案。Terry Borman 与Marie Wood声称:医生对显示其1岁女儿生而患有某种综合症的检测结果轻描淡写,未向他们说明其严重性。这对夫妇的律师Thomas Schaffer认为:他的委托人从未提到过会实施堕胎,“我们所说的问题是他们应享有作出某个指导性决定的权利。”尽管诉讼为了孩子与父母的利益主张赔偿,但律师认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犹他州法庭是否将承认孩子的诉讼主张。他说:“我不认为孩子的讼案同父母提起的讼案一样有力。父母可以说:看,我们不得不抚养这个孩子。”在此之外的几个案件中法庭否决了基于孩子利益所提出的权利主张。在另一例由孩子提起的“不当生命”诉讼中,医生的律师认为:医生们不应向原告赔偿,因为并不是他们引起她出生上的缺陷,也不应就她生存的事实负责。“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在讲的是孩子应当死亡。什么可以消除对孩子的损害?死亡,结束生命”,律师辩称:“我想象不出10年后孩子会站在这里说——我宁愿会死亡。”类似案件的医生代理人Ann Ruley Combs律师向法官陈述,认为他们不应当承认一个“不当生命”之诉,医生的任何可能的过失并不能给予孩子要求赔偿的权利。“如果这个孩子关于生命有权提出主张,意味着我们在创造一种每个孩子都有期望得以完美出生的权利。”俄亥俄生命权利协会也极力促使法庭否决该主张。 立法顾问Mark Lally认为:“你们所说的情况是唯一避免伤害的方法是使孩子流产。这等于贬低性地说,她的生命不值得存活。这不应当是我们的法律所趋。”
某些学者的态度有所不同。如在俄亥俄州的案件中,Alicia一经受孕便患有天生瘫痪,Patricia 与 Lawrence Heste希望该州高级法庭允许其6岁的女儿就其出生控告她的医生。法庭否决了该诉请。但一位名为Betsy Malloy的辛辛那提大学的法学教授是健康照护与残障民事诉讼方面的专家,她对此评论:“这显然是具开拓性的法例”, “我想这种类型的案例会越来越常见”。并且她预言:随着出生前遗传检测的普遍性以及不同形式的检查被应用,州法院将会见到更多的相类诉讼。这些诉讼为了父母的利益而得以提起,他们或者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检测结果,或者从来不知道需要实施一种特殊的检测。
C、关于“不当妊娠”之诉
在“不当妊娠”的情形,一个生而正常与健康的孩童能否视为对父母的某种损害?许多法庭遵守的准则是,从法律上讲,不能将任何一个健康孩童视为对其父母的伤害,原因正如某一法庭所阐明:作为一种共享的情感,这种无形却极为重要、不可计算而无价的父母身份“利益”,远远超过任何金钱上的负担。但有些判例认为一个“额外”的孩童对其家庭构成了侵害。例如某法庭进行了如下阐述:从公共政策角度讲,避孕失败不会产生任何损害,但从法律上讲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成千上万的人天天采取避孕措施来避免发生“被告认为是一种利益而绝不是损害”的结果;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们,以其行为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感受。
(2)何种赔偿请求可以获得支持?
在Viccaro v. Milunsky案,Viccaro 夫妇于结婚之前咨询了被告医生(一个遗传学专家)关于Amy成为某种先天性功能紊乱疾病的患者或携带者的可能性。Amy家族的几个成员被声称患有此病。这是一种具严重损坏性的疾病,它能影响到人的皮肤、头发、指甲、神经细胞、汗腺、眼睛与耳朵的部分以及其他人体器官。被告得出结论:Amy未患此病,并且也无进一步发展此紊乱病症或影响后代的可能。依照该医嘱,Amy结婚并怀了孕,于1980年生下了一个无该病症状的女儿。但之后于1984年出生的Adam却严重患有此病,将终其一生进行治疗并承受身体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Viccaro夫妇向被告提出了损害赔偿的主张。
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诉讼成立,哪些是可救济的损害?该问题提出了6项专门与可能要求:1、与抚养孩子有关的经济负担;2、满足孩子医疗与教育特别需求的相关费用(在成年前);3、父母因孩子需要而提供的特别照护而生的费用,包括可得收入;4、父母因生育与抚养孩子而生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害补偿;5、孩子从事社会交往而生的花费;6、孩子接受社会服务而生的花费。
该庭的Wilkins法官主张应由Adam的父母而非Adam本人作为原告。他认为:在理论基础上,很难推论被告医生违反了对Adam负有的任何义务。但有一点可以被提出:Adam的确作为被告疏忽的后果而存在,并且他出于医疗照护、教育及其他需要而引起实在与专门的花费。正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使得有些审判法庭支持象Adam一样的孩子可以就其一生中由于遗传缺陷所产生的那些特殊费用主张补偿。但是,只要Adam的父母被赋予就由Adam的遗传缺陷而生的特别费用向被告索赔的权利,Adam没必要再就那些费用提起自己的诉讼。同时,如果孩子生而患有遗传性功能紊乱,几乎所有法庭都会支持父母就与该病相关而发生的专门医疗费、教育或其它费用向过失医生提起的索赔要求,唯一相反的权威例证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与密苏里州。法庭赞成通常的规则:即Viccaro夫妇有权就与照顾Adam有关的专门医疗费、教育费用以及其他特殊损失要求赔偿。如果该夫妇能够证明在Adam成年后仍继续担负其扶持责任,他们将有权就发生于Adam成年后的特别费用主张赔偿。
在马萨诸塞州,父母有义务扶助一个因身体或精神损害而不能自理的成年子女。Viccaro夫妇因被告疏忽而遭受的精神痛苦以及任何由此产生的身体上的损害也都是可救济的。但Viccaro夫妇主张赔偿Adam作为一个正常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损失缺乏根据。被告不对Adam遭受真实存在的遗传病的痛苦的事实本身负责。尽管被告可能对某些损害承担责任,因为依原告观点,如果没有被告的过失,Viccaro夫妇不会生下孩子;但被告不能为Viccaro夫妇丧失了有一个正常孩子为伴的损失承担责任。法庭找不到任何根据以支持Viccaro夫妇对Adam作为正常孩子参予社会活动所带来的花费的赔偿请求。但是有几个法庭允许生而具缺陷的孩子向有过失的医生主张赔偿遗传缺陷给其一生所带来的特别费用,如Turpin v.Sortini案(具遗传性耳聋的孩子可以主张抚养费特别损失);Procanik v.Cillo案(生而患有麻疹综合症的孩子可就专门的医疗费而非一般的损赔主张赔偿);Harbeson v.Parke-Pavis案(孩子可以就其一生中因天生缺陷而引起的特别费用主张赔偿)。
有法庭认为:尽管此类判例中损失的计算可能比较困难,将其与类似非法致人死亡伤害与遭受的痛苦或对配偶权的扩大损失等的固定赔偿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另一种与孩子出生是否构成对父母的侵害问题不相关的争论是:孩子发现自己的出生只是归于一个医生的过失而非父母的期盼;一旦他们的父母宣称他们不值得抚养,孩子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通常来说,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为父母带来的好处是如此之大,远非抚养他带来的身体上、感情上与经济上的负担可比较。然而,当一对夫妇已经作出了不生孩子的选择,或不生更多孩子,那么对他们来讲,孩子的出生至少不是一个纯收益。这是他们的选择,法庭有必要尊重该决定。
(3)是否支持胎儿的抚养费请求?
A、美国实务中对于胎儿的抚养费请求的态度主要有三种:
一为支持意见。
最有利原告的案例可能是Marciniak v.Lundborg一案,该案中的某夫妇已有两个孩子并不再想要更多的孩子,但由于被告的过失而生下了不想要的孩子。起初,如同B案一样,法庭拒绝了一系列针对承担孩子抚养费责任的否定性论点。法庭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使被告就侵权行为而生的可预见的那些损害承担责任。法庭拒绝就给孩子带来的心理伤害的争论,声称:诉讼本身是孩子抚养费损失问题,而非使他们摆脱一个并不想要的孩子。很显然他们想保留这个孩子,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一个孩子所需要的宠爱、关心以及感情上的支持,但这一切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供养、负责衣食、教育及其他抚养孩子所需的经济手段。这正是诉讼所关心的,并且相信这个孩子在长大后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减轻家庭对孩子抚养费的经济损失能够很好地增进包括孩子在内的整个家庭方面的幸福,而不会给其带来损害。诉讼也不会引发降低人类生命的圣洁性的后果。法庭没有察觉提起本案的Marciniak夫妇有任何贬低其孩子生命价值的表现,相反,他们在力图使之提高与增进。法庭反驳了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原告并未采取通过保留孩子或堕胎的方式而减轻他们的损害。“我们并不认为期望父母在孩子与诉因之间作出本质选择是合理之举……堕胎与否纯属私人问题,其中深层次地包含了道德与宗教方面的信念”。但是,尽管法庭结论认为被告应对可预见性损害承担责任,但它拒绝将该责任扩至孩子成年以后。既然本案并未包括孩子成长受到严重阻碍的情形或存在其他需要救助至成年以后的理由,那么则没有道理突破这里的界限。
另在Burke v. Rivo案,已有三个孩子的波克家经历着经济上的困难,妻子希望重新工作以补给家庭并完成其工作目标。她约见被告与之讨论不想再多要孩子的愿望。被告介绍了一种称为Bipolar canterization的绝育手术,并保证能使她将来不会受孕。两年后,该妻子生下了第四个健康的孩子。于是她又不得不接受了另一种绝育手术。波克夫妇声称:“如果被告早告诉其妻子有避孕失败的风险,无论风险有多大,她会在一开始便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绝育手术。” 大多数法官倾向于承认作为医生过失结果而生的孩子的父母就与该出生直接相关的损害(有时包括对父母感情痛苦的赔偿)进行赔偿补救,但法庭在父母能否就孩子的抚养费要求赔偿这一问题上见解存在分歧。主要问题是:原告是否有权要求孩子的抚养费赔偿? 依据通常的侵权法与合同法原则,那种损失是原告主张的非法行为产生的一种既是可合理预见、又是自然与有充分根据的后果。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公共政策上的考虑而限制传统侵权与合同损害的适用。法庭推定:并不存在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决定不孕的父母相关的任何此类考虑。同时,一些作为拒绝支持由医生过失而生的健康儿的抚养费的补救的所谓“正当理由”显然不具说服力。这样一种司法主张是缺乏贴切性的:即认为抚养一个孩子带来的快乐与自豪感可以超越该父母遭受的任何经济上的损失,因而就排除了对孩子抚养费的救济。一个人寻求医疗方的介入以阻止其生孩子的事实表明,对那个人来说,父母身份带来的利益并不比生一个孩子带来的负担、经济因素及其他更重要。避孕与不育措施的广泛运用以及每年无数次堕胎手术的实施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人并不愿将成为父母视为一种单纯的积极情形。
法庭赞同孩子出生在任何时候对父母而言都是一种净收益的否定性司法意见,同时坚决拒绝这样的建议——即堕胎或其采用带来的有益性能够构成要求医生就因其过失而使孩子受孕进行赔偿的数额的基础。法庭同样对这样一种理由不置可否:即认为不允许孩子抚养费的救济是因为,如果有一天孩子发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并且是别人支付费用抚养了自己,将会对其产生不利影响。表达了对孩子这一影响之关心的法庭,却在孩子得知自己不被需要时所受伤害未表达任何关心的情况下,允许父母就来自过失医生的某些直接费用请求救济;而一旦孩子得知是他人而非父母被强迫支付了抚养费,这一事实可能会减轻孩子因得知自己曾不被需要的精神痛苦。在任何情况下,应当是父母而非法庭有权利来断定一个诉讼是否对孩子造成了不利影响以及应否得以维持。法庭同时反驳了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孩子抚养费太具投机性,与医生的过失过分不相称。法庭认为该主张是不正当的,因为预期的孩子抚养费的确定并不比许多在侵权案中天天作出的未来损失的计算更加复杂与不切实际。如果一个医生由于在照护新生儿时有过失,损害赔偿的计算会根据新生儿一生中的收入能力及预见到的医疗费来确定。孩子的抚养费远比以上情形更容易确定。假如在此类案件中存在否认正常侵权损害救济的正当性的话,那也不应当是孩子抚养费不能合理计算或该费用给医生施加了过重负担。
还有人认为法庭不应当允许“不当出生”案中的被告施加于原告一个不需要的利益;同时,原告的救济不因由被告侵权而生的任何利益而减少。例如,一位评论者撰文:当然,一个孩子的出生可能会给其父母带来某种无形的情感上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并非父母所要求与有能力支付的。
二为反对意见。
Burke v.Rivo一案中,O,Connor法官不赞成赔偿依据侵权或合同理论进行估价,并作为对抚养费的补偿,或者向一个绝育手术完成后或给出建议与保证后仍出生的孩子承担责任;也不认为损害赔偿能够反映孩子出生对其父母、家庭经济状况或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这并非普通的医疗误诊案,其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对人类新生命的缔造,并且在构想一个适当的损赔规则时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侵权法源于社会价值并应当促进适当公共政策的运用。正如多数不赞成抚养费救济的法院那样,O’Connor法官认为不将孩子对父母的价值区分开来的赔偿判决对被告不公平,也是不可忍受的。
在其看来,一个致力于寻求一个孩子对其父母价值多少的审判同样无法忍受。这种审判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是因为它要求决定一个孩子对其父母而言是否意味着一种损失。如果这个孩子并未出生,其父母是否更富有?这个孩子的价值是否小于抚养其所需花费的费用?如果价值小的话,到底小多少?即使这种审查会产生一种合理且并不具投机性的结论,一种令人疑惑的建议是:损失与利益的平衡本身实际将孩子当作了私人财产。这一审查违背了国民必须与每一个人类生命相一致的尊严性。强调对孩子亲权损失或其死亡的损赔额进行估价的假设成立基础是:孩子生命是有价值的,其损伤或死亡或归结为对父母的损失。这种假设与国家公共政策中应当体现的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不一致。价值大小的比较决定了被告的损赔额。的确,正当的公共政策需要作出一种确认:对他人而言构成损失的是孩子的伤害与死亡,而非其生命本身。拒绝法庭信奉的规则并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上的理由。但是,进一步考虑(哪怕是简要地)新采用的规则对这一国家的孩子与家庭产生的潜在的不利影响是妥当的。“致力于加强与鼓励家庭生活以保护与照护儿童是这一国家的政策”。该种政策确实不能服务于(事实上它也未服务于)这样一种损害赔偿规则:即要求父母(即使其将胜诉)说服法官或陪审团相信其孩子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如孩子抚养费损失更大。加强与鼓励家庭生活以利于孩子保护与照护的利益是合法与有力的。的确,应由国家来决定是否采纳一项损害赔偿规则,这一规则会鼓励有害于家庭的诉讼——该类诉讼将产生这样的结果,孩子最终会发现自己不被父母所扶养(因为他们不想要他),而实际上是被一个不情愿的陌生人扶养长大。
三为折衷意见,即认为应具体分析原告寻求避孕的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决定应否支持赔偿。
例如在Hartke v. Mckelway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认为: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裁决否定了原告要求赔偿抚养费的请求,因为证据表明原告寻求避孕并非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同时法庭推断她对所生的孩子事实上持赞赏态度。
“不当出生”案中存在赔偿数额计算方面的特别困难,因为孩子的出生对特定父母的侵害程度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随着具体情形与期望而变化。父母可能在事实上获得了一个他们极为喜爱的孩子,并私下认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利益。因为父母避孕原则是多种的,也许因为社会经济上的原因,为了避免其工作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或者为了节省家庭资源;也许由于优生因素,避免一个残疾儿的出生;也许因为治疗因素,避免对孕妇及出生儿带来危险。当一对夫妇决定不育的原因仅仅是治疗或优生方面时,一个健康儿的出生,即使是非计划的,对其父母而言最可能是一种巨大利益。在此类案例中,法庭倾向于认为将孩子的巨额抚养费强加于被告医生是不公正的,并且担心基于冲动或对医生的偏见产生如此一个判决。
这样,在考虑孩子的抚养费应否被支持这一问题时,多数法院与评论者将重点置于不孕原因的分析上。例如,在最早的“不当出生”案中法庭明确指出:“手术的目的是挽救妻子的生命,与之相伴的是孩子的意外出生。补救怀孕与生育手术的费用不符合声称的目的。妻子脱险了。原告未失去妻子,相反被祝福成为另一个孩子的父亲。诉请的费用对孩子出生来说是意外,它们远非基于手术本身的目的而生”。其他一些判例同此结果。法庭倾向于赞成实情调查者将重点置于夫妇避孕的原因之上,以此来决定孩子的出生(从衡平法的角度)是否对其父母构成了侵害。例如,在夫妇避孕主要是治疗或优生方面的原因的情形下,可以推测,意外出生的健康儿对其父母构成侵害的程度只是该父母所体验的可能有害于母亲或可能出生一个残疾儿的异常的惊吓。法庭与陪审团可以假定父母珍视该孩子,通常的抚养费用将被孩子出生带来的特定利益所超越。所以很清楚,一旦发生在母亲身上的生育孩子的特殊危险消除,从公平意义上讲,对她而言有一个孩子会是一种积极的经历。在这些情况下,支持孩子抚养费只会给孩子的家庭带来意外收获。
B、损害能否为胎儿带来的父母身份利益所充抵?
对于这一问题同样存在赞成与反对的对立态度。
允许对孩子的抚养费损失进行补偿的法庭,通常要求抚养费损害可以被胎儿带来的父母身份利益所抵销。也许正如一位法官所言,允许以抚养利益抵销损害赔偿“只不过是将抵销用于减弱对医疗侵权人与其保险人金钱上的震动。”如果这样,仍然存在的事实是削弱判决力的愿望被普遍共享,并反馈出深层的价值。这一愿望也许基于这样一种感觉:即使是在避孕与家庭计划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今天,夫妻也通常要面临预想不到的怀孕。
有些管辖法院支持赔偿一个正常孩子的抚养费直至其成年;但这一费用可被父母自一个正常、健康孩子得来的利益相抵销。如此一个经事实审查得来的均衡要求将孩子抚养经济损失与自一个正常、健康孩子而来的感情所得(转换为货币价值)相比较。这些法院认为:此种比较与侵权法表达的一般原则相符合。为数不多的几个法院则认为:因为赋予父母的利益并不影响侵害的经济利益,因而不应当确认减少孩子的抚养费损失。如果父母不孕的目的是基于优生(如避免一种可怕遗传缺陷)或治疗上的原因(为母亲健康考虑),并且出生的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司法上支持正常孩子自出生至成年的抚养费的数额会远低于基于经济上的原因寻求不孕而失败的情况。法庭由此得出结论:除了前述的可救济的损害赔偿,如果父母不孕是基于经济或财政上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得以就一个正常健康但不需要(至少开始)的孩子的抚养费损失要求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审查者应当就父母可能自孩子身上得到或将得到的利益与孩子抚养费损失相抵偿。
然而,在前述Marciniak v.Lundborg一案谈到抵销问题时,Wisconsin法官引用920条评论:“痛苦与心理遭遇方面的损害并不会通过显示原告的收入能力由于被告的行为增强而减轻。”这样以来,经济利益仅能与经济性损害相对应,发生感情利益仅能与感情伤害相对应。在这里,被告试图将感情利益与经济损害分割开来。父母所作的不要孩子的决定中包含了放弃可能来自另一个孩子的感情利益的决定。当父母作出决定放弃这一丰富感情的机会时,强加该利益于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必须以抵销其已经证明的经济损害赔偿的方式付出什么的作法,显然是不公平的。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相同争论很普遍。此外,孩子可能赋予父母的任何经济利益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同样,Viccaro v. Milunsky案中的O`connor法官对孩子的抚养费请求以及相关的抵销问题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对一个法官或陪审团来讲,致力于相关抵销问题的审查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并得出结论:即使抚养一个正常孩子的经济负担在某些情况下是实际存在的,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它不应得到补偿。法官或陪审团衡量一个正常孩子的出生带给其父母多少净收益的假设与人们应对人类生命怀有的尊重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于这种审查对社会的危害性表现为,对家庭与孩子的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父母因其主张的违法事实而获赔偿的价值。尽管抚养一个不正常孩子的负担要比抚养一个正常孩子的负担重得多,但支配的价值与原则是相同的。
2、欧洲法态度
欧洲侵权法不承认美国普通法中出现的上述“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称谓。两条基本规则概括了欧洲的共同观点。其一,任何人都无权决定自己之不生存,这已被普遍接受。所以一个人被孕育或者堕胎这一事实不能对那个人构成一个诉因。同样,如果明知存在孕育或遗传方面的缺陷,但忽视这种影响而导致出生的孩子严重残障,也不构成一个诉因。 例如英国的“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认为:“被告不对孩子就以其专业能力负责向孩子的父母亲提供治疗或咨询意见中的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个原则是,尚未出生者享有人格尊严权(如法国宪法保障“从生命之初就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因此,责任与损失产生于出生之前或者出生之后无关。从而认为,因为未出生者没有法律上的能力所以在取得法律上的能力之后也不能对出生前受到的损害提出诉讼的观点,在宪法上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将一个残障的孩子在法律上与缺陷产品同等对待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在堕胎失败给胎儿造成伤害并在后来影响其终生的案件中,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法国行政法院1989年9月27日所作出的判决:即使失败的堕胎没有对胎儿造成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妇女违背丈夫的意愿做流产手术,尽管堕胎不构成刑事犯罪,父亲也有权请求对物质损害/非物质损害的赔偿,因为这在技术上是不法的。
但欧洲法并未明确规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不想受孕或者知道胎儿有“缺陷”而要将其堕胎的父母有权请求赔偿。对于因健康原因而不想要的孩子,欧洲国家认为是被冠上了一个不幸的美国称呼“错误生命”。这些案件通常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在父母亲一方声称做过绝育手术后或在父母亲接受了不适当的避孕措施后怀孕,或者是在堕胎失败后出生。无论是对被告的行为进行合同上的考量还是进行侵权行为的考量都无关紧要,应当一般接受的做法是,既不能将孩子的抚养费用也不能将与其出生有关的物质上的或非物质上的不利作为可以得到救济的损害。不到一半的欧洲国家的法律采取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倡导者有丹麦的法院。荷兰的一些法院,如阿纳姆地方法院1974年11月28日的判决和1976年2 月26日的判决:在父亲输精管结扎后孩子出生,法院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该男子受到了损失,但是赔偿抚养费不符合荷兰法律制度的规定;又如赫特根布奇上诉法院1983年5月17日的判决:失败的绝育手术,不对痛苦和疼痛予以赔偿,仅对收入损失以及与怀孕有关的费用予以赔偿。法国行政法院,如1982年7月2日的判决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并不产生导致其母亲当然得到救济的损害.....除非存在特殊情况。意大利最高法院。意大利最高法院声明,“由于堕胎失败致父母亲之经济损失不能得到赔偿”。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法院赞成对抚养费用进行有限赔偿。
有关判决认为:将一个婴儿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构成侵权,因此无论是父母还是秘密解除双方约定避孕措施的妇女都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在上述情况下,各国一致认为任何人都没有主张不被生下来的权利。区别仅在于处理结果上,对于出生前就已经严重残疾的案件,德国法院仅赋予了父母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法国法院则同时赋予了父母和婴儿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依欧洲侵权法的精神,没有抚养,人的生命无法延续,所以不可能对延续生命作出肯定的判决而对支付抚养费用作出否定的判决。如果解除对孩子的照顾与抚养既是自然权利又是其父母的基本义务这一原则,将导致大量的问题。此等解除不仅严重违反家庭法,而且可能导致年长的兄姐提出要求其父母亲少生弟妹的主张。另外,对出生健康的孩子的抚养费予以补偿可能会需要许多新的规定;按照父母亲的受益情况调整医生承担的赔偿额也将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孩子给他家庭带来了欢乐而且他也可能是“有用的”。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疑问:尽管父母亲对孩子的抚养通常必须超过这一成年年限,但是民事责任法的哪一方面能够证实将对补偿限制于孩子的未成年期是适当的呢?如果父母亲在成功起诉外科医生之后又有了另一个孩子,他们向外科医生请求前面孩子的抚养费的权利是否应当被撤销呢?人们是否能提出夫妇因没有克制性交或没有更仔细地学习避孕指南或者声称做过绝育的男子对其性伴侣未做早孕检查负有责任而有共同过失呢?如果实际上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父母亲作出了不做堕胎手术的决定或者决定不将孩子交给他人收养,是否就应当切断因果链呢?即使是在这个流行避孕的时代,一个孩子也不是人们可以随便从定单上取消的某种东西。给予母亲补偿以防止其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希望堕胎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判决医生对孩子的出生承担责任可能会鼓励妇女终止妊娠。
(二) 父母为侵权主体
依多数国家的法理,子女出生后,父母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其人身权的,应依侵权行为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如果父母的侵害行为发生在子女出生以前,例如父亲的遗传病染至胎儿使其生而缺陷;夫妻相殴,丈夫踢打妻子腹部致胎儿天生残疾或痴呆;医生开药不当而母亲在此基础上基于过错加大药量而使胎儿受到侵害;身为孕妇的竞技者参加比赛为对手伤害,或孕妇因病住院或生产时与医院签定了免责条款等,父母应否承担责任?父母的过错或允诺能否产生“阻却违法”的后果?当然,“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也包括了“不当出生”中因强奸或无效婚姻所生子女的救济问题。
在此问题上,比较各国的态度:
1、在美国法上
子女因出生前受父母侵害而请求损害赔偿的实例很少。在Zepda v. Zepda一案,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曾明白表示,使人出生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关于子女应否承担父母的过错,侵权法权威教授Prosser在其有名的《侵权行为法》(Law of Torts)一书中作了如下说明:父母的过失由其子女负担,是一项不适当的古老原则,因为子女与其父母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同一性。
在C.A.M v.R.A.W一案中,生下一个健康孩子的原告向被告(孩子父亲)提起了诉讼,声称被告使她确信他做过绝育手术。法庭在审阅了大量涉及该领域的诉讼案后,得出结论:“基于一对自愿发生性关系而出生的正常健康孩子,排除了法庭调查可能在性交之前或性交过程中由任何一方作出的关于控制出生的声称的必要性。”法庭区分了该案与 I.P.M. v.Schmid Laboratories一案,该案中一对夫妇控告某保险套生产商,声称由于被告的保险套的缺陷导致了一对正常双胞胎的出生。法庭允许被告对该父亲在保险套的错误使用上的疏忽提出交叉诉讼。
但在奸生与欺诈婚姻情况下,法院基于公益的考虑,往往不支持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如在William v. State of New York一案中,某妇女因精神衰弱住进纽约市神经医院治疗,因医院监督疏懈,导致她遭到强暴,因而生产一子,名叫William。该子认为医院未尽适当监督义务,使其母遭人侮辱,致其出生,从而不能获得一个正常孩童应有的家庭生活、父母的抚养及照顾,财产权益均被削夺,并蒙受私生子的污名的讥笑及其他不利益,主张纽约州应以医院所有人的地位,对其所受损害负承担赔偿责任。纽约州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认为被告强暴原告之母时,原告尚未出生或受孕的事实对于侵权行为的成立不发生影响。但二审法院废弃了此项判决,Gibson法官在其简短的判决理由中称:“承认此种请求权,使对一个人的出生负责赔偿一项难以确定的损害,自立法政策言,实属不妥,欠缺合理依据。”1966年12月29日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意此项观点,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权,尽管具有新奇性,但该案情形特殊,影响深远,应甚重考虑;再说,就法律构成要件而言,使某人在此种情形出生而不在他种情形出生,很难认为是不法致他人受有损害而构成侵权行为。
又如Zepda v. Zepda一案,被告依“不法使人出生”为理由,向生父请求损害赔偿,产生新的争议。该案被告为波多黎各的黑人,虽已结婚,却自称未娶而向某白女求婚,并与其同居。该女怀孕之后,发现受骗,拒不结婚,所生的孩子认为自己生而为私生子,且为杂种,因此对其父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芝加哥地方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二审判决原告败诉,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也维持原判决。各级法院判决之所以拒绝承认此种“不法使人出生”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有基于事实的考虑,有基于法律上的理由,王泽鉴先生认为可归为四点:首先,在1960年美国的非婚生子女数额庞大,假若确认使人以非婚生子女地位出生构成侵权行为,则容易引发诉讼,势必造成社会问题。其次,这种新的侵权行为一旦被创设,则不满意自己肤色、患有遗传病或羞于父母声名的人也会主张损害赔偿,甚至不免有人会以“未经同意被出生,致在人间受苦”为理由提起诉讼,请求的依据将无限扩大,漫无边际。第三,社会变迁及科学进步,使法院面临新的问题,必须改革旧法,补充或创造新的制度,以期能适应变动多端的时代。然而就本案而言,法院无立即采取措施的必要。其所涉及的法律论点虽然新奇,但问题本身及社会背景,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不必急于创设新的侵权类型,速求解决。第四,从损害赔偿的观点,所谓损害是就减损被害人的权益而言。在本案中,原告于出生前本不存在,被告使其出生,由无变有,纵原告对于自己出生之状况不满意,从法律观点言也难说受有损害。
如果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其母亲被治疗师诱奸的结果,审理法庭的部分分析结论应否被改变?参看Poor v.Moore一案,该案结论为:母亲有权取得就孩子的照护而生的实际、合理的费用以及未来赡养孩子之付出的部分补偿…孩子孕于其母亲被侵害过程中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成文法与普通法上的赡养责任。”法庭对以下观点的明智性提出了置疑,即允许“父母一方就其孩子的不当出生向另方提起诉讼,一方利用孩子作为侵权主张的损害赔偿基础来对抗另一方的作法不会给孩子带来多少好处”。
2、英国法上对其尤为关注。
最值注意的是英国最近法制的发展。英国法制委员会在其“出生前侵害之损害赔偿”的资料文件中,曾初步认为,依英国普通法,父母于其子女出生之前加以侵害的,仍应当负侵权责任,此项原则应当维持不变。对于这一点,各界人士见解不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很大。但多数意见倾向认为子女对其生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律师协会提出如下备忘录:“就逻辑及原则而言,生母怀孕期间或怀孕之前,因其过失之作为或不作为致胎儿受有损害,对其所生之子女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任何法律体系,于若干领域,逻辑及原则应对社会之可接受性及自然感情让步,此项特殊责任,即属此种领域。”英国法制委员会在其正式报告中,建议采取折衷的立场,即生母无须负责,但生父仍不免其责,并于“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第1条第1项设定该规定。之所以认为生母无须负责,目的是为了顾全亲子关系,避免作为父母婚姻上的攻击手段,以及过分限制生母的社会生活;之所以认为生父不免其责任,主要理由为上述顾虑并不存在,再说,生父与胎儿不属同一体,肇致损害机会较少,而且生父并不当然为生母之“夫”,所以原则上应当适用普通法的一般原则,使生父就其所加于子女的损害,负损害赔偿责任。
3、德国法上。
在父亲以梅毒传染其子的案例中,德国S高等法院肯定生父应当负侵权责任,最高法院则以侵害行为时被告尚无权利能力为由加以否定,但都没有提及父母的侵害行为本身是否具有违法性的问题。在医院输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至于父亲或母亲于怀孕之际,因患有一时或先天疾病,而将此疾病传染于受胎的子女,致其健康自出生时起即遭受损害时,是否构成对健康的损害,抑或在此情形根本不发生损害赔偿,如果无父亲或母亲可非难的行为,则该孩童根本不能出生,因本案原告健康的受损害,因可归责于被告医院之行为所致,故本庭无须作成判决。”
由此可知,德国实务上早已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是未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学说方面,学者Selb认为对胎儿健康的侵害,除故意者外,合法与不法的界限,很难断定。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的人格权互相对立,强制孕妇从事维护胎儿的生活方式,对民法而言实在是一种奢望,对母亲生活方式的控制,既违反其利益,实际上也无法实施。因而强调,因德国民法对此问题没有明文规定,父母侵权责任的界限的确难以划定,仅能参酌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填补漏洞。基于这种认识,Selb认为单纯因受胎怀孕,致其子女受损害的(例如遗传病),父母不负责任。至于父母因故意或过失,以外在原因致其子女于出生前遭受损害时,则须负责。
此外,《澳门民法典》第63条第4项规定:“然而,生父母无须就受孕时对子女造成之畸形或传给子女之疾病负责,亦无须就受孕后对胎儿造成之损害负责,但属故意造成之损害者除外”。台湾学者认为:父母明知或可知其有传染病,如性病、肝病等仍怀孕而生下带病子女,该子女不具有请求权,理由有在于其受损害时无权利能力,而在于没有父母,他们根本不会出生,自无法确认其有损害的存在。
笔者认为:对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应参酌多数国家的法理:一般情形下,如子女生而患有遗传性疾病,基于公益上的考虑,不宜支持子女以此为诉因向父母提起诉讼;但在奸生或由欺诈婚姻所生的例外情形,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父母于道德或法律上都具有可受谴责性,因此应对子女向其提起的赔偿请求作适当考虑。但在父母有一般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忽视生母与胎儿形体上的一体性与特殊性,既然实践中父母可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替未成年人,由此而为的允诺会产生阻却违法的效力,对胎儿也应当适用该法理。
六、小 结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胎儿的损害赔偿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问题,用传统上简单、一概而论的研究方法已经显得不甚合适。笔者通过本文,对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个基本建议:即应区分不同侵权形态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探讨。具体而言:
1、对人于出生前受侵害致健康受损的情形,尽管我国立法与理论未多论及,但实务中支持该诉因的法院实际上已经在运用一般侵权法原理解决问题。然而对其处理尚未上升为一般规则。笔者以为:人因出生前的侵害致健康损害时,由于实际受侵害的人是某个因受孕期间受侵害生而健康受损、但现尚生存之人,胎儿损害赔偿问题转而成为符合侵权法理论但主体稍显特殊的类型而已,所以可将因出生前侵害而健康受损的人视为该类损害赔偿案的请求权主体,使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简单化为探讨一般人身权(本文指健康权)受侵害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应遵循侵权法一般原理,只须侵权责任要件齐备即可支持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2、对人于出生前受侵害致死亡的情形,应包含因侵害致出生后不久即告死亡与致出生前死亡(即死产)两种类型。在因第三人过错而致胎儿流产于母体的情形,曾有以此为诉因提起的个别诉案。但在因最常见的医疗操作过失致以上情形发生时,笔者反而未发现我国实务中的相关判例,这从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了立法者与司法界对这一问题的漠视态度,当然与我国的法律意识层次与传统心理也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此类诉讼必将占有一席之地,立法与司法界将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途径。笔者建议:在前种情形下,由于胎儿出生后先是存活,既而死亡,因此,即使时间再短,此时的“胎儿”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的独立的人,可适用非法致人死亡的一般原理处理之。但对于死产的情况,应将其视为母体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还是视其为独立的“人”,以及应如何很好地处理两种类型在处理结果上可能出现的冲突?这些问题还尚须学界结合实践发展作出进一步研究。
3、对“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情形,我国立法与学界均未涉及。但司法上却已有了相关判例,如前述由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脑瘫婴儿案”,原告获赔55万元;以及2000年发生在广州的基于医院检查过失未发现胎儿的缺陷而引起的“女婴出生少右臂,父母向医院索赔”案等。以上诉因可归为本文所述的“不当出生”。但由孩子本身作为原告的“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之诉则未见其例。笔者赞成美国实务中对“不当出生”诉因的一般认可态度,但认为应设立相应的请求权规则,使问题的解决有所依据。同时,笔者反对“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诉因,认为在目前状况下对该问题尚须进一步观察与研究,否则可能会引发与人类生命价值观的冲突。
4、对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笔者主张,我国应参考多数国家的法理:基于公益上的考虑,一般不宜支持子女以生而患有遗传性疾病之类诉因提起的诉讼;但在奸生或由欺诈婚姻所生的例外情形,对子女向过错方提起的赔偿请求,应作适当考虑。应充分考虑父母与胎儿关系的一体性与特殊性。
文章结束之际,笔者的个人感受是:鉴于问题的复杂,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深入;笔者有志于继续探讨。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一个研究的合理切入口,以期引起法律同仁对这一问题关注并给出更好的建议。
注释:
Viccaro v. Milunsky,Supreme Judici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77,551 N.E.2d 8
www.findlaw.com
Gleitmanv.Cosgrove,49N.J.22,227 A.2d 689,1967
Gleitmanv.Cosgrove,49N.J.22,227 A.2d 689,1967
www.findlaw.com
Blake v.Cruz, Surpreme Court of Idaho,1984 108 Idaho 253,698 p.2d 315.
Payto v. Abbott Labs,386 Mass,540,557-560,437 N.E.2d 171,1982
www.nolo.com/lawcenter.
www.nolo.com/lawcenter.
参看Terell v.Carain[Terell .v.Carain,496S.w.2d124,131]案(一个“不需要”之孩子的出生不仅对其父母与其自己,也对其兄弟姐妹会是一种灾难)以及Terell v.Carain,cert.denied,415 u.s. 927,94 S.Ct. 1434,39 L.ed.2d484(1974)案的态度。
Viccaro v. Milunsky, 406 Mass. 777,783 (1990)
Turpin v.Sortini,31 Cal.3d 220,237-239,182Cal.Rptr.337,643 P.2d 954,1982
Procanik v.Cillo,97 N.J.339,352-354,478 A.2d 755,1984
Harbeson v.Parke Pavis,Inc.98 Wash.2d 460,479-480,656 P.2d 483,1983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Kashi,The Case of the Unwanted Blessing:Wrongful Life,31U.Miami L.Rev.1409,1416(1997)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Hartke v. Mckelway,United States Coun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1983,707.
Hartke v. Mckelway,United States Coun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1983,707.
第二重述1979年第920条.
Hartke v.Mckelway一案的争议。707F.2d1544,1557-1558n.16(D.C.Cir.1983)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Viccaro v. Milunsky, 406 Mass. 777,783 (1990).
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被维持。在Aiedale NHS Trust v.Bland [1993] 1 All ER 821 案件中,英国上议院正确地认为,就一个在谢菲尔德的足球场发生的灾难之受害者而言,没有义务延长永远不会苏醒的患者的生命。转引自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7页。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8页。
如西部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对妇女的绝育手术失败的赔偿中,孩子出生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神圣的事件,所以公共秩序禁止对抚养费予以补偿。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9页。
参见奥地利最高法院1994年1月27日所作出的判决,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4月17日判决为基础,并进一步指出,非婚生的父亲即使该非婚生子女的母亲在导致怀孕的每次性行为之前对她的怀孕能力故意作了虚假陈述,也不能向她就该非婚生子女抚养费要求赔偿。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4页。
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第712-713页。
Zepda v. Zepda ,1963,41111,1pp.2d 240,190 N.E. 2d 849
C.A. M v.R.A.W,237N.J.Super.532,568 A,2d 556,1990
I.P. M. v.Schmid Laboratories,Inc,178 N.I.Super.122,428 A.2d 515 1981
William v.State of New York,34 U.S. Law Weeks,1965 260 N.Y.S.2d 953.
Zepda v. Zepda, 1963, 411 II, 1pp. 2d 240, 190 N. E. 2d 849.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Poor v. Moore,791 P.2d 1005,Alaska 1990.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第285-287页。
BG HZ 8, 243.
同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主要参考书目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台)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Henry Campbell Black.M.A,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
Report on Injuries to Unborn Children, The Law Commission No.60,(1974)Cmnd.57090.
郑冲,贾红梅 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Marc.A.Franklin,Frederick I.Richman,Robert L.Rabin A.Calder,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Fifth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
Prosser,Law of Torts,Third Edition,1964.
Working paper No. 47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马克昌,比较民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杨立新,吴兆祥,杨帆.人身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Harry Shulman,Fleming James,Jr. Oscar S.Gray, Torts,Third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76.
Robert S.Thompson,John A.Sebert,Jr.Remedies amages,Equity and Restitution,Second Edition,Matthew Bender Co. amages,Equity and Restitution,Second Edition,Matthew Bender Co.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张新宝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王利明,人格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
杨立新,人身权法总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Charles T.Mccorsneck, William F.Fritz, Damages, Second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52.
William L.Prosser, Hastings,Johm W.Wade, Victor E.Schwartz, Torts,Eighth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Press, Inc.1988.
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orts,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1979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黄立,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Edward D.RE, Stanton D.Kraus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Remedies, Third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
Clarence Morris, C.Robert Morris, Torts, Second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
(美)彼得.哈伊著,沈宗灵译,美国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李亚虹,美国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网 络 资 源
http: //www.findlaw.com/casecode
http: //www.excite.com
http: //www.nolo.com/lawcenter
http: //www.civillaw.com.cn
http: //www.rmfyb.com
http: //www.chinalawinfo.com
http: //www.canada.justice.gc.ca
http: //www.yahoo
http: //www.chinalaw.com
http: //www.gztz.org
http: //www.Lexis.com
http: //www.cinews.net
http: //www.sohu.com
http: //www.sina.com
http: //www.online.jn.sd.cn
http: //www.echolaw.com
出处:载于刘士国主编:《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240331
原作者:冯恺
五、对两类特别胎儿损害赔偿问题的评述
从胎儿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看,存在两类特别的情形:一类为夫妻由于身体、经济或工作等方面缘故不希望孩子出生而依医嘱采取了相应的避孕措施或请求医生实施了相应人流手术,但由于加害人的过错,致使避孕失败或流产无效而使胎儿出生,或由于医生过失未发现胎儿的异常而致生而残障等原因,而引发“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之诉。这类情形似乎与上文内容有所雷同,即胎儿是活着出生的。但实际上具有其独特的一面:胎儿或生而健康,或生而所具有的缺陷本身并非被告的过失导致,只不过这类出生违背了父母的真实意愿,从而被认为是“不当”的。另一类为父母是侵权主体的情形。基于该部分内容上的特殊性以及篇幅方面原因,笔者将其单列为一部分进行论述。
(一)“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
1、美国法态度
在美国实务中,孩子主张的索赔案通常被概括为“不当生命”之诉,即一个因被告过失生而具遗传缺陷的孩子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由孩子父母提起的该主张通常被冠以“不当出生”的称呼,这是由于被告的过失而致父母生出了一个具遗传病或其他先天缺陷的孩子而为该父母所提起的诉讼。而在类似上述Burke v.Rivo案中的诉讼主张通常被归于“不当怀孕”或“不当妊娠”,该主张基于因为绝育手术的疏忽操作或其他过失而致一个正常、健康孩子得以出生,如果没有以上过失,这个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就不会出生。
当然,也有少数法庭反对以上称谓。如审理Viccaro v. Milunsky案的法庭认为,这些称谓并不具指导性。任何“非法性”不在于生命、出生、妊娠或怀孕本身,而在于医生的过失。如果有损害的话,也并非出生本身,而是由于医生的过失使父母得以决定是否生育一个孩子或是否生育一个有遗传病或其他缺陷孩子的权利受到否定,从而给其带来身体、感情以及财政状况上的不利影响。法庭主张应避免使用诸如“不当生命”、“不当出生”或“不当怀孕”之类的称谓。
关于该类诉讼的争论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应否承认该类诉因?何种赔偿请求能受到支持?是否支持胎儿的抚养费请求?
(1)应否承认该类诉因?
美国超过40个之多的州允许就对造成一个孩子出生前侵害的侵权事实提起诉讼。加利福尼亚州甚至立法允许对未出生者进行补救:胎儿于出生前,“就其出生利益而言被视为现已存在之人。”但威斯康星州、爱达荷州、新汉普郡以及亚利桑那州等拒绝以医生在孩子出生前未能诊断其患有麻疹为理由代表孩子利益提起诉讼。特拉华州、纽约、西维吉尼亚州以及伊利诺斯州等也否决了基于不同的遗传缺陷而提出的诉讼主张。其他有几个州支持由某个生而残障的孩子提起的诉讼。
A、关于“不当出生”之诉
承认一个“不当出生”的诉因是相对近期的成就。曾一度阻碍着这一观点的公共政策在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审理的具里程碑意义的Gleitmanv.Cosgrove案中引起争议。这一案件中法庭否决了被告责任的承担。理由之一基于损害计算上的困难。为了决定对该案父母的损害赔偿数额,一个法官不得不估算基于成为父母而生的无形、不可计算、复杂的利益并将其与诉请的感情及金钱上的伤害相权衡。理由之二为:即使堕胎被实施而未触及刑事制裁,在政策上仍禁止就拒绝获得怀孕机会所进行的侵权损害赔偿。
但新泽西州法庭在Cleitman案判决12年后,声明仅仅因为损失难以精确计算便拒绝对父母伤害的赔偿是对司法基本原则的曲解。其他法院同样发觉对不同损害计算上的困难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度被认为在否决“不当出生”诉讼案中具说服力的争议逐渐失去了潜力。此外存在两种持相同论点的政策上的考虑:第一种考虑建立于发展医疗科技能力,以在怀孕或出生前预测出生缺陷,认为强加责任于医生表明了以减少基因缺陷为目的的社会利益。第二种考虑源于一般的侵权原则。一个因过失而剥夺了某位妇女决定是否流产的选择权的医生,应当就其前后引起的损害进行赔偿。社会具有既定的利益以减少与禁止出生缺陷,以及要求过错人就因每个违背适当的照顾责任而自然导致的具充分赔偿依据的后果进行赔偿,这种视不当出生为一项求偿主张的做法得到了法庭的一致认可,并最终被所有考虑这一问题的十三个管辖区认可。
如在俄克拉荷马州发生的Dupl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案中,法庭发现Tinker空军基地的OB/GYN诊所的医生与护士在对Duplan太太的出生前照护工作中有玩忽职守的表现。该玩忽职守行为发生于1992年6月对CMV(一种疾病)进行的实验测试中。尽管CMV的感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无害处,但Duplan太太知道一旦被一个孕妇所感染,将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Duplan太太工作于一个儿童日托中心,她知道自己出于感染CMV的特殊危险中,因此要求诊所对其进行CMV感染检查。 经过多次请求后,Duplan太太最终接受了CMV测试。测试结果表明:Duplan太太在其怀孕的前三个月初步感染了CMV。尽管实际测试已表明了可能的结果,诊所的护士却告诉她对CMV具有免疫能力。不合标准的照护继续进行。医生没有同Duplan夫妇谈论CMV的感染问题,也没有跟踪检查病毒是否正在破坏他们的未出生胎儿。Duplan夫妇证实: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存在一种能导致高度出生缺陷危险的活性感染的话,他们会采取堕胎措施。法庭特别指出:针对美国政府提起的这一诉讼并非建立在医生有义务同Duplan太太探讨堕胎问题的观念之上。相反,法庭将其判决建立于它所发现的以下事实基础上:医生有法定义务为Duplan太太提供关于其胎儿危险性的充分信息,以使其能够对是否考虑堕胎作出明智的判断,但医生违背了这一义务。至于护士,“国家的一般照护标准规定护士不得向病人解释检查结果。”但是,当一个护士进行了解释时,该规定要求其给出的是准确信息。法庭发现本案中该护士违反了照护标准要求的义务,由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B、关于“不当生命”之诉
与“不当出生”相反,除了几个例外的审判例,法庭普遍拒绝承认“不当生命”为侵权诉因,即使是在那些生而有缺陷孩子提起的最令人同情的诉讼中。这一司法上的谨慎态度部分上源于,从理论上讲它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否定的事实。“不当生命”之诉中的原告主张并非是他们不应当被有缺陷地出生,而是他们压根就不应当出生。这一主张的本质是:孩子的生命是“不当的”。审理前述Blake v. Cruz一案的法庭也拒绝接受承认如此一个诉因,认为 Dessie Blake 并未遭受任何基于出生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上可认知的“不法性”。即使认为在爱达荷州“不当生命”是一种司法上可认知的侵害,损害赔偿额的不可计算性在任何情形下将排斥对该诉因的认可。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的Wilkins法官提出了孩子能否就其被出生的状况提起诉讼的问题,认为对其回答应是否定的。因为正如其父母主张的:如果没有被告的疏忽,孩子不会被生养。那么,如果他被允许向被告提起过失侵权之诉,将会出现逻辑上的根本矛盾。这个国家最普遍的规则是:医生不应对因其过失而生的孩子承担责任。在Payto v. Abbott Labs一案中,法庭面临一个具某些相似性却又不同的问题。在该案中,法庭阻止一个认为如果其母亲不使用被告提供的药品就不会生下自己的妇女就其经受的因其母亲服药而引起其身体与精神上的损害赔偿要求。法庭认为:“使原告存在的可信方法的提供者,不应对该方法不可避免的伴生后果承担责任。”
在盐湖城提起的一个案件在犹他州最高法院得以立案。Terry Borman 与Marie Wood声称:医生对显示其1岁女儿生而患有某种综合症的检测结果轻描淡写,未向他们说明其严重性。这对夫妇的律师Thomas Schaffer认为:他的委托人从未提到过会实施堕胎,“我们所说的问题是他们应享有作出某个指导性决定的权利。”尽管诉讼为了孩子与父母的利益主张赔偿,但律师认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犹他州法庭是否将承认孩子的诉讼主张。他说:“我不认为孩子的讼案同父母提起的讼案一样有力。父母可以说:看,我们不得不抚养这个孩子。”在此之外的几个案件中法庭否决了基于孩子利益所提出的权利主张。在另一例由孩子提起的“不当生命”诉讼中,医生的律师认为:医生们不应向原告赔偿,因为并不是他们引起她出生上的缺陷,也不应就她生存的事实负责。“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在讲的是孩子应当死亡。什么可以消除对孩子的损害?死亡,结束生命”,律师辩称:“我想象不出10年后孩子会站在这里说——我宁愿会死亡。”类似案件的医生代理人Ann Ruley Combs律师向法官陈述,认为他们不应当承认一个“不当生命”之诉,医生的任何可能的过失并不能给予孩子要求赔偿的权利。“如果这个孩子关于生命有权提出主张,意味着我们在创造一种每个孩子都有期望得以完美出生的权利。”俄亥俄生命权利协会也极力促使法庭否决该主张。 立法顾问Mark Lally认为:“你们所说的情况是唯一避免伤害的方法是使孩子流产。这等于贬低性地说,她的生命不值得存活。这不应当是我们的法律所趋。”
某些学者的态度有所不同。如在俄亥俄州的案件中,Alicia一经受孕便患有天生瘫痪,Patricia 与 Lawrence Heste希望该州高级法庭允许其6岁的女儿就其出生控告她的医生。法庭否决了该诉请。但一位名为Betsy Malloy的辛辛那提大学的法学教授是健康照护与残障民事诉讼方面的专家,她对此评论:“这显然是具开拓性的法例”, “我想这种类型的案例会越来越常见”。并且她预言:随着出生前遗传检测的普遍性以及不同形式的检查被应用,州法院将会见到更多的相类诉讼。这些诉讼为了父母的利益而得以提起,他们或者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检测结果,或者从来不知道需要实施一种特殊的检测。
C、关于“不当妊娠”之诉
在“不当妊娠”的情形,一个生而正常与健康的孩童能否视为对父母的某种损害?许多法庭遵守的准则是,从法律上讲,不能将任何一个健康孩童视为对其父母的伤害,原因正如某一法庭所阐明:作为一种共享的情感,这种无形却极为重要、不可计算而无价的父母身份“利益”,远远超过任何金钱上的负担。但有些判例认为一个“额外”的孩童对其家庭构成了侵害。例如某法庭进行了如下阐述:从公共政策角度讲,避孕失败不会产生任何损害,但从法律上讲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成千上万的人天天采取避孕措施来避免发生“被告认为是一种利益而绝不是损害”的结果;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们,以其行为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感受。
(2)何种赔偿请求可以获得支持?
在Viccaro v. Milunsky案,Viccaro 夫妇于结婚之前咨询了被告医生(一个遗传学专家)关于Amy成为某种先天性功能紊乱疾病的患者或携带者的可能性。Amy家族的几个成员被声称患有此病。这是一种具严重损坏性的疾病,它能影响到人的皮肤、头发、指甲、神经细胞、汗腺、眼睛与耳朵的部分以及其他人体器官。被告得出结论:Amy未患此病,并且也无进一步发展此紊乱病症或影响后代的可能。依照该医嘱,Amy结婚并怀了孕,于1980年生下了一个无该病症状的女儿。但之后于1984年出生的Adam却严重患有此病,将终其一生进行治疗并承受身体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Viccaro夫妇向被告提出了损害赔偿的主张。
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诉讼成立,哪些是可救济的损害?该问题提出了6项专门与可能要求:1、与抚养孩子有关的经济负担;2、满足孩子医疗与教育特别需求的相关费用(在成年前);3、父母因孩子需要而提供的特别照护而生的费用,包括可得收入;4、父母因生育与抚养孩子而生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害补偿;5、孩子从事社会交往而生的花费;6、孩子接受社会服务而生的花费。
该庭的Wilkins法官主张应由Adam的父母而非Adam本人作为原告。他认为:在理论基础上,很难推论被告医生违反了对Adam负有的任何义务。但有一点可以被提出:Adam的确作为被告疏忽的后果而存在,并且他出于医疗照护、教育及其他需要而引起实在与专门的花费。正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使得有些审判法庭支持象Adam一样的孩子可以就其一生中由于遗传缺陷所产生的那些特殊费用主张补偿。但是,只要Adam的父母被赋予就由Adam的遗传缺陷而生的特别费用向被告索赔的权利,Adam没必要再就那些费用提起自己的诉讼。同时,如果孩子生而患有遗传性功能紊乱,几乎所有法庭都会支持父母就与该病相关而发生的专门医疗费、教育或其它费用向过失医生提起的索赔要求,唯一相反的权威例证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与密苏里州。法庭赞成通常的规则:即Viccaro夫妇有权就与照顾Adam有关的专门医疗费、教育费用以及其他特殊损失要求赔偿。如果该夫妇能够证明在Adam成年后仍继续担负其扶持责任,他们将有权就发生于Adam成年后的特别费用主张赔偿。
在马萨诸塞州,父母有义务扶助一个因身体或精神损害而不能自理的成年子女。Viccaro夫妇因被告疏忽而遭受的精神痛苦以及任何由此产生的身体上的损害也都是可救济的。但Viccaro夫妇主张赔偿Adam作为一个正常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损失缺乏根据。被告不对Adam遭受真实存在的遗传病的痛苦的事实本身负责。尽管被告可能对某些损害承担责任,因为依原告观点,如果没有被告的过失,Viccaro夫妇不会生下孩子;但被告不能为Viccaro夫妇丧失了有一个正常孩子为伴的损失承担责任。法庭找不到任何根据以支持Viccaro夫妇对Adam作为正常孩子参予社会活动所带来的花费的赔偿请求。但是有几个法庭允许生而具缺陷的孩子向有过失的医生主张赔偿遗传缺陷给其一生所带来的特别费用,如Turpin v.Sortini案(具遗传性耳聋的孩子可以主张抚养费特别损失);Procanik v.Cillo案(生而患有麻疹综合症的孩子可就专门的医疗费而非一般的损赔主张赔偿);Harbeson v.Parke-Pavis案(孩子可以就其一生中因天生缺陷而引起的特别费用主张赔偿)。
有法庭认为:尽管此类判例中损失的计算可能比较困难,将其与类似非法致人死亡伤害与遭受的痛苦或对配偶权的扩大损失等的固定赔偿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另一种与孩子出生是否构成对父母的侵害问题不相关的争论是:孩子发现自己的出生只是归于一个医生的过失而非父母的期盼;一旦他们的父母宣称他们不值得抚养,孩子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通常来说,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为父母带来的好处是如此之大,远非抚养他带来的身体上、感情上与经济上的负担可比较。然而,当一对夫妇已经作出了不生孩子的选择,或不生更多孩子,那么对他们来讲,孩子的出生至少不是一个纯收益。这是他们的选择,法庭有必要尊重该决定。
(3)是否支持胎儿的抚养费请求?
A、美国实务中对于胎儿的抚养费请求的态度主要有三种:
一为支持意见。
最有利原告的案例可能是Marciniak v.Lundborg一案,该案中的某夫妇已有两个孩子并不再想要更多的孩子,但由于被告的过失而生下了不想要的孩子。起初,如同B案一样,法庭拒绝了一系列针对承担孩子抚养费责任的否定性论点。法庭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使被告就侵权行为而生的可预见的那些损害承担责任。法庭拒绝就给孩子带来的心理伤害的争论,声称:诉讼本身是孩子抚养费损失问题,而非使他们摆脱一个并不想要的孩子。很显然他们想保留这个孩子,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一个孩子所需要的宠爱、关心以及感情上的支持,但这一切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供养、负责衣食、教育及其他抚养孩子所需的经济手段。这正是诉讼所关心的,并且相信这个孩子在长大后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减轻家庭对孩子抚养费的经济损失能够很好地增进包括孩子在内的整个家庭方面的幸福,而不会给其带来损害。诉讼也不会引发降低人类生命的圣洁性的后果。法庭没有察觉提起本案的Marciniak夫妇有任何贬低其孩子生命价值的表现,相反,他们在力图使之提高与增进。法庭反驳了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原告并未采取通过保留孩子或堕胎的方式而减轻他们的损害。“我们并不认为期望父母在孩子与诉因之间作出本质选择是合理之举……堕胎与否纯属私人问题,其中深层次地包含了道德与宗教方面的信念”。但是,尽管法庭结论认为被告应对可预见性损害承担责任,但它拒绝将该责任扩至孩子成年以后。既然本案并未包括孩子成长受到严重阻碍的情形或存在其他需要救助至成年以后的理由,那么则没有道理突破这里的界限。
另在Burke v. Rivo案,已有三个孩子的波克家经历着经济上的困难,妻子希望重新工作以补给家庭并完成其工作目标。她约见被告与之讨论不想再多要孩子的愿望。被告介绍了一种称为Bipolar canterization的绝育手术,并保证能使她将来不会受孕。两年后,该妻子生下了第四个健康的孩子。于是她又不得不接受了另一种绝育手术。波克夫妇声称:“如果被告早告诉其妻子有避孕失败的风险,无论风险有多大,她会在一开始便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绝育手术。” 大多数法官倾向于承认作为医生过失结果而生的孩子的父母就与该出生直接相关的损害(有时包括对父母感情痛苦的赔偿)进行赔偿补救,但法庭在父母能否就孩子的抚养费要求赔偿这一问题上见解存在分歧。主要问题是:原告是否有权要求孩子的抚养费赔偿? 依据通常的侵权法与合同法原则,那种损失是原告主张的非法行为产生的一种既是可合理预见、又是自然与有充分根据的后果。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公共政策上的考虑而限制传统侵权与合同损害的适用。法庭推定:并不存在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决定不孕的父母相关的任何此类考虑。同时,一些作为拒绝支持由医生过失而生的健康儿的抚养费的补救的所谓“正当理由”显然不具说服力。这样一种司法主张是缺乏贴切性的:即认为抚养一个孩子带来的快乐与自豪感可以超越该父母遭受的任何经济上的损失,因而就排除了对孩子抚养费的救济。一个人寻求医疗方的介入以阻止其生孩子的事实表明,对那个人来说,父母身份带来的利益并不比生一个孩子带来的负担、经济因素及其他更重要。避孕与不育措施的广泛运用以及每年无数次堕胎手术的实施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人并不愿将成为父母视为一种单纯的积极情形。
法庭赞同孩子出生在任何时候对父母而言都是一种净收益的否定性司法意见,同时坚决拒绝这样的建议——即堕胎或其采用带来的有益性能够构成要求医生就因其过失而使孩子受孕进行赔偿的数额的基础。法庭同样对这样一种理由不置可否:即认为不允许孩子抚养费的救济是因为,如果有一天孩子发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并且是别人支付费用抚养了自己,将会对其产生不利影响。表达了对孩子这一影响之关心的法庭,却在孩子得知自己不被需要时所受伤害未表达任何关心的情况下,允许父母就来自过失医生的某些直接费用请求救济;而一旦孩子得知是他人而非父母被强迫支付了抚养费,这一事实可能会减轻孩子因得知自己曾不被需要的精神痛苦。在任何情况下,应当是父母而非法庭有权利来断定一个诉讼是否对孩子造成了不利影响以及应否得以维持。法庭同时反驳了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孩子抚养费太具投机性,与医生的过失过分不相称。法庭认为该主张是不正当的,因为预期的孩子抚养费的确定并不比许多在侵权案中天天作出的未来损失的计算更加复杂与不切实际。如果一个医生由于在照护新生儿时有过失,损害赔偿的计算会根据新生儿一生中的收入能力及预见到的医疗费来确定。孩子的抚养费远比以上情形更容易确定。假如在此类案件中存在否认正常侵权损害救济的正当性的话,那也不应当是孩子抚养费不能合理计算或该费用给医生施加了过重负担。
还有人认为法庭不应当允许“不当出生”案中的被告施加于原告一个不需要的利益;同时,原告的救济不因由被告侵权而生的任何利益而减少。例如,一位评论者撰文:当然,一个孩子的出生可能会给其父母带来某种无形的情感上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并非父母所要求与有能力支付的。
二为反对意见。
Burke v.Rivo一案中,O,Connor法官不赞成赔偿依据侵权或合同理论进行估价,并作为对抚养费的补偿,或者向一个绝育手术完成后或给出建议与保证后仍出生的孩子承担责任;也不认为损害赔偿能够反映孩子出生对其父母、家庭经济状况或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这并非普通的医疗误诊案,其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对人类新生命的缔造,并且在构想一个适当的损赔规则时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侵权法源于社会价值并应当促进适当公共政策的运用。正如多数不赞成抚养费救济的法院那样,O’Connor法官认为不将孩子对父母的价值区分开来的赔偿判决对被告不公平,也是不可忍受的。
在其看来,一个致力于寻求一个孩子对其父母价值多少的审判同样无法忍受。这种审判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是因为它要求决定一个孩子对其父母而言是否意味着一种损失。如果这个孩子并未出生,其父母是否更富有?这个孩子的价值是否小于抚养其所需花费的费用?如果价值小的话,到底小多少?即使这种审查会产生一种合理且并不具投机性的结论,一种令人疑惑的建议是:损失与利益的平衡本身实际将孩子当作了私人财产。这一审查违背了国民必须与每一个人类生命相一致的尊严性。强调对孩子亲权损失或其死亡的损赔额进行估价的假设成立基础是:孩子生命是有价值的,其损伤或死亡或归结为对父母的损失。这种假设与国家公共政策中应当体现的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不一致。价值大小的比较决定了被告的损赔额。的确,正当的公共政策需要作出一种确认:对他人而言构成损失的是孩子的伤害与死亡,而非其生命本身。拒绝法庭信奉的规则并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上的理由。但是,进一步考虑(哪怕是简要地)新采用的规则对这一国家的孩子与家庭产生的潜在的不利影响是妥当的。“致力于加强与鼓励家庭生活以保护与照护儿童是这一国家的政策”。该种政策确实不能服务于(事实上它也未服务于)这样一种损害赔偿规则:即要求父母(即使其将胜诉)说服法官或陪审团相信其孩子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如孩子抚养费损失更大。加强与鼓励家庭生活以利于孩子保护与照护的利益是合法与有力的。的确,应由国家来决定是否采纳一项损害赔偿规则,这一规则会鼓励有害于家庭的诉讼——该类诉讼将产生这样的结果,孩子最终会发现自己不被父母所扶养(因为他们不想要他),而实际上是被一个不情愿的陌生人扶养长大。
三为折衷意见,即认为应具体分析原告寻求避孕的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决定应否支持赔偿。
例如在Hartke v. Mckelway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认为: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裁决否定了原告要求赔偿抚养费的请求,因为证据表明原告寻求避孕并非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同时法庭推断她对所生的孩子事实上持赞赏态度。
“不当出生”案中存在赔偿数额计算方面的特别困难,因为孩子的出生对特定父母的侵害程度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随着具体情形与期望而变化。父母可能在事实上获得了一个他们极为喜爱的孩子,并私下认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利益。因为父母避孕原则是多种的,也许因为社会经济上的原因,为了避免其工作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或者为了节省家庭资源;也许由于优生因素,避免一个残疾儿的出生;也许因为治疗因素,避免对孕妇及出生儿带来危险。当一对夫妇决定不育的原因仅仅是治疗或优生方面时,一个健康儿的出生,即使是非计划的,对其父母而言最可能是一种巨大利益。在此类案例中,法庭倾向于认为将孩子的巨额抚养费强加于被告医生是不公正的,并且担心基于冲动或对医生的偏见产生如此一个判决。
这样,在考虑孩子的抚养费应否被支持这一问题时,多数法院与评论者将重点置于不孕原因的分析上。例如,在最早的“不当出生”案中法庭明确指出:“手术的目的是挽救妻子的生命,与之相伴的是孩子的意外出生。补救怀孕与生育手术的费用不符合声称的目的。妻子脱险了。原告未失去妻子,相反被祝福成为另一个孩子的父亲。诉请的费用对孩子出生来说是意外,它们远非基于手术本身的目的而生”。其他一些判例同此结果。法庭倾向于赞成实情调查者将重点置于夫妇避孕的原因之上,以此来决定孩子的出生(从衡平法的角度)是否对其父母构成了侵害。例如,在夫妇避孕主要是治疗或优生方面的原因的情形下,可以推测,意外出生的健康儿对其父母构成侵害的程度只是该父母所体验的可能有害于母亲或可能出生一个残疾儿的异常的惊吓。法庭与陪审团可以假定父母珍视该孩子,通常的抚养费用将被孩子出生带来的特定利益所超越。所以很清楚,一旦发生在母亲身上的生育孩子的特殊危险消除,从公平意义上讲,对她而言有一个孩子会是一种积极的经历。在这些情况下,支持孩子抚养费只会给孩子的家庭带来意外收获。
B、损害能否为胎儿带来的父母身份利益所充抵?
对于这一问题同样存在赞成与反对的对立态度。
允许对孩子的抚养费损失进行补偿的法庭,通常要求抚养费损害可以被胎儿带来的父母身份利益所抵销。也许正如一位法官所言,允许以抚养利益抵销损害赔偿“只不过是将抵销用于减弱对医疗侵权人与其保险人金钱上的震动。”如果这样,仍然存在的事实是削弱判决力的愿望被普遍共享,并反馈出深层的价值。这一愿望也许基于这样一种感觉:即使是在避孕与家庭计划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今天,夫妻也通常要面临预想不到的怀孕。
有些管辖法院支持赔偿一个正常孩子的抚养费直至其成年;但这一费用可被父母自一个正常、健康孩子得来的利益相抵销。如此一个经事实审查得来的均衡要求将孩子抚养经济损失与自一个正常、健康孩子而来的感情所得(转换为货币价值)相比较。这些法院认为:此种比较与侵权法表达的一般原则相符合。为数不多的几个法院则认为:因为赋予父母的利益并不影响侵害的经济利益,因而不应当确认减少孩子的抚养费损失。如果父母不孕的目的是基于优生(如避免一种可怕遗传缺陷)或治疗上的原因(为母亲健康考虑),并且出生的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司法上支持正常孩子自出生至成年的抚养费的数额会远低于基于经济上的原因寻求不孕而失败的情况。法庭由此得出结论:除了前述的可救济的损害赔偿,如果父母不孕是基于经济或财政上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得以就一个正常健康但不需要(至少开始)的孩子的抚养费损失要求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审查者应当就父母可能自孩子身上得到或将得到的利益与孩子抚养费损失相抵偿。
然而,在前述Marciniak v.Lundborg一案谈到抵销问题时,Wisconsin法官引用920条评论:“痛苦与心理遭遇方面的损害并不会通过显示原告的收入能力由于被告的行为增强而减轻。”这样以来,经济利益仅能与经济性损害相对应,发生感情利益仅能与感情伤害相对应。在这里,被告试图将感情利益与经济损害分割开来。父母所作的不要孩子的决定中包含了放弃可能来自另一个孩子的感情利益的决定。当父母作出决定放弃这一丰富感情的机会时,强加该利益于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必须以抵销其已经证明的经济损害赔偿的方式付出什么的作法,显然是不公平的。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相同争论很普遍。此外,孩子可能赋予父母的任何经济利益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同样,Viccaro v. Milunsky案中的O`connor法官对孩子的抚养费请求以及相关的抵销问题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对一个法官或陪审团来讲,致力于相关抵销问题的审查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并得出结论:即使抚养一个正常孩子的经济负担在某些情况下是实际存在的,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它不应得到补偿。法官或陪审团衡量一个正常孩子的出生带给其父母多少净收益的假设与人们应对人类生命怀有的尊重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于这种审查对社会的危害性表现为,对家庭与孩子的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父母因其主张的违法事实而获赔偿的价值。尽管抚养一个不正常孩子的负担要比抚养一个正常孩子的负担重得多,但支配的价值与原则是相同的。
2、欧洲法态度
欧洲侵权法不承认美国普通法中出现的上述“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称谓。两条基本规则概括了欧洲的共同观点。其一,任何人都无权决定自己之不生存,这已被普遍接受。所以一个人被孕育或者堕胎这一事实不能对那个人构成一个诉因。同样,如果明知存在孕育或遗传方面的缺陷,但忽视这种影响而导致出生的孩子严重残障,也不构成一个诉因。 例如英国的“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认为:“被告不对孩子就以其专业能力负责向孩子的父母亲提供治疗或咨询意见中的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个原则是,尚未出生者享有人格尊严权(如法国宪法保障“从生命之初就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因此,责任与损失产生于出生之前或者出生之后无关。从而认为,因为未出生者没有法律上的能力所以在取得法律上的能力之后也不能对出生前受到的损害提出诉讼的观点,在宪法上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将一个残障的孩子在法律上与缺陷产品同等对待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在堕胎失败给胎儿造成伤害并在后来影响其终生的案件中,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法国行政法院1989年9月27日所作出的判决:即使失败的堕胎没有对胎儿造成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妇女违背丈夫的意愿做流产手术,尽管堕胎不构成刑事犯罪,父亲也有权请求对物质损害/非物质损害的赔偿,因为这在技术上是不法的。
但欧洲法并未明确规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不想受孕或者知道胎儿有“缺陷”而要将其堕胎的父母有权请求赔偿。对于因健康原因而不想要的孩子,欧洲国家认为是被冠上了一个不幸的美国称呼“错误生命”。这些案件通常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在父母亲一方声称做过绝育手术后或在父母亲接受了不适当的避孕措施后怀孕,或者是在堕胎失败后出生。无论是对被告的行为进行合同上的考量还是进行侵权行为的考量都无关紧要,应当一般接受的做法是,既不能将孩子的抚养费用也不能将与其出生有关的物质上的或非物质上的不利作为可以得到救济的损害。不到一半的欧洲国家的法律采取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倡导者有丹麦的法院。荷兰的一些法院,如阿纳姆地方法院1974年11月28日的判决和1976年2 月26日的判决:在父亲输精管结扎后孩子出生,法院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该男子受到了损失,但是赔偿抚养费不符合荷兰法律制度的规定;又如赫特根布奇上诉法院1983年5月17日的判决:失败的绝育手术,不对痛苦和疼痛予以赔偿,仅对收入损失以及与怀孕有关的费用予以赔偿。法国行政法院,如1982年7月2日的判决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并不产生导致其母亲当然得到救济的损害.....除非存在特殊情况。意大利最高法院。意大利最高法院声明,“由于堕胎失败致父母亲之经济损失不能得到赔偿”。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法院赞成对抚养费用进行有限赔偿。
有关判决认为:将一个婴儿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构成侵权,因此无论是父母还是秘密解除双方约定避孕措施的妇女都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在上述情况下,各国一致认为任何人都没有主张不被生下来的权利。区别仅在于处理结果上,对于出生前就已经严重残疾的案件,德国法院仅赋予了父母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法国法院则同时赋予了父母和婴儿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依欧洲侵权法的精神,没有抚养,人的生命无法延续,所以不可能对延续生命作出肯定的判决而对支付抚养费用作出否定的判决。如果解除对孩子的照顾与抚养既是自然权利又是其父母的基本义务这一原则,将导致大量的问题。此等解除不仅严重违反家庭法,而且可能导致年长的兄姐提出要求其父母亲少生弟妹的主张。另外,对出生健康的孩子的抚养费予以补偿可能会需要许多新的规定;按照父母亲的受益情况调整医生承担的赔偿额也将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孩子给他家庭带来了欢乐而且他也可能是“有用的”。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疑问:尽管父母亲对孩子的抚养通常必须超过这一成年年限,但是民事责任法的哪一方面能够证实将对补偿限制于孩子的未成年期是适当的呢?如果父母亲在成功起诉外科医生之后又有了另一个孩子,他们向外科医生请求前面孩子的抚养费的权利是否应当被撤销呢?人们是否能提出夫妇因没有克制性交或没有更仔细地学习避孕指南或者声称做过绝育的男子对其性伴侣未做早孕检查负有责任而有共同过失呢?如果实际上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父母亲作出了不做堕胎手术的决定或者决定不将孩子交给他人收养,是否就应当切断因果链呢?即使是在这个流行避孕的时代,一个孩子也不是人们可以随便从定单上取消的某种东西。给予母亲补偿以防止其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希望堕胎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判决医生对孩子的出生承担责任可能会鼓励妇女终止妊娠。
(二) 父母为侵权主体
依多数国家的法理,子女出生后,父母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其人身权的,应依侵权行为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如果父母的侵害行为发生在子女出生以前,例如父亲的遗传病染至胎儿使其生而缺陷;夫妻相殴,丈夫踢打妻子腹部致胎儿天生残疾或痴呆;医生开药不当而母亲在此基础上基于过错加大药量而使胎儿受到侵害;身为孕妇的竞技者参加比赛为对手伤害,或孕妇因病住院或生产时与医院签定了免责条款等,父母应否承担责任?父母的过错或允诺能否产生“阻却违法”的后果?当然,“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也包括了“不当出生”中因强奸或无效婚姻所生子女的救济问题。
在此问题上,比较各国的态度:
1、在美国法上
子女因出生前受父母侵害而请求损害赔偿的实例很少。在Zepda v. Zepda一案,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曾明白表示,使人出生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关于子女应否承担父母的过错,侵权法权威教授Prosser在其有名的《侵权行为法》(Law of Torts)一书中作了如下说明:父母的过失由其子女负担,是一项不适当的古老原则,因为子女与其父母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同一性。
在C.A.M v.R.A.W一案中,生下一个健康孩子的原告向被告(孩子父亲)提起了诉讼,声称被告使她确信他做过绝育手术。法庭在审阅了大量涉及该领域的诉讼案后,得出结论:“基于一对自愿发生性关系而出生的正常健康孩子,排除了法庭调查可能在性交之前或性交过程中由任何一方作出的关于控制出生的声称的必要性。”法庭区分了该案与 I.P.M. v.Schmid Laboratories一案,该案中一对夫妇控告某保险套生产商,声称由于被告的保险套的缺陷导致了一对正常双胞胎的出生。法庭允许被告对该父亲在保险套的错误使用上的疏忽提出交叉诉讼。
但在奸生与欺诈婚姻情况下,法院基于公益的考虑,往往不支持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如在William v. State of New York一案中,某妇女因精神衰弱住进纽约市神经医院治疗,因医院监督疏懈,导致她遭到强暴,因而生产一子,名叫William。该子认为医院未尽适当监督义务,使其母遭人侮辱,致其出生,从而不能获得一个正常孩童应有的家庭生活、父母的抚养及照顾,财产权益均被削夺,并蒙受私生子的污名的讥笑及其他不利益,主张纽约州应以医院所有人的地位,对其所受损害负承担赔偿责任。纽约州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认为被告强暴原告之母时,原告尚未出生或受孕的事实对于侵权行为的成立不发生影响。但二审法院废弃了此项判决,Gibson法官在其简短的判决理由中称:“承认此种请求权,使对一个人的出生负责赔偿一项难以确定的损害,自立法政策言,实属不妥,欠缺合理依据。”1966年12月29日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意此项观点,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权,尽管具有新奇性,但该案情形特殊,影响深远,应甚重考虑;再说,就法律构成要件而言,使某人在此种情形出生而不在他种情形出生,很难认为是不法致他人受有损害而构成侵权行为。
又如Zepda v. Zepda一案,被告依“不法使人出生”为理由,向生父请求损害赔偿,产生新的争议。该案被告为波多黎各的黑人,虽已结婚,却自称未娶而向某白女求婚,并与其同居。该女怀孕之后,发现受骗,拒不结婚,所生的孩子认为自己生而为私生子,且为杂种,因此对其父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芝加哥地方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二审判决原告败诉,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也维持原判决。各级法院判决之所以拒绝承认此种“不法使人出生”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有基于事实的考虑,有基于法律上的理由,王泽鉴先生认为可归为四点:首先,在1960年美国的非婚生子女数额庞大,假若确认使人以非婚生子女地位出生构成侵权行为,则容易引发诉讼,势必造成社会问题。其次,这种新的侵权行为一旦被创设,则不满意自己肤色、患有遗传病或羞于父母声名的人也会主张损害赔偿,甚至不免有人会以“未经同意被出生,致在人间受苦”为理由提起诉讼,请求的依据将无限扩大,漫无边际。第三,社会变迁及科学进步,使法院面临新的问题,必须改革旧法,补充或创造新的制度,以期能适应变动多端的时代。然而就本案而言,法院无立即采取措施的必要。其所涉及的法律论点虽然新奇,但问题本身及社会背景,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不必急于创设新的侵权类型,速求解决。第四,从损害赔偿的观点,所谓损害是就减损被害人的权益而言。在本案中,原告于出生前本不存在,被告使其出生,由无变有,纵原告对于自己出生之状况不满意,从法律观点言也难说受有损害。
如果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其母亲被治疗师诱奸的结果,审理法庭的部分分析结论应否被改变?参看Poor v.Moore一案,该案结论为:母亲有权取得就孩子的照护而生的实际、合理的费用以及未来赡养孩子之付出的部分补偿…孩子孕于其母亲被侵害过程中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成文法与普通法上的赡养责任。”法庭对以下观点的明智性提出了置疑,即允许“父母一方就其孩子的不当出生向另方提起诉讼,一方利用孩子作为侵权主张的损害赔偿基础来对抗另一方的作法不会给孩子带来多少好处”。
2、英国法上对其尤为关注。
最值注意的是英国最近法制的发展。英国法制委员会在其“出生前侵害之损害赔偿”的资料文件中,曾初步认为,依英国普通法,父母于其子女出生之前加以侵害的,仍应当负侵权责任,此项原则应当维持不变。对于这一点,各界人士见解不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很大。但多数意见倾向认为子女对其生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律师协会提出如下备忘录:“就逻辑及原则而言,生母怀孕期间或怀孕之前,因其过失之作为或不作为致胎儿受有损害,对其所生之子女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任何法律体系,于若干领域,逻辑及原则应对社会之可接受性及自然感情让步,此项特殊责任,即属此种领域。”英国法制委员会在其正式报告中,建议采取折衷的立场,即生母无须负责,但生父仍不免其责,并于“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第1条第1项设定该规定。之所以认为生母无须负责,目的是为了顾全亲子关系,避免作为父母婚姻上的攻击手段,以及过分限制生母的社会生活;之所以认为生父不免其责任,主要理由为上述顾虑并不存在,再说,生父与胎儿不属同一体,肇致损害机会较少,而且生父并不当然为生母之“夫”,所以原则上应当适用普通法的一般原则,使生父就其所加于子女的损害,负损害赔偿责任。
3、德国法上。
在父亲以梅毒传染其子的案例中,德国S高等法院肯定生父应当负侵权责任,最高法院则以侵害行为时被告尚无权利能力为由加以否定,但都没有提及父母的侵害行为本身是否具有违法性的问题。在医院输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至于父亲或母亲于怀孕之际,因患有一时或先天疾病,而将此疾病传染于受胎的子女,致其健康自出生时起即遭受损害时,是否构成对健康的损害,抑或在此情形根本不发生损害赔偿,如果无父亲或母亲可非难的行为,则该孩童根本不能出生,因本案原告健康的受损害,因可归责于被告医院之行为所致,故本庭无须作成判决。”
由此可知,德国实务上早已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是未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学说方面,学者Selb认为对胎儿健康的侵害,除故意者外,合法与不法的界限,很难断定。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的人格权互相对立,强制孕妇从事维护胎儿的生活方式,对民法而言实在是一种奢望,对母亲生活方式的控制,既违反其利益,实际上也无法实施。因而强调,因德国民法对此问题没有明文规定,父母侵权责任的界限的确难以划定,仅能参酌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填补漏洞。基于这种认识,Selb认为单纯因受胎怀孕,致其子女受损害的(例如遗传病),父母不负责任。至于父母因故意或过失,以外在原因致其子女于出生前遭受损害时,则须负责。
此外,《澳门民法典》第63条第4项规定:“然而,生父母无须就受孕时对子女造成之畸形或传给子女之疾病负责,亦无须就受孕后对胎儿造成之损害负责,但属故意造成之损害者除外”。台湾学者认为:父母明知或可知其有传染病,如性病、肝病等仍怀孕而生下带病子女,该子女不具有请求权,理由有在于其受损害时无权利能力,而在于没有父母,他们根本不会出生,自无法确认其有损害的存在。
笔者认为:对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应参酌多数国家的法理:一般情形下,如子女生而患有遗传性疾病,基于公益上的考虑,不宜支持子女以此为诉因向父母提起诉讼;但在奸生或由欺诈婚姻所生的例外情形,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父母于道德或法律上都具有可受谴责性,因此应对子女向其提起的赔偿请求作适当考虑。但在父母有一般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忽视生母与胎儿形体上的一体性与特殊性,既然实践中父母可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替未成年人,由此而为的允诺会产生阻却违法的效力,对胎儿也应当适用该法理。
六、小 结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胎儿的损害赔偿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问题,用传统上简单、一概而论的研究方法已经显得不甚合适。笔者通过本文,对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个基本建议:即应区分不同侵权形态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探讨。具体而言:
1、对人于出生前受侵害致健康受损的情形,尽管我国立法与理论未多论及,但实务中支持该诉因的法院实际上已经在运用一般侵权法原理解决问题。然而对其处理尚未上升为一般规则。笔者以为:人因出生前的侵害致健康损害时,由于实际受侵害的人是某个因受孕期间受侵害生而健康受损、但现尚生存之人,胎儿损害赔偿问题转而成为符合侵权法理论但主体稍显特殊的类型而已,所以可将因出生前侵害而健康受损的人视为该类损害赔偿案的请求权主体,使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简单化为探讨一般人身权(本文指健康权)受侵害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应遵循侵权法一般原理,只须侵权责任要件齐备即可支持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2、对人于出生前受侵害致死亡的情形,应包含因侵害致出生后不久即告死亡与致出生前死亡(即死产)两种类型。在因第三人过错而致胎儿流产于母体的情形,曾有以此为诉因提起的个别诉案。但在因最常见的医疗操作过失致以上情形发生时,笔者反而未发现我国实务中的相关判例,这从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了立法者与司法界对这一问题的漠视态度,当然与我国的法律意识层次与传统心理也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此类诉讼必将占有一席之地,立法与司法界将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途径。笔者建议:在前种情形下,由于胎儿出生后先是存活,既而死亡,因此,即使时间再短,此时的“胎儿”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的独立的人,可适用非法致人死亡的一般原理处理之。但对于死产的情况,应将其视为母体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还是视其为独立的“人”,以及应如何很好地处理两种类型在处理结果上可能出现的冲突?这些问题还尚须学界结合实践发展作出进一步研究。
3、对“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情形,我国立法与学界均未涉及。但司法上却已有了相关判例,如前述由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脑瘫婴儿案”,原告获赔55万元;以及2000年发生在广州的基于医院检查过失未发现胎儿的缺陷而引起的“女婴出生少右臂,父母向医院索赔”案等。以上诉因可归为本文所述的“不当出生”。但由孩子本身作为原告的“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之诉则未见其例。笔者赞成美国实务中对“不当出生”诉因的一般认可态度,但认为应设立相应的请求权规则,使问题的解决有所依据。同时,笔者反对“不当生命”与“不当妊娠”的诉因,认为在目前状况下对该问题尚须进一步观察与研究,否则可能会引发与人类生命价值观的冲突。
4、对父母为侵权主体的情形,笔者主张,我国应参考多数国家的法理:基于公益上的考虑,一般不宜支持子女以生而患有遗传性疾病之类诉因提起的诉讼;但在奸生或由欺诈婚姻所生的例外情形,对子女向过错方提起的赔偿请求,应作适当考虑。应充分考虑父母与胎儿关系的一体性与特殊性。
文章结束之际,笔者的个人感受是:鉴于问题的复杂,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研究仍须进一步深入;笔者有志于继续探讨。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一个研究的合理切入口,以期引起法律同仁对这一问题关注并给出更好的建议。
注释:
Viccaro v. Milunsky,Supreme Judici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77,551 N.E.2d 8
www.findlaw.com
Gleitmanv.Cosgrove,49N.J.22,227 A.2d 689,1967
Gleitmanv.Cosgrove,49N.J.22,227 A.2d 689,1967
www.findlaw.com
Blake v.Cruz, Surpreme Court of Idaho,1984 108 Idaho 253,698 p.2d 315.
Payto v. Abbott Labs,386 Mass,540,557-560,437 N.E.2d 171,1982
www.nolo.com/lawcenter.
www.nolo.com/lawcenter.
参看Terell v.Carain[Terell .v.Carain,496S.w.2d124,131]案(一个“不需要”之孩子的出生不仅对其父母与其自己,也对其兄弟姐妹会是一种灾难)以及Terell v.Carain,cert.denied,415 u.s. 927,94 S.Ct. 1434,39 L.ed.2d484(1974)案的态度。
Viccaro v. Milunsky, 406 Mass. 777,783 (1990)
Turpin v.Sortini,31 Cal.3d 220,237-239,182Cal.Rptr.337,643 P.2d 954,1982
Procanik v.Cillo,97 N.J.339,352-354,478 A.2d 755,1984
Harbeson v.Parke Pavis,Inc.98 Wash.2d 460,479-480,656 P.2d 483,1983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Kashi,The Case of the Unwanted Blessing:Wrongful Life,31U.Miami L.Rev.1409,1416(1997)
Burkev.Rivo,Supreme Judicial(Court of Massachusetts,1990.406 Mass.764,551N.E.2d
Hartke v. Mckelway,United States Coun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1983,707.
Hartke v. Mckelway,United States Coun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1983,707.
第二重述1979年第920条.
Hartke v.Mckelway一案的争议。707F.2d1544,1557-1558n.16(D.C.Cir.1983)
Marciniak v.Lundborg,153 Wis.2d 59,450 NW 243 1990.
Viccaro v. Milunsky, 406 Mass. 777,783 (1990).
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被维持。在Aiedale NHS Trust v.Bland [1993] 1 All ER 821 案件中,英国上议院正确地认为,就一个在谢菲尔德的足球场发生的灾难之受害者而言,没有义务延长永远不会苏醒的患者的生命。转引自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7页。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8页。
如西部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对妇女的绝育手术失败的赔偿中,孩子出生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神圣的事件,所以公共秩序禁止对抚养费予以补偿。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09页。
参见奥地利最高法院1994年1月27日所作出的判决,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4月17日判决为基础,并进一步指出,非婚生的父亲即使该非婚生子女的母亲在导致怀孕的每次性行为之前对她的怀孕能力故意作了虚假陈述,也不能向她就该非婚生子女抚养费要求赔偿。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第74页。
雷斯蒂安?冯?巴尔著:《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第712-713页。
Zepda v. Zepda ,1963,41111,1pp.2d 240,190 N.E. 2d 849
C.A. M v.R.A.W,237N.J.Super.532,568 A,2d 556,1990
I.P. M. v.Schmid Laboratories,Inc,178 N.I.Super.122,428 A.2d 515 1981
William v.State of New York,34 U.S. Law Weeks,1965 260 N.Y.S.2d 953.
Zepda v. Zepda, 1963, 411 II, 1pp. 2d 240, 190 N. E. 2d 849.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Poor v. Moore,791 P.2d 1005,Alaska 1990.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第285-287页。
BG HZ 8, 243.
同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主要参考书目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台)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Henry Campbell Black.M.A,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
Report on Injuries to Unborn Children, The Law Commission No.60,(1974)Cmnd.57090.
郑冲,贾红梅 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Marc.A.Franklin,Frederick I.Richman,Robert L.Rabin A.Calder,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Fifth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
Prosser,Law of Torts,Third Edition,1964.
Working paper No. 47
(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马克昌,比较民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杨立新,吴兆祥,杨帆.人身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Harry Shulman,Fleming James,Jr. Oscar S.Gray, Torts,Third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76.
Robert S.Thompson,John A.Sebert,Jr.Remedies:Damages,Equity and Restitution,Second Edition,Matthew Bender Co.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张新宝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王利明,人格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
杨立新,人身权法总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Charles T.Mccorsneck, William F.Fritz, Damages, Second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52.
William L.Prosser, Hastings,Johm W.Wade, Victor E.Schwartz, Torts,Eighth Edition, 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Press, Inc.1988.
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orts,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1979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黄立,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Edward D.RE, Stanton D.Kraus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Remedies, Third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
Clarence Morris, C.Robert Morris, Torts, Second Edition,Westbury,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0
(美)彼得.哈伊著,沈宗灵译,美国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李亚虹,美国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网 络 资 源
http: //www.findlaw.com/casecode
http: //www.excite.com
http: //www.nolo.com/lawcenter
http: //www.civillaw.com.cn
http: //www.rmfyb.com
http: //www.chinalawinfo.com
http: //www.canada.justice.gc.ca
http: //www.yahoo
http: //www.chinalaw.com
http: //www.gztz.org
http: //www.Lexis.com
http: //www.cinews.net
http: //www.sohu.com
http: //www.sina.com
http: //www.online.jn.sd.cn
http: //www.echolaw.com
出处:载于刘士国主编:《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