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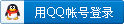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原作者:刘湧
我第一次读谢老关于民间对日战争索赔的文章是一九九九年夏天。那时我刚从日本学习回国,在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语言上的一些便利,有幸协助康健律师在劳工调查中做一些翻译工作。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是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这一跨世纪的国际大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国内始于1995年。康健律师自1996年起就担起“慰安妇”案和“劳工案”的重任,与日本律师以及国际友人一同不懈地努力工作着。
我所谈到的谢老的文章,是谢老与其他六名中国著名法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中国公民李秀梅等诉日本国损害赔偿案和中国公民刘连仁诉日本国损害赔偿案的法律适用意见》。李秀梅案属于“慰安妇”,而刘连仁案属于“劳工案”。该文章发稿于1997年12月28日,是国内较早的关于民间对日索赔法律实务的专家意见。该文就中国公民对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诸如法律适用、管辖、消灭时效、精神损害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于法理的主权第一的法律意见。正是由于这篇文章在法律实务问题上明确主张司法主权,因此,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应处于标志性文献的地位。在现实中,该文章大大地鼓舞了民间对日索赔的仁人志士的斗志,包括日本律师在内,同时也给日本法官以震动。
以上的认识也是我后来才渐渐形成的。当时我读这篇文章时,对其背景情况知之甚少,只是觉得此文不同凡响,份量沉重。
我第一次见到谢老是2000年10月10日,在全国律协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法院审理强制劳工对日索赔诉讼问题专家论证会”上。从会议名称上可以看出会议的重要。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先生亲自主持了论证会。论证会的议题使人联想到七名法学大家的联名文章。可以说,如果没有前面的文章,也不会有这日的论证会。那时,七名法学大家之首的谢老就坐在我的面前。一位谦和安静矮个老人,一身熨烫平整的蓝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时留下的印象且至今没有变。不错,谢老是一位大家,但他没有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作派。也许是谢老一生真诚的缘故吧,他总是以真情实意说话、做事与待人。有谁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呢?
高会长因为谢老亲自出席论证会非常高兴。那天他是亲自到谢老家里将谢老接到协会里来的。他向与会者介绍谢老且称颂不已。高会长说,谢老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且硕果累累,许多人都以自称是谢老的学生为荣。
在论证会上,首先由案件承办律师介绍了民间对日战争索赔工作在日本和在美国的进展情况,以及中国原劳工将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原五家侵权企业的计划。谢老听完介绍后,谦和安静的老人变得激动起来。他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给中国公民个人也造成极大的损害。被侵害人对加害者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理所当然。中国政府是放弃了国家的请求权,但并没有放弃民间个人的请求权。没有谁有权力放弃中国公民个人的请求权。民间对日索赔工作早就应该做了。中国法院受理本国公民的起诉天经地义。这个工作意义重大,但会很艰难,需要有人勇于承担工作。我感谢实际奉献的律师,全国人民也会感谢你们的。谢老言词激越,发自肺腑以至热泪满面,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会后,谢老把我叫到他身边,仔细地问了一些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他认真地听了我的回答后,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同时表示他自己也会与我们共同努力的。谢老将自己的住址与电话留给我,说有事情随时可以和他联系。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家幸运地和谢老的家只有一条二环路相隔,我们是邻居。
谢老出席论证会,使所有出席者受到鼓舞,论证会开得热烈务实。论证会后的两个月后,五名曾被抓当劳工的中国公民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五家日本企业为被告提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经常到谢老家拜访谈论对日索赔的问题,也常把一些最新动态、会议文件送给谢老。每次我去拜访前都要先给谢老打个电话联系。只要谢老在,他都会让我去,从不推辞。我每次去拜访时,谢老总是亲切地到门口迎接,走时一直送到门口。我向谢老介绍情况时,谢老总是认真地倾听,然后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为了推动民间对日索赔工作,谢老竭尽了全力。例如:为了早日在中国法院提起对日本企业的索赔诉讼,谢老亲自给他在某单位的学生打电话,又亲笔写了推荐信让我去找该人联系。又如2002年的一天,谢老对我说,某老将过生日,到时我去找他商量如何推动这项工作。他的学生多,又都分布在各领域部门,他说话比我的影响大。那时谢老的身体较弱,已不大出门了。
2002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律协正式成立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小组聘请了两位顾问,一位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文迟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谢怀栻先生。谢老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该次成立大会,顾问的聘书是会后由高会长亲自送去的。虽然如此,谢老作为顾问仍然是尽职尽责,这是指导小组成员皆承认的事实。
2002年4月26日中国15名原告在日本福冈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与三井矿山的一审判决下来了,中国劳工对三井矿山胜诉。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难得的胜诉判决。日本的舆论界沸腾了,中国媒体也做了罕见的现场报导。我有幸与康健律师和两位原告老大爷亲历了历史的这一幕。回到国内的当天,我妻子告诉我,谢先生昨天和今天都打来电话,说你在日本胜诉了,祝贺你们。还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赶紧给谢老打电话。谢老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他高兴地说:“刘律师,你们辛苦了。中国劳工胜诉了,我从电视中看到了。太好了!”我对谢老说:“康健律师和我约好明天去看您,同时送去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要旨。”谢老高兴地说:“我等着你们。”第二天,我和康健律师去拜访谢老。谢老高兴地接待我们,认真地听我们介绍福冈判决的前后情况,并提出一些问题。谢老很兴奋,他说:“要动员学者多写文章谈论对日民间索赔,也要努力推动在中国法院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工作。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主战场应当在中国。”
2003年是多事之年,被称为“六亲不认”症的SARS瘟君席卷全国。这一年我们失去了谢老。
200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我和谢老通电话,准备将一些资料送给他。电话另一边传来的谢老的话令我非常吃惊,令我至今难忘,而且令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谢老的声音显得有些凄凉:“刘律师啊,我可能帮助不了你们啦。你们要多保重。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了。”
惊愕之余,我回答到:“谢老,您别这样说,您已经给了我们很大很多的帮助。您的关心就是对我们的爱护、支持和帮助。我们大家都感谢您。”
谢老的语气中显出一丝欣慰的平静:“我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告诉谢老,我已经积攒了一些新的资料,准备给他送去。谢老听后稍微停顿之后,稍显无奈地回答说:“好吧,你来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谢老通电话。我记不得是谢老打给我,还是我打给谢老的了。我吃惊,是因为在我和谢老的接触中,他总是谦和、安静、关心他人、坚持原则,从未说过消极的话。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上,谢老从未表示过犹豫、动摇。
事后回想起来,这次通话是谢老向我的生前绝别,而我不谙世事,竟粗心到没有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曾有耳闻,谢老患病严重。但我见谢老时,他从未提及自己病的严重,只说,人年纪大了,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要出毛病。所以我只以为听说的事是以讹传讹。如果当时我能多想一些,我会立即去看谢老的。
春节后,我约好康健律师再打电话给谢老时,没有人接,连保姆也没接电话。再打时,保姆来接电话说,谢老已经住院。我和康健律师准备去医院探视时,SARS来了,人与人隔离了,病房探视成为不可能。5月的一天,谢老的女儿谢英医生来电话告诉我谢老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我呆若木鸡。虽然不能去医院探视,但我心里总等着谢老一朝出院,我就可以去看望他。想不到与谢老最后的通电话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懊悔。每当我走出车公庄地铁站,总要抬头望一望道路对面谢老所住过的那栋楼房,心头怅然不已。“今日我来君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谢老是赤诚之人。他出于赤诚,于国难时期,寒窗学法报国;出于赤诚,做为战胜国代表接收台湾法院;出于赤诚,以法律工作者的凛然正气仗义直言,直指时弊;出于赤诚,虽历经患难,法制建国矢志不移;出于赤诚,暮年慷慨挥泪,参与民间对日战争索赔工作。他曾说过:法制兴废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纵观历史,有法制的国家统治没有法制的国家,有法不依的国家国际地位低下,让人瞧不起。
我与谢老交往时间不长,却感佩其赤诚无私。现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工作虽多阻碍也颇多进展。愿此跨世纪的国际大诉讼早日完满结局,以酬谢老夙志。
别离几近周年,记此短文以缅怀谢老。
(2004年3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
240331
原作者:刘湧
我第一次读谢老关于民间对日战争索赔的文章是一九九九年夏天。那时我刚从日本学习回国,在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语言上的一些便利,有幸协助康健律师在劳工调查中做一些翻译工作。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是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这一跨世纪的国际大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国内始于1995年。康健律师自1996年起就担起“慰安妇”案和“劳工案”的重任,与日本律师以及国际友人一同不懈地努力工作着。
我所谈到的谢老的文章,是谢老与其他六名中国著名法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中国公民李秀梅等诉日本国损害赔偿案和中国公民刘连仁诉日本国损害赔偿案的法律适用意见》。李秀梅案属于“慰安妇”,而刘连仁案属于“劳工案”。该文章发稿于1997年12月28日,是国内较早的关于民间对日索赔法律实务的专家意见。该文就中国公民对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诸如法律适用、管辖、消灭时效、精神损害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于法理的主权第一的法律意见。正是由于这篇文章在法律实务问题上明确主张司法主权,因此,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应处于标志性文献的地位。在现实中,该文章大大地鼓舞了民间对日索赔的仁人志士的斗志,包括日本律师在内,同时也给日本法官以震动。
以上的认识也是我后来才渐渐形成的。当时我读这篇文章时,对其背景情况知之甚少,只是觉得此文不同凡响,份量沉重。
我第一次见到谢老是2000年10月10日,在全国律协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法院审理强制劳工对日索赔诉讼问题专家论证会”上。从会议名称上可以看出会议的重要。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先生亲自主持了论证会。论证会的议题使人联想到七名法学大家的联名文章。可以说,如果没有前面的文章,也不会有这日的论证会。那时,七名法学大家之首的谢老就坐在我的面前。一位谦和安静矮个老人,一身熨烫平整的蓝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时留下的印象且至今没有变。不错,谢老是一位大家,但他没有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作派。也许是谢老一生真诚的缘故吧,他总是以真情实意说话、做事与待人。有谁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呢?
高会长因为谢老亲自出席论证会非常高兴。那天他是亲自到谢老家里将谢老接到协会里来的。他向与会者介绍谢老且称颂不已。高会长说,谢老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且硕果累累,许多人都以自称是谢老的学生为荣。
在论证会上,首先由案件承办律师介绍了民间对日战争索赔工作在日本和在美国的进展情况,以及中国原劳工将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原五家侵权企业的计划。谢老听完介绍后,谦和安静的老人变得激动起来。他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给中国公民个人也造成极大的损害。被侵害人对加害者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理所当然。中国政府是放弃了国家的请求权,但并没有放弃民间个人的请求权。没有谁有权力放弃中国公民个人的请求权。民间对日索赔工作早就应该做了。中国法院受理本国公民的起诉天经地义。这个工作意义重大,但会很艰难,需要有人勇于承担工作。我感谢实际奉献的律师,全国人民也会感谢你们的。谢老言词激越,发自肺腑以至热泪满面,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会后,谢老把我叫到他身边,仔细地问了一些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他认真地听了我的回答后,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同时表示他自己也会与我们共同努力的。谢老将自己的住址与电话留给我,说有事情随时可以和他联系。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家幸运地和谢老的家只有一条二环路相隔,我们是邻居。
谢老出席论证会,使所有出席者受到鼓舞,论证会开得热烈务实。论证会后的两个月后,五名曾被抓当劳工的中国公民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五家日本企业为被告提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经常到谢老家拜访谈论对日索赔的问题,也常把一些最新动态、会议文件送给谢老。每次我去拜访前都要先给谢老打个电话联系。只要谢老在,他都会让我去,从不推辞。我每次去拜访时,谢老总是亲切地到门口迎接,走时一直送到门口。我向谢老介绍情况时,谢老总是认真地倾听,然后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为了推动民间对日索赔工作,谢老竭尽了全力。例如:为了早日在中国法院提起对日本企业的索赔诉讼,谢老亲自给他在某单位的学生打电话,又亲笔写了推荐信让我去找该人联系。又如2002年的一天,谢老对我说,某老将过生日,到时我去找他商量如何推动这项工作。他的学生多,又都分布在各领域部门,他说话比我的影响大。那时谢老的身体较弱,已不大出门了。
2002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律协正式成立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小组聘请了两位顾问,一位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文迟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谢怀栻先生。谢老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该次成立大会,顾问的聘书是会后由高会长亲自送去的。虽然如此,谢老作为顾问仍然是尽职尽责,这是指导小组成员皆承认的事实。
2002年4月26日中国15名原告在日本福冈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与三井矿山的一审判决下来了,中国劳工对三井矿山胜诉。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难得的胜诉判决。日本的舆论界沸腾了,中国媒体也做了罕见的现场报导。我有幸与康健律师和两位原告老大爷亲历了历史的这一幕。回到国内的当天,我妻子告诉我,谢先生昨天和今天都打来电话,说你在日本胜诉了,祝贺你们。还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赶紧给谢老打电话。谢老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他高兴地说:“刘律师,你们辛苦了。中国劳工胜诉了,我从电视中看到了。太好了!”我对谢老说:“康健律师和我约好明天去看您,同时送去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要旨。”谢老高兴地说:“我等着你们。”第二天,我和康健律师去拜访谢老。谢老高兴地接待我们,认真地听我们介绍福冈判决的前后情况,并提出一些问题。谢老很兴奋,他说:“要动员学者多写文章谈论对日民间索赔,也要努力推动在中国法院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工作。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主战场应当在中国。”
2003年是多事之年,被称为“六亲不认”症的SARS瘟君席卷全国。这一年我们失去了谢老。
200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我和谢老通电话,准备将一些资料送给他。电话另一边传来的谢老的话令我非常吃惊,令我至今难忘,而且令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谢老的声音显得有些凄凉:“刘律师啊,我可能帮助不了你们啦。你们要多保重。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了。”
惊愕之余,我回答到:“谢老,您别这样说,您已经给了我们很大很多的帮助。您的关心就是对我们的爱护、支持和帮助。我们大家都感谢您。”
谢老的语气中显出一丝欣慰的平静:“我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告诉谢老,我已经积攒了一些新的资料,准备给他送去。谢老听后稍微停顿之后,稍显无奈地回答说:“好吧,你来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谢老通电话。我记不得是谢老打给我,还是我打给谢老的了。我吃惊,是因为在我和谢老的接触中,他总是谦和、安静、关心他人、坚持原则,从未说过消极的话。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上,谢老从未表示过犹豫、动摇。
事后回想起来,这次通话是谢老向我的生前绝别,而我不谙世事,竟粗心到没有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曾有耳闻,谢老患病严重。但我见谢老时,他从未提及自己病的严重,只说,人年纪大了,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要出毛病。所以我只以为听说的事是以讹传讹。如果当时我能多想一些,我会立即去看谢老的。
春节后,我约好康健律师再打电话给谢老时,没有人接,连保姆也没接电话。再打时,保姆来接电话说,谢老已经住院。我和康健律师准备去医院探视时,SARS来了,人与人隔离了,病房探视成为不可能。5月的一天,谢老的女儿谢英医生来电话告诉我谢老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我呆若木鸡。虽然不能去医院探视,但我心里总等着谢老一朝出院,我就可以去看望他。想不到与谢老最后的通电话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懊悔。每当我走出车公庄地铁站,总要抬头望一望道路对面谢老所住过的那栋楼房,心头怅然不已。“今日我来君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谢老是赤诚之人。他出于赤诚,于国难时期,寒窗学法报国;出于赤诚,做为战胜国代表接收台湾法院;出于赤诚,以法律工作者的凛然正气仗义直言,直指时弊;出于赤诚,虽历经患难,法制建国矢志不移;出于赤诚,暮年慷慨挥泪,参与民间对日战争索赔工作。他曾说过:法制兴废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纵观历史,有法制的国家统治没有法制的国家,有法不依的国家国际地位低下,让人瞧不起。
我与谢老交往时间不长,却感佩其赤诚无私。现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工作虽多阻碍也颇多进展。愿此跨世纪的国际大诉讼早日完满结局,以酬谢老夙志。
别离几近周年,记此短文以缅怀谢老。
(2004年3月)
出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