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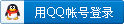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立法瑕疵
——兼谈对演员黄海波收容教育的选择性执法之嫌
法道难易
演员黄海波嫖娼案发,使得以往不大为人所知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而以行政法规形式表现的法律文件进入公众视野。
且不论世界范围内对授权立法现象的纷争与质疑,也不谈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我国是否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上位法律存在抵触和冲突,本文单就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中先后二次出现的“可以”一词的使用,略抒拙见。
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规定:
“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卖淫、嫖娼人员,可以不予收容教育: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传染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一周岁以内婴儿的;
(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
众所周知,按照法学理论,“可以”属于授权性规范的措词。“可以”不是“应当”,更不是“必须”;可以这样,就意味着可以不这样。所以,对卖淫、嫖娼人员可以收容教育,就等于也可以不收容教育。什么情况下可以收容教育,什么情况下也可以不收容教育?没有相应的细化规定。这就为相关执法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许正因为这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中上海高院的数名法官在被拘留10天后并没有跟着予以收容教育。
这合法吗?收容与否的取舍之间,既然皆无不可,自难谓其与法不符,故当属合法范畴。可这公平吗?显然很不公平。于是,对演员黄海波的收容教育,也就不能不被诟病为有选择性执法之嫌。笔者没有理由随便猜测在对上海高院那数名法官未予收容教育而对演员黄海波则实施收容教育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执法人员的人为因素,却不能不理直气壮地指出: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立法瑕疵,至少应该尽快加以修订完善。
也许有人会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其中也使用了“可以”一词。或者说,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中的“可以”一词,正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相关条款中沿用而来的。如此分析似乎可以让人从一定侧面看到“可以”一词在相关法条中使用的因由,却丝毫不能掩盖这种机械照搬的错误之所在。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相关条款中使用“可以”一词,旨在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对卖淫嫖娼人员实施收容教育的办法。而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相关条款中使用“可以”一词,其效果就变成了执法实践中的一种非必须性指令,很容易导致与法治原则格格不入的选择性执法现象。
所以,即使没有任何法律以外的不正当考虑,对演员黄海波的收容教育,恐怕难以轻松洗脱其选择性执法的有失公允之嫌。
其实,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立法瑕疵还表现在,对其第七条第二款所列四种特殊对象,既然是“可以”不予收容教育,是否表示也“可以”收容教育?若果真如此,岂不贻笑大方?!
总之,无论如何,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
240331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立法瑕疵
——兼谈对演员黄海波收容教育的选择性执法之嫌
法道难易
演员黄海波嫖娼案发,使得以往不大为人所知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而以行政法规形式表现的法律文件进入公众视野。
且不论世界范围内对授权立法现象的纷争与质疑,也不谈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我国是否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上位法律存在抵触和冲突,本文单就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中先后二次出现的“可以”一词的使用,略抒拙见。
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规定:
“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卖淫、嫖娼人员,可以不予收容教育: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传染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一周岁以内婴儿的;
(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
众所周知,按照法学理论,“可以”属于授权性规范的措词。“可以”不是“应当”,更不是“必须”;可以这样,就意味着可以不这样。所以,对卖淫、嫖娼人员可以收容教育,就等于也可以不收容教育。什么情况下可以收容教育,什么情况下也可以不收容教育?没有相应的细化规定。这就为相关执法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许正因为这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中上海高院的数名法官在被拘留10天后并没有跟着予以收容教育。
这合法吗?收容与否的取舍之间,既然皆无不可,自难谓其与法不符,故当属合法范畴。可这公平吗?显然很不公平。于是,对演员黄海波的收容教育,也就不能不被诟病为有选择性执法之嫌。笔者没有理由随便猜测在对上海高院那数名法官未予收容教育而对演员黄海波则实施收容教育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执法人员的人为因素,却不能不理直气壮地指出: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立法瑕疵,至少应该尽快加以修订完善。
也许有人会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其中也使用了“可以”一词。或者说,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中的“可以”一词,正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相关条款中沿用而来的。如此分析似乎可以让人从一定侧面看到“可以”一词在相关法条中使用的因由,却丝毫不能掩盖这种机械照搬的错误之所在。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相关条款中使用“可以”一词,旨在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对卖淫嫖娼人员实施收容教育的办法。而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相关条款中使用“可以”一词,其效果就变成了执法实践中的一种非必须性指令,很容易导致与法治原则格格不入的选择性执法现象。
所以,即使没有任何法律以外的不正当考虑,对演员黄海波的收容教育,恐怕难以轻松洗脱其选择性执法的有失公允之嫌。
其实,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立法瑕疵还表现在,对其第七条第二款所列四种特殊对象,既然是“可以”不予收容教育,是否表示也“可以”收容教育?若果真如此,岂不贻笑大方?!
总之,无论如何,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