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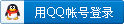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许少波. 华侨大学 教授
一、问题提出
2012年最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以此为标志,曾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过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程序和制度已正式入法。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所规定的“先行调解”,有学者基于《民事诉讼法》法律文本的制度安排和条款逻辑,将其解读为“立案前的调解”。{1}{2}{3}有学者将其模糊地界定为“审前调解”。也有学者认为先行调解中的“调解”是存在歧义的,建议立法者尽快作出解释,区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两种不同的情形。{4}有些研究者将其解释为法院立案前的调解和法院立案后不久的调解。{5}203-204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不能局限于对该条款乃至《民事诉讼法》文本的孤立考察,而应当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的广袤时空中对“先行调解”作整体性的把握。
基于以上认识,先行调解主要应当在三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二是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三是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调解。
二、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
先行调解,无论是作为一个用语,还是作为一个原则,或者是一种程序制度,如果从历史的向度来考察,首先都是立足于诉讼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的。因此,就先行调解的含义来说,首先应当是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为了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也为了宣传自己的先进思想理念以教育和团结最广大的劳苦大众,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根据现代法的精神,制定颁行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必需的新法规,如土地法、婚姻法等。然而,这些新法规与当时的法律文化观念和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是极其不相适应的,这就造成了执行中“两难”局面:一方面共产党决不能放弃自己有关土地、婚姻等方面的具有宣誓性、旗帜性和先进性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新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又不能不迁就当时当地的法律文化和风俗习惯,以稳定根据地的权力基础和保证农民红军的战斗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以实体与程序要求高度弹性和“双重软化”的诉讼调解就自然成为破解该“两难”局面的利器,诉讼调解成为法院首选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十世纪50年代,“先行调解”用语正式诞生。1950年7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始终重视调解,始终把调解工作看作自己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和团结群众而区别于反动审判机关的最重要标志;“过去和现在各地人民法院之所以重视调解工作,主要地是由于经过调解而解息纠纷,不但可以减少诉讼人的时间和人力物力;不但可以减轻人民法院的一部分审判工作;而且经过调解比经过审判解决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更易于消除成见和促进团结”。{6}442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于1950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第30条第2款规定:“起诉的民事或轻微的刑事案件,法院亦应视具体情况,先行调解。调解如不成立,应即进行审判。但调解非诉讼必经程序”。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先行调解”。
二十世纪60至80年代,先行调解被推向极致。60年代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工具的人民法院,其根本任务一方面是实行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民事案件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即“非敌对性”的矛盾案件,要求最好用说服、教育、批评等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调解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196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确定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针。随后,在《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63年8月颁行)中又规定:“调解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也是处理婚姻案件的必经程序。凡能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的方式”。其实,实务部门在执行该意见时,调解已经被扩大适用为处理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各地法院在总结经验时普遍认为:“处理民事案件,自始至终应体现‘调解为主’的精神。凡是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也要先经过调解”。{6}3491 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中指出:“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也要先经过调解”。至此,先行调解已被推向极致。
200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了6类特定类型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和“全程调解”的概念,要求“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求将“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把调解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首选结案方式和基本工作方法”。
通过考察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历史与现实,可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先行调解”,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意指的就是诉讼调解。
第二,从产生背景和存在理由上看,先行调解始终是与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易言之,先行调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成党和国家政治使命的手段和工具。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为了宣传、贯彻党的先进思想理念和组织、动员最广大的革命力量推翻反动统治,建国初期是为了建立新型的密切联系和团结群众的司法,20世纪60、 70年代是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下则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撕开政治的面纱,调解本真的司法功能和作用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主要是“经过调解而解息纠纷,不但可以减少诉讼人的时间和人力物力;不但可以减轻人民法院的一部分审判工作;而且经过调解比经过审判解决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更易于消除成见和促进团结”。
第四,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先行调解只是概念性、原则性的,后来则具体化为在当事人起诉后至法院开庭审理前,针对特定类型案件的程序制度。
第五,这是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先行调解始终是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法律政策交织在一起的,但先行调解与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最近一段时期,有不少学者将“先行调解”与“调解优先”等同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笔者认为,“先行调解”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调解优先”在涵义上虽有交叉,但却有重大区别,甚至可以说有本质的不同。其一是,先行调解是一种程序性安排,“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到目前为止,相关法律法规直接使用“先行调解”一语的共有三次,除了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该规定不纯粹属于诉讼调解的范畴,后文有具体议论),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第30条第2款在规定“视具体情况”进行“先行调解”的同时,其但书部分还指出:“调解非诉讼必经程序”;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更是直接针对六类特殊类型的案件规定先行调解。很显然,所谓的“先行调解”,只是相对于判决就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视具体情况”所作的程序性安排,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优劣的判断。在程序安排的背后,即使确实含有价值优劣的判断,但价值判断本身是与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捆绑在一起的,离开特定类型的案件,判断将无从谈起。同时,就“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而言,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指出:“调解是高质量审判,调解是高效益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优先性判断”,是“公开承认调解作为一种优质的纠纷解决和结案方式,在实现‘案结事了’这一目标方面,调解的功能和效果事实上优于判决”。{7}可见,“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即调解的地位要比判决高。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既然调解“优先”,自然要“先行”调解。同时,尽管我国的立法、司法和主流学理均认同调解权属于审判权的范畴,并反复表明“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但笔者并不认为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正宗方式,诉讼调解充其量也只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变形。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调解不成的案件可以判决”,而不是,“判决不成的案件可以调解”。可见,二者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在程序适用和效力上,判决的最终性是不可动摇的。这也在另一层意义上为“先行调解首先是一种程序安排”的论断作一个有力的注脚。
其二是,先行调解的法理根据是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与案件类型相适应,“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司法的政治化及对解纷效果的经验预测。根据诉讼原理,解决纠纷的机制必须与案件类型相适应。不同的案件类型,其个性特征必不相同。而个性特征的差别,在程序法上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必然不同。为了追求不同案件类型纠纷解决的具体妥当性,就必须斟酌不同案件类型的个性特征和特殊需求,以及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供给情况,从而探究特定案件类型适用程序的法理。{8}76因此,单就某种解纷方式而言,没有绝对的“调解优于判决”,也没有绝对的“判决优于调解”,而只有在适用于某种案件类型时何者为优。作为一种解纷机制,调解与判决一经形成,其功能和价值就已经内含于程序机制之中,成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预置。而评判解纷机制价值优劣的标准不应该是静止不动的,不应该由其自身说了算,而应该由使用它们的案件类型作出决定。其中的奥妙正如:是皮鞋好,还是布鞋好,由脚决定;是海鲜好吃,还是牛羊肉好吃,由顾客说了算。因此,先行调解是案件类型的不同需要决定的,而“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是基于一种主观判断。
其三是,先行调解有时间段的限制,“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则可以全程优先,反复优先。所谓的“先行调解”,是“调解程序”相对于“判决程序”的“先行”,也即必须在审判程序开始前进行“调解”。如果已经正式开庭审理开始进行判决,调解就无法“先行”。因此,先行调解只能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而“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是就整个纠纷解决的过程而言的,只要纠纷还没有最终消除,就应当“主要”、“着重”和“优先”适用调解,反复适用调解。否则,调解的“主要”、“着重”和“优先”地位就难以体现。
总之,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由某些特殊类型案件决定的,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至正式开庭审理前首先适用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一种程序和制度安排。
三、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
在逻辑上,非诉讼调解是指除诉讼调解以外的调解。在现实形态上,非诉讼调解主要是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在实质性上,非诉讼调解是指在诉讼程序之外,不是由现职法官作为主持人且调解协议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基于非诉讼调解的内在规定性,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指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在当事人尚未诉请法院司法保护之前,国家鼓励尽可能通过非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程序制度。
从表面上看,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从未直接作出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虽然我国语境的“先行调解”产生于诉讼调解,但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确实存在的。在原理上,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由此形成的纠纷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纠纷当事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心理结构是有差别的,个人偏好和价值观也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也总是处在不断变迁和演进的过程之中。因此,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可以满足所有纠纷类型、所有纠纷当事人、所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纠纷解决方式,任何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形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只能是幻想,司法神话的破灭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适用于不同纠纷类型、不同纠纷当事人和不同社会需求的纠纷解决方式必然是多元化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可以独立适用(使用)但又不是孤立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联结在一起必然是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非诉讼调解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纠纷解决的第三人并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院,解决纠纷的标准也不必然反映国家主流的价值观,解决纠纷的程序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此,纠纷解决的结果—非诉讼调解的效力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沐具有最终性。换言之,非诉讼调解在不少情况下,客观上已经成为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也即诉讼程序的“先行”解纷方式。
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与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相比,二者虽然同属于先行调解,但却有本质的不同。第一,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之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的案件压力,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快速地、经济地解决纠纷的权利;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地、一次性地消除纠纷,也就是所谓的“案结事了”。第二,前者属于非诉讼性质的调解,后者属于诉讼性质的调解,二者刚好相反。自然地,这两种性质的调解在所适用的原则、基准法、程序规则和法律效力上均不可能相同。第三,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性”主要是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的,既包括判决也包括诉讼调解。并且,在法律效力上,非诉讼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程序对纠纷的解决具有终局性的“既判力”。二者结合在一起则构成了“梯次型”的解纷结构;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性”只能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诉讼调解与其相对的判决均具有终局性解决纠纷的效力,二者结合在一起只能是一个平面的构造。第四,反映在法律上,前者至多是一种法律政策,主要是鼓励和提倡适用(使用)非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后者则早已演变为法律的直接规定,甚至具体化为开庭审理和判决的前置程序,适用的强制性自不必说。第五,前者在时间段上限定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如果当事人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不管法院是否受理,已不属于这里所说的“非诉讼调解”的范畴;而后者的时间段则限定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开庭审理之前。
四、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
从时间段上来说,本文将法院受理案件后到开庭审理前先进行的调解称为“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第一种意义),把纠纷产生后至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前先进行的调解界定为“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第二种意义),但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先进行的调解又该如何称呼呢?在这里,笔者将其称为“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第三种意义)。并且认为,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此种情况。要使这一断言令人信服,就必须正面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界定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二是为什么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即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对于第一个问题,李浩教授的相关议论已经非常有力,{1}{2}本文没有添足的必要。第二个问题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论断,自然需要“重笔”交待。
首先,在政策指引上,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是我国积极构建、推行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物。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提出,法院可以邀请、委托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机构和个人进行调解,并规定了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为推行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迈出了第一步。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思路。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站在律立和完善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要求研究和探索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的对接机制。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具体提出,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相结合的“大调解”工具。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则将“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写进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14条明确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至此,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司法政策已基本形成。
司法政策的目的和导向很清楚,在我国社会快速变革和转型期,为有效应对不断增多的矛盾纠纷,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绝对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充分发挥司法结构解决纠纷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还要尽最大可能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这就需要构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覆盖全社会的“调解之网”。这张网是由三张子网组成的:一是诉讼调解之网;二是非诉讼调解之网;三是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之网。既要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之网和非诉讼调解之网各自独立的作用,又要高度重视将诉讼调解之网与非诉讼调解之网链接在一起所可能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正是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互交错、链接的产品。
其次,在实践运作上,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样态,但均可定位在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连接线上。在司法政策的推动下,尤其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各地方法院积极响应,创造了样态繁多、各具特色的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模式。如北京朝阳区模式、上海长宁区模式、南京钟楼区模式、厦门思明区模式、广州市模式、杭州市模式、海南区法院模式、及全国各地的“大调解”模式等。从具体的程序运作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在当事人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立案庭的法官直接进行调解,调解成功所达成的协议即与诉讼调解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功的则直接立案,进入诉讼程序。二是在法院接到当事人的起诉后,经过审查,如果认为案件有调解的可能,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就将案件委托给法院以外的机构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一般以法院以外调解机构的名义出具调解书。当然,如果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审查确认,也可以出具法院的调解书;调解不成功的,则将案件交回法院走诉讼程序。第三种情况是,法院接到当事人起诉后,如有调解可能,则由设立在法院内的人民调解窗口或联合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有的法院直接确认其具有诉讼调解的效力,有的法院则不予直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诉讼程序。
如果从“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这一先行调解的旨趣来评判的话,第一种情况仍然是由法院包揽调解的全部,只是诉讼调解的扩大化。第二种情形也做到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比较松散的,对当事人、法院及纠纷解决来说,其便利性、快捷性和经济性值得怀疑。相对来说,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应当是第三种情形。该种情形已经超越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外在形式结合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了构成要素和理念融合、链接的高级阶段。非诉讼调解机构直接入驻法院,法院对调解的主持者直接进行培训,法律的规则、原则和理念直接作用于非诉讼调解因素,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在这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在程序上更是环环相扣、“亲密无间”。
最后,域外法院附设ADR具有双重性。如果说作为诉讼调解和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均源自国内,是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的程序制度,那么,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理念和行动,则生成和发展于域外的法院附设ADR。作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ADR本与在法院进行的诉讼无关,但20世纪70年代后,英美法系国家却在法院内部设立了ADR,在诉讼程序中“嵌入”了具有非讼性的ADR纠纷解决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司法ADR或法院附设ADR。故司法ADR具有司法和非司法双重属性。与传统诉讼程序相比,司法ADR在程序、主持者和程序效果上具有非司法性质;与法院外ADR相比,司法ADR在法院对程序的参与、管理和渗透上,以及与法院诉讼程序的衔接上又具有一定的司法性质。{9}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与域外的法院附设ADR大致相当,具有司法和非司法、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双重的属性。
五、结语
基于以上讨论,先行调解主要应当在三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二是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三是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先行调解,无论是作为一个用语,还是作为一个原则,或者是一种程序制度,如果从历史的向度来考察,首先都是立足于诉讼调解的,相对于判决而言的。因此,就先行调解的含义来说,首先应当是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诉讼调解是指法院受理案件后至开庭审理前所进行的调解;非诉讼调解是指除诉讼调解以外的调解,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不是由现职法官作为主持人且调解协议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则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调解。
注释:
参见李浩:《论“先行调解”的性质》,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参见张艳丽:《如何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对新民事诉讼法有关“审前调解”的理解与适用》,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参见吴英姿:《“调解优先”:改革范式与法律解读—以0市法院改革为样本》,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有学者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叙明。1931年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然而中国共产党几乎立即就从这种激进的立场撤退,原因非常实际:党希望保护红军中的农民战士对妻子的主张权。对农民而言,在农村结婚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按照结婚的通常花费和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一生只负担得起一次结婚。允许妇女任意与丈夫离婚,无论对军人还是对他们的家庭都是很严重的打击。因此,对于有争议的婚姻,可行的办法显然是既不全部拒绝也不一概准许。前者意味着背离共产党对结婚和离婚自由的承诺,后者又肯定会遭到乡村社会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规定有争议的离婚必须先行调解,就能在两条原则的张力之间做到有效的折中。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92页。
在当时的民事审判工作中,甚至一度提出和推广过“调解为主”的方针。参见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非诉讼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由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的调解组织按照公平中立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
国内学理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兴起的诉前调解是在借鉴域外法院附设ADR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从调解的种类、样态和主持者来说,尤其是法院对调解的作用上,我国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是不能与国外的法院附设ADR划等号的。
参考文献:
{1}李浩.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与认识[N].人民法院报,2012-10-17(7).
{2}李浩.非诉讼权利实现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对先行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督促程序的解读[N].检察日报,2012-9-12(3).
{3}徐卉.先行调解的规范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2012-10-17(7).
{4}宋朝武.对民诉法修正案中调解制度的若干理解[J]中国审判,2012(6).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版):203-204.
{6}中国社科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7}范愉.调解的正当性与发展趋势[N].人民法院报,2009-10-14(5).
{8}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6.
{9}章武生.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新发展[J].公民与法,2009(5). 出处:《海峡法学》2013年第1期 |
240331
许少波. 华侨大学 教授
一、问题提出
2012年最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以此为标志,曾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过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程序和制度已正式入法。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所规定的“先行调解”,有学者基于《民事诉讼法》法律文本的制度安排和条款逻辑,将其解读为“立案前的调解”。{1}{2}{3}有学者将其模糊地界定为“审前调解”。也有学者认为先行调解中的“调解”是存在歧义的,建议立法者尽快作出解释,区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两种不同的情形。{4}有些研究者将其解释为法院立案前的调解和法院立案后不久的调解。{5}203-204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不能局限于对该条款乃至《民事诉讼法》文本的孤立考察,而应当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的广袤时空中对“先行调解”作整体性的把握。
基于以上认识,先行调解主要应当在三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二是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三是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调解。
二、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
先行调解,无论是作为一个用语,还是作为一个原则,或者是一种程序制度,如果从历史的向度来考察,首先都是立足于诉讼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的。因此,就先行调解的含义来说,首先应当是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为了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也为了宣传自己的先进思想理念以教育和团结最广大的劳苦大众,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根据现代法的精神,制定颁行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必需的新法规,如土地法、婚姻法等。然而,这些新法规与当时的法律文化观念和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是极其不相适应的,这就造成了执行中“两难”局面:一方面共产党决不能放弃自己有关土地、婚姻等方面的具有宣誓性、旗帜性和先进性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新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又不能不迁就当时当地的法律文化和风俗习惯,以稳定根据地的权力基础和保证农民红军的战斗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以实体与程序要求高度弹性和“双重软化”的诉讼调解就自然成为破解该“两难”局面的利器,诉讼调解成为法院首选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十世纪50年代,“先行调解”用语正式诞生。1950年7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始终重视调解,始终把调解工作看作自己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和团结群众而区别于反动审判机关的最重要标志;“过去和现在各地人民法院之所以重视调解工作,主要地是由于经过调解而解息纠纷,不但可以减少诉讼人的时间和人力物力;不但可以减轻人民法院的一部分审判工作;而且经过调解比经过审判解决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更易于消除成见和促进团结”。{6}442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于1950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第30条第2款规定:“起诉的民事或轻微的刑事案件,法院亦应视具体情况,先行调解。调解如不成立,应即进行审判。但调解非诉讼必经程序”。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先行调解”。
二十世纪60至80年代,先行调解被推向极致。60年代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工具的人民法院,其根本任务一方面是实行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民事案件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即“非敌对性”的矛盾案件,要求最好用说服、教育、批评等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调解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196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确定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针。随后,在《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63年8月颁行)中又规定:“调解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也是处理婚姻案件的必经程序。凡能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的方式”。其实,实务部门在执行该意见时,调解已经被扩大适用为处理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各地法院在总结经验时普遍认为:“处理民事案件,自始至终应体现‘调解为主’的精神。凡是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也要先经过调解”。{6}3491 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中指出:“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也要先经过调解”。至此,先行调解已被推向极致。
200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了6类特定类型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和“全程调解”的概念,要求“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求将“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把调解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首选结案方式和基本工作方法”。
通过考察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历史与现实,可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先行调解”,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意指的就是诉讼调解。
第二,从产生背景和存在理由上看,先行调解始终是与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易言之,先行调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成党和国家政治使命的手段和工具。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为了宣传、贯彻党的先进思想理念和组织、动员最广大的革命力量推翻反动统治,建国初期是为了建立新型的密切联系和团结群众的司法,20世纪60、 70年代是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下则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撕开政治的面纱,调解本真的司法功能和作用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主要是“经过调解而解息纠纷,不但可以减少诉讼人的时间和人力物力;不但可以减轻人民法院的一部分审判工作;而且经过调解比经过审判解决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更易于消除成见和促进团结”。
第四,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先行调解只是概念性、原则性的,后来则具体化为在当事人起诉后至法院开庭审理前,针对特定类型案件的程序制度。
第五,这是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先行调解始终是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法律政策交织在一起的,但先行调解与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最近一段时期,有不少学者将“先行调解”与“调解优先”等同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笔者认为,“先行调解”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调解优先”在涵义上虽有交叉,但却有重大区别,甚至可以说有本质的不同。其一是,先行调解是一种程序性安排,“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到目前为止,相关法律法规直接使用“先行调解”一语的共有三次,除了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该规定不纯粹属于诉讼调解的范畴,后文有具体议论),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第30条第2款在规定“视具体情况”进行“先行调解”的同时,其但书部分还指出:“调解非诉讼必经程序”;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更是直接针对六类特殊类型的案件规定先行调解。很显然,所谓的“先行调解”,只是相对于判决就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视具体情况”所作的程序性安排,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优劣的判断。在程序安排的背后,即使确实含有价值优劣的判断,但价值判断本身是与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捆绑在一起的,离开特定类型的案件,判断将无从谈起。同时,就“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而言,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指出:“调解是高质量审判,调解是高效益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优先性判断”,是“公开承认调解作为一种优质的纠纷解决和结案方式,在实现‘案结事了’这一目标方面,调解的功能和效果事实上优于判决”。{7}可见,“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即调解的地位要比判决高。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既然调解“优先”,自然要“先行”调解。同时,尽管我国的立法、司法和主流学理均认同调解权属于审判权的范畴,并反复表明“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但笔者并不认为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正宗方式,诉讼调解充其量也只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变形。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调解不成的案件可以判决”,而不是,“判决不成的案件可以调解”。可见,二者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在程序适用和效力上,判决的最终性是不可动摇的。这也在另一层意义上为“先行调解首先是一种程序安排”的论断作一个有力的注脚。
其二是,先行调解的法理根据是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与案件类型相适应,“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司法的政治化及对解纷效果的经验预测。根据诉讼原理,解决纠纷的机制必须与案件类型相适应。不同的案件类型,其个性特征必不相同。而个性特征的差别,在程序法上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必然不同。为了追求不同案件类型纠纷解决的具体妥当性,就必须斟酌不同案件类型的个性特征和特殊需求,以及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供给情况,从而探究特定案件类型适用程序的法理。{8}76因此,单就某种解纷方式而言,没有绝对的“调解优于判决”,也没有绝对的“判决优于调解”,而只有在适用于某种案件类型时何者为优。作为一种解纷机制,调解与判决一经形成,其功能和价值就已经内含于程序机制之中,成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预置。而评判解纷机制价值优劣的标准不应该是静止不动的,不应该由其自身说了算,而应该由使用它们的案件类型作出决定。其中的奥妙正如:是皮鞋好,还是布鞋好,由脚决定;是海鲜好吃,还是牛羊肉好吃,由顾客说了算。因此,先行调解是案件类型的不同需要决定的,而“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是基于一种主观判断。
其三是,先行调解有时间段的限制,“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则可以全程优先,反复优先。所谓的“先行调解”,是“调解程序”相对于“判决程序”的“先行”,也即必须在审判程序开始前进行“调解”。如果已经正式开庭审理开始进行判决,调解就无法“先行”。因此,先行调解只能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而“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调解优先,’是就整个纠纷解决的过程而言的,只要纠纷还没有最终消除,就应当“主要”、“着重”和“优先”适用调解,反复适用调解。否则,调解的“主要”、“着重”和“优先”地位就难以体现。
总之,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由某些特殊类型案件决定的,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至正式开庭审理前首先适用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一种程序和制度安排。
三、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
在逻辑上,非诉讼调解是指除诉讼调解以外的调解。在现实形态上,非诉讼调解主要是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在实质性上,非诉讼调解是指在诉讼程序之外,不是由现职法官作为主持人且调解协议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基于非诉讼调解的内在规定性,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指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在当事人尚未诉请法院司法保护之前,国家鼓励尽可能通过非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程序制度。
从表面上看,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从未直接作出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虽然我国语境的“先行调解”产生于诉讼调解,但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是确实存在的。在原理上,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由此形成的纠纷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纠纷当事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心理结构是有差别的,个人偏好和价值观也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也总是处在不断变迁和演进的过程之中。因此,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可以满足所有纠纷类型、所有纠纷当事人、所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纠纷解决方式,任何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形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只能是幻想,司法神话的破灭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适用于不同纠纷类型、不同纠纷当事人和不同社会需求的纠纷解决方式必然是多元化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可以独立适用(使用)但又不是孤立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联结在一起必然是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非诉讼调解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纠纷解决的第三人并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院,解决纠纷的标准也不必然反映国家主流的价值观,解决纠纷的程序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此,纠纷解决的结果—非诉讼调解的效力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沐具有最终性。换言之,非诉讼调解在不少情况下,客观上已经成为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也即诉讼程序的“先行”解纷方式。
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与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相比,二者虽然同属于先行调解,但却有本质的不同。第一,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之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的案件压力,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快速地、经济地解决纠纷的权利;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地、一次性地消除纠纷,也就是所谓的“案结事了”。第二,前者属于非诉讼性质的调解,后者属于诉讼性质的调解,二者刚好相反。自然地,这两种性质的调解在所适用的原则、基准法、程序规则和法律效力上均不可能相同。第三,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性”主要是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的,既包括判决也包括诉讼调解。并且,在法律效力上,非诉讼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程序对纠纷的解决具有终局性的“既判力”。二者结合在一起则构成了“梯次型”的解纷结构;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性”只能是相对于判决而言的,诉讼调解与其相对的判决均具有终局性解决纠纷的效力,二者结合在一起只能是一个平面的构造。第四,反映在法律上,前者至多是一种法律政策,主要是鼓励和提倡适用(使用)非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后者则早已演变为法律的直接规定,甚至具体化为开庭审理和判决的前置程序,适用的强制性自不必说。第五,前者在时间段上限定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如果当事人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不管法院是否受理,已不属于这里所说的“非诉讼调解”的范畴;而后者的时间段则限定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开庭审理之前。
四、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
从时间段上来说,本文将法院受理案件后到开庭审理前先进行的调解称为“作为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第一种意义),把纠纷产生后至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前先进行的调解界定为“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第二种意义),但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先进行的调解又该如何称呼呢?在这里,笔者将其称为“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第三种意义)。并且认为,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此种情况。要使这一断言令人信服,就必须正面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界定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二是为什么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即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对于第一个问题,李浩教授的相关议论已经非常有力,{1}{2}本文没有添足的必要。第二个问题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论断,自然需要“重笔”交待。
首先,在政策指引上,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是我国积极构建、推行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物。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提出,法院可以邀请、委托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机构和个人进行调解,并规定了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为推行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迈出了第一步。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思路。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站在律立和完善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要求研究和探索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的对接机制。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具体提出,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相结合的“大调解”工具。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则将“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写进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14条明确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至此,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司法政策已基本形成。
司法政策的目的和导向很清楚,在我国社会快速变革和转型期,为有效应对不断增多的矛盾纠纷,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绝对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充分发挥司法结构解决纠纷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还要尽最大可能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这就需要构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覆盖全社会的“调解之网”。这张网是由三张子网组成的:一是诉讼调解之网;二是非诉讼调解之网;三是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之网。既要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之网和非诉讼调解之网各自独立的作用,又要高度重视将诉讼调解之网与非诉讼调解之网链接在一起所可能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正是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互交错、链接的产品。
其次,在实践运作上,第三种意义的先行调解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样态,但均可定位在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连接线上。在司法政策的推动下,尤其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各地方法院积极响应,创造了样态繁多、各具特色的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模式。如北京朝阳区模式、上海长宁区模式、南京钟楼区模式、厦门思明区模式、广州市模式、杭州市模式、海南区法院模式、及全国各地的“大调解”模式等。从具体的程序运作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在当事人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立案庭的法官直接进行调解,调解成功所达成的协议即与诉讼调解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功的则直接立案,进入诉讼程序。二是在法院接到当事人的起诉后,经过审查,如果认为案件有调解的可能,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就将案件委托给法院以外的机构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一般以法院以外调解机构的名义出具调解书。当然,如果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审查确认,也可以出具法院的调解书;调解不成功的,则将案件交回法院走诉讼程序。第三种情况是,法院接到当事人起诉后,如有调解可能,则由设立在法院内的人民调解窗口或联合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有的法院直接确认其具有诉讼调解的效力,有的法院则不予直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诉讼程序。
如果从“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这一先行调解的旨趣来评判的话,第一种情况仍然是由法院包揽调解的全部,只是诉讼调解的扩大化。第二种情形也做到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比较松散的,对当事人、法院及纠纷解决来说,其便利性、快捷性和经济性值得怀疑。相对来说,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应当是第三种情形。该种情形已经超越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外在形式结合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了构成要素和理念融合、链接的高级阶段。非诉讼调解机构直接入驻法院,法院对调解的主持者直接进行培训,法律的规则、原则和理念直接作用于非诉讼调解因素,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在这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在程序上更是环环相扣、“亲密无间”。
最后,域外法院附设ADR具有双重性。如果说作为诉讼调解和作为非诉讼调解的先行调解均源自国内,是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的程序制度,那么,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一种理念和行动,则生成和发展于域外的法院附设ADR。作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ADR本与在法院进行的诉讼无关,但20世纪70年代后,英美法系国家却在法院内部设立了ADR,在诉讼程序中“嵌入”了具有非讼性的ADR纠纷解决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司法ADR或法院附设ADR。故司法ADR具有司法和非司法双重属性。与传统诉讼程序相比,司法ADR在程序、主持者和程序效果上具有非司法性质;与法院外ADR相比,司法ADR在法院对程序的参与、管理和渗透上,以及与法院诉讼程序的衔接上又具有一定的司法性质。{9}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与域外的法院附设ADR大致相当,具有司法和非司法、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双重的属性。
五、结语
基于以上讨论,先行调解主要应当在三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二是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三是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先行调解,无论是作为一个用语,还是作为一个原则,或者是一种程序制度,如果从历史的向度来考察,首先都是立足于诉讼调解的,相对于判决而言的。因此,就先行调解的含义来说,首先应当是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诉讼调解是指法院受理案件后至开庭审理前所进行的调解;非诉讼调解是指除诉讼调解以外的调解,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不是由现职法官作为主持人且调解协议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交错的先行调解则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至正式立案受理前所进行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应当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调解。
注释:
参见李浩:《论“先行调解”的性质》,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参见张艳丽:《如何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对新民事诉讼法有关“审前调解”的理解与适用》,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参见吴英姿:《“调解优先”:改革范式与法律解读—以0市法院改革为样本》,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有学者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叙明。1931年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然而中国共产党几乎立即就从这种激进的立场撤退,原因非常实际:党希望保护红军中的农民战士对妻子的主张权。对农民而言,在农村结婚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按照结婚的通常花费和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一生只负担得起一次结婚。允许妇女任意与丈夫离婚,无论对军人还是对他们的家庭都是很严重的打击。因此,对于有争议的婚姻,可行的办法显然是既不全部拒绝也不一概准许。前者意味着背离共产党对结婚和离婚自由的承诺,后者又肯定会遭到乡村社会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规定有争议的离婚必须先行调解,就能在两条原则的张力之间做到有效的折中。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92页。
在当时的民事审判工作中,甚至一度提出和推广过“调解为主”的方针。参见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非诉讼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由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的调解组织按照公平中立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
国内学理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兴起的诉前调解是在借鉴域外法院附设ADR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从调解的种类、样态和主持者来说,尤其是法院对调解的作用上,我国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也即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是不能与国外的法院附设ADR划等号的。
参考文献:
{1}李浩.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与认识[N].人民法院报,2012-10-17(7).
{2}李浩.非诉讼权利实现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对先行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督促程序的解读[N].检察日报,2012-9-12(3).
{3}徐卉.先行调解的规范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2012-10-17(7).
{4}宋朝武.对民诉法修正案中调解制度的若干理解[J]中国审判,2012(6).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版):203-204.
{6}中国社科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7}范愉.调解的正当性与发展趋势[N].人民法院报,2009-10-14(5).
{8}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6.
{9}章武生.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新发展[J].公民与法,2009(5). 出处:《海峡法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