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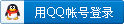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赵旭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一、关于程序性违法
相对于实体性违法,程序性违法是指程序参与主体违反某一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这里的程序参与主体,既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双方、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也包括程序的主持者——法官,还包括其他参与诉讼程序、在诉讼中负有一定义务的主体,如鉴定人员、翻译人员、证人等。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在司法界、理论界及社会公众中的深刻影响,程序性违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至今也没有)。一般而言,程序性违法行为只要没有严重到影响实体判决的公正,该行为即不会受到惩戒。这种情况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程序性违法中尤为严重。理论上,任何违反程序法的行为都应当由该主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将会导致该证据在庭审中被排除,再如合议庭的组成不合法将可能导致案件的发回重审。在立法上,两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都有相关的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对法官的程序性违法,除了列举的三四种违法行为,对其他的违法行为只要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正确判决”即不会被发回重审。逻辑的可笑之处在于,即便是因为程序违法严重到影响了“公正审判”的地步,其导致的结果却是未违法的程序参与人要承担相当程度的不利后果,因为案件被发回重审了,意味着被告人可能被合法地延长羁押、当事人的纠纷被合法地久拖不决、证人要因此耗费更多的时间来出庭,而法院却没有对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导致的诉讼拖延等损失进行赔偿。导致这种情况的制度原因极其深刻,比如侦查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构造中的“侦查本位”、法官的不独立等等。革除这些弊端非一日之功,亦非某一项单纯的规则改革所能完成,更何况某些改革时机未必成熟。[①]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借助某些微观方面的努力来制约这些程序性违法行为。
本文之所以选取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制约为视角来进行考量,是因为:第一,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法官的程序性违法受到忽略的现象更为严重,尤其在民事诉讼中。这个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司法的纠问式诉讼导致公众程序观念的虚无,不晓得有程序性违法;另外,大部分当事人,由于对法律(尤其是程序)的陌生,往往不知道法官是否违法;再者,即便是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来解决,比如法官违反审限的规定导致诉讼拖延的情况,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救济渠道;最后,当事人往往会有这样的观念:法官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法官自己的案子怎么办?所以即便是法官有些许程序性违法,只要不是太“欺负人”就算了。这些便引出本文之所以采此视角原因之第二,作为法律职业者,作为诉讼程序的亲身参与者,律师最知道法官有无程序违法情况,而作为委托人利益的维护者律师也最应当负有制约法官的义务。第三,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及时制约,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司法成本。如果案件由于程序性违法的及时被纠正,而不须等到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等来通过重审或再审来纠正,那么诉讼参与人的因此不利益便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再次使用也可以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事情大部分得过且过,其原因何在?而如果律师愿意制约,途径应当如何呢?此即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先从两个真实的法官程序违法个案谈起。
二、个案的启示
(一)一个典型的法官程序违法个案
2004年11月12日,北京市宣武区法院立案受理了一起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于案情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不大(纠纷标的为价值约20万元的机器设备的搬迁),法院决定采取简易程序审理,独任审判员为该院民庭秘法官。案件于2004年11月29日正式开庭审理,其间11月29日、12月29日、2005年1月5日、1月6日开庭四次,于2005年1月6日庭审结束。然而,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却迟迟得不到本案的判决。原告代理律师多次打电话给本案审判员秘法官询问何时下判决,该法官总是推说太忙,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手头案子积压太多,结不了。”案件拖了三个月之久,仍无消息。在律师的一再追问、要求判决的情况下,该法官说:“本案法定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已过,要改成普通程序审理,何时开庭,另行通知。”于是本案当事人再次陷入了对开庭通知的漫长等待,一个多月后,在律师的多次催问下,2005年4月22日,本案终于再次以普通程序开庭,法庭由审判员秘法官及两名陪审员组成。于是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又走了一遍,终于普通程序庭审完毕,结果该案件再次陷入了对判决的苦苦等待。至2005年8月9日,本案件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诉讼过程后,当事人终于难熬等待的折磨,被迫部分和解,第三人同意原告将设备拉走(因为原告急需设备投入新的合作项目,正是由于案件的久拖不决原告已经丧失了一个合作机会;第三人急需设备占据的厂房进行生产,也是由于案件的久拖不决,第三人多付了几个月的房租)。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秘某的很多表现很发人深思,出于本文的意旨,笔者举出其中两次。一次是在庭审后,该法官曾经很不屑地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说:“人家那么多案子都能调解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另有一次,原告代理律师曾经于2005年5月23日,应该法官的要求向其提交书面材料一份,后来在谈话中提及,该法官抱怨代理人未将情况反映给他,当代理人提到材料已交给他后,秘法官竟然很坦然地说根本没看这个材料。时至2005年11月3日,案件立案近一年了,该案仍然没有得到法院判决。[②]
这个普通的经济案件,反映的问题的确很多,比如法官的素质问题,强制调解的问题等等。但最根本的,笔者认为还是法官的程序性违法的问题。本案的法官的一个很明显的违法之处,在于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案件自立案之日,拖延了五个月之久仍未给出判决,远远超过了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对于此,当事人及代理人没有丝毫办法,因为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关于违反该程序应当如何救济的规定。而本案的秘法官却有办法:超过审限了?好说,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便罢。全然不顾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纠纷的最终、尽快解决的切盼。使得纠纷当事人利益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尊严和公信力。并且,本案法官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的作法,其本身也很难说是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院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70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次日起计算。”可见,即便是案情复杂(最高院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68条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给出了解释,但案情究竟复杂与否仍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从本案看,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无疑。因为本案最初就是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完毕,只需一个判决即可终结的。更何况法官已经给出了案件为何久拖不决的原因:案件积压太多,结不了。)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那也应当是在审理过程中作出决定,更何况即便是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审理期限仍然超过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案件六个月的审理期限。当然,民诉法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有特殊情况吗?难道“案件积压太多,结不了”也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如果有,并且经过了院长批准那有什么拿不到台面上的,还需要以“案件积压”为借口来搪塞代理人的追问呢?
案例中所示法官的行为,明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笔者称之为“典型的程序性违法”。
(二)一个非典型案例
据笔者的了解,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这种违反审限、拖延诉讼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还是有法可循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更多的时候法官的行为根本不违背任何法律。比如,案件中所提到的律师就在北京市大兴区法院遇到过另外一件事情,执行庭某法官通知被执行人和其代理人于2004年某月某日上午9点在法院某谈话室谈话,第二天早上当被执行人和律师风尘仆仆从市里花费了近2个小时按时赶到法院,却找不到法官,打电话一联系,法官出去办事了,法官很坦然地说:“忘记了”,让被执行人和律师回去,“改天再说”。
这个案例,很难明确地说法官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哪一条,哪一款。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法官不按时出庭应当如何处理,笔者姑且在本文中称之为“非典型程序错误”,之所以将之称为“错误”而不是“违法”是因为人家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肯定不正确,法官通知当事人及代理人到庭谈话,却忘记了,便临时取消,该法官不算违法也并不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是当事人忘记了出庭会怎样?是要为此承担不利结果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一百三十条也规定了当事人不出庭的程序后果,原告按撤诉处理,被告缺席判决。同样是程序的参与主体,为什么法官不出庭就没有相应的后果?如果说,当事人不出庭是对法庭的藐视,那法官不按时出庭不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吗?不是更应当受到制裁吗?或许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法官又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凭什么制裁法官。笔者看来,无论哪个国家的程序法律都没有必要对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作出规定,我们也从没见过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官必须按时出庭的”。法官是“游戏”的主持者和裁判者,法官随意的不出庭,纠纷当事人凭什么相信这样随意的法官会作出公正的裁判?法官——这个所谓的精英分子,连“诚实、守信”这个市场经济下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怎么能让当事人尊重其“权威”?
(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法官之所以会如此大胆地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或未规定的程序,原因并不复杂。第一、司法传统所导致的程序虚无;第二、对法官程序违法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法治的最大障碍来自文化传统。(P8)在中国传统司法中,“全能型衙门”的“些小吾曹州县吏”,居于本级政府权力格局的核心,地位至高无上,大堂之上说一不二(P60)。滋贺秀三将这种法官以“父母官”的身份“坐堂问案”的方式称为“父母型诉讼”。(P16)在这种“庭审”中,大老爷说什么便是什么,说什么时候开庭便什么时候开,说什么时候“休庭”便什么时候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的,更无论有法可循了。《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便写贾语村刚补授了应天府便接了人命官司,语村听了原告的陈述大怒,正待发签捕人、拿人拷问之际,葫芦僧出现了,向语村使眼色儿,“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一个眼色,心下“疑怪”,便退堂“休庭”,哪里需要什么法定“诉讼中止”啊什么的。这种司法传统,其影响便会是:其一,法官拿程序不当回事;其二,当事人拿法官程序违法不当回事。法官、当事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程序岂能不虚无?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小民”们不愿挨,又有什么渠道救济呢?只要程序违法不“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错案追究制度”又会追究到哪个法官头上呢?这恰好说明了对法官程序违法的制约无力,陈瑞华教授对此早有深刻的揭示,(P8-69)笔者深表赞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病症,是一项庞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司法体制、全社会的法制观念等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笔者本文不拟探讨这个问题,只希望在当前的体制框架内找到一种微观的方法,暂时缓解病痛,以无奈地等待“大手术”。
三、律师在制约法官程序违法中的作用
(一)律师所应有的作用
笔者在前面提过,相对于“外行”的当事人,律师最了解法官在诉讼中有无程序违法,而同时律师如果能及时对这种程序违法进行制约,那么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司法成本。此外,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也是律师职责的应有之意。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法官还是律师,他们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而所谓职业共同体应当有同一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其中很重要的几点是应当具有“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以及程序优先和形式理性。[③]正是有以这些法律家所应有的独特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职业素养,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和权威、保证司法自治与司法优先,保证法治对人治的阻隔。遵守和维护这些原则,应当是“法律人”最基本的道德和使命。这也许是中国“法律人”遭遇信任危机的最根本所在,正如孙笑侠教授所述:“我国的部分‘法律人’……缺乏相应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失职于对正义的维护并且还进一步亵渎了正义。”(P74)律师在面对法官的程序违法的时候,应当有维护法律职业尊严的使命感,而不应当是保持“明哲保身”的沉默甚或于“进一步亵渎正义”。因为,律师并非以维护委托人职责为其惟一职责,他还应当肩负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使命。
在我国,律师对法官的制约,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制度背景的。尽管中国的“讼师”已有千年的历史,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在中国的出现却晚至鸦片战后,从租界的领事法庭走向“会审公堂”,逐渐介入晚清直至民国的社会生活。清末的司法改革,律师制度进入了“改革派”视野,而这些“有识之士”之所以推崇参照西方设立律师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律师在公堂上的出现可以制约法官(当时称为推事)。当时的邮传部主事陈宗蕃在其1910年的“司法独立之始亟宜预防流弊以重宪政”奏折中就提出:“律师之用,所以宣达诉讼者之情,而与推事相对待,有推事而无律师,则推事之权横而恣。”(P10)当时的立法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目的?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官治国、司法行政不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地方官兼任司法官主持审判,而这些官员多由科举出身,并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对法律条款也多一知半解,不客气的说,这些所谓的法官多是“法盲”。当然,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浓厚的儒家思想。“德主刑辅”、“春秋决狱”这些儒家观念决定了司法官裁判的依据可以、而且主要不依靠法律,而是儒家伦理道德。比如,中国古代官僚的模范海瑞就以这样的标准来执行法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样的精神,与“四书”的训示想符合,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P135)在这样的审判标准下,法官是不需要懂法的。
“法盲”法官,再加之其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政务繁忙,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了解案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幕友对于那些只通制艺、不晓律例的官吏,在进行司法审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463)这就导致了大堂上的草菅人命、百弊丛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末司法改革家们才力主引进西方律师制度以制约“推事”。
其实今天中国的法官,虽然不可拿之与当年的司法官相比较。但从法官的素质、法庭上法官的作用来看,恐怕难逃当年的影子。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不高,审理方式上表现出超职权主义的倾向,这些学者们都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④]面对这样的司法现状,恐怕我们的律师还应当与当年一样担负起制约法官的重任吧!
(二)当前律师制约法官程序违法的困局
笔者曾经跟很多律师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其实就当前的司法体制也并非绝对没有制约的途径,那就是法院内部的法官评价机制。法官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如果反映到领导(院长或者庭长)那里,还是可以得到适当解决的,这个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批评。当然,姑且不论这样的“惩戒”是否合乎法官惩戒应有的程序与强度,仅就这样的“反映问题”本身,笔者的律师朋友们还没有人实行过,包括本文案例中的律师。问及原因,有二:第一,不愿意或者不敢得罪法官。这个律师朋友回答地很直接:“谁知道以后我还有没有案子落在他手上,而且我得罪了一个法官就相当于得罪了这个法院所有的法官,我以后在这个法院的案子都可能会被在合法的限度内‘穿小鞋’,你还吐不出一个‘苦’字来。”第二,担心当事人会因此遭受不利的判决。可见,律师的苦衷只有两个字——不敢。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实在厚重,法官虽然没有同检察官、律师形成职业共同体,却形成了法官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你得罪了一个法官,这个院里其他该法官的朋友都会视你为“敌人”,视你为异类。还有的律师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举报了他以后见面多尴尬?”这就更说明了中国的“熟人社会”人情的厚重啊。更为重要的是,你违反了中国司法的一个“潜规则”——法官程序无违法。尽管诉讼法上规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则,但法官却无视这些规则的存在,因为只要不会影响到实体上的审理结果,程序上的违法是很少会受到惩戒的。这个“潜规则”并非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P2)而仅仅是中国司法传统的影响。这个传统是:(1)法官在程序上历来“一家独大”,也即纠问式诉讼传统影响下的所谓职权主义;(2)实体正义至上,程序虚无。
大家都遵守这个“潜规则”,法官才会跟律师“fair play”,否则,律师如果敢于打破这个规则,法官难免会有给律师“穿小鞋”,并且是在程序的框架内,让你有苦难言。司法实践中究竟是不是会这样,笔者所接触的律师当中还没有人“以身试法”,所以也无从得知。但律师们对此的担心是一致的,而仅仅是潜在可能的危险也足以使律师对法官的程序违法视而不见了。因为律师从“举报”法官中并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相反却有足够大的潜在危险。
另外,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遭遇法官程序违法的当事人未必就愿意律师“投诉”法官。原因也很简单,案子还在人家手里呢,判决还没下呢,怎么敢得罪法官?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是律师职责的根本所在,一边是程序利益一边是实体利益,律师当然得选择实实在在的实体利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局。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当是建立法官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但凡程序违法而无论是否影响实体结果都应当受到相应的制裁。但在这样的机制还未诞生,甚至还未引起学界、立法者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途径稍加改造,也好扬汤止沸,稍解燃眉之急,以待将来釜底抽薪时,锅还未煮漏。
笔者的建议:首先,律师协会应当担负起制约法官的重任。中国人的传统,爱找组织解决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当面锣对面鼓”地发生正面冲突,尤其是当对方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很“熟”的时候。由律师协会代替自己的会员来进行投诉,会有效地缓解人情的“尴尬”。当然,这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法官也同样会知道是谁在投诉他,但当这种投诉成为普遍,“潜规则”便会被打破,当投诉的律师不再是少数,那他也不会被视为“异类”。律师应当将诉讼中的法官程序违法的情况反映给当地的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向有关机构或官员反映。这就需要律师协会内部建立相应的投诉机构,专司程序违法投诉。其次,这种行政式的投诉应当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案件审理完毕,律师协会根据律师的反映来进行投诉,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遭受不利益的实体判决。当然,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违法发生时就进行纠正,提起程序性裁判程序,但在目前的司法体制内,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地论证,这种裁判程序还未进入改革视野,起不到立竿见影之效。再次,对于法官程序违法的情况,投诉应当是“绝大多数”。理论上,投诉与否主动权在律师,但法官的程序违法破坏的是整个司法秩序、司法权威,是与国家设立司法程序的初衷相背离的。打个比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犯罪是因其破坏了公共利益而必受国家追诉从而排斥了被害人的意愿的话,那么法官的程序违法也应当因其破坏了司法秩序、公共利益而在相当程度上排斥当事人的意愿。如何来实现这种“绝大多数”,笔者的想法是由律师协会建立程序违法调查制度,律师每当诉讼终结都必须将诉讼程序合法与否的情况反映给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汇总投诉。当然,律师协会不能因律师的不投诉而惩戒该律师。但这种制度的建立,相信会使律师对法官程序违法的投诉变成常态,而不至于顾虑重重。
注释:
[①] 比如法官独立,在目前的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尤其是程序虚无的观念盛行的情况下追求法官独立,笔者认为可能结果会适得其反。
[②] 本案由笔者的一位律师朋友提供,笔者亲眼见到了该案的有关诉讼文书,出于种种顾虑本文在引用的时候对有关人员名字做了文字处理。
[③]关于法律职业思维方式,很多学者都有过详尽的分析和列举,可参见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总第86期;孙笑侠:“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载《法学》2002年第1期;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④] 可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84页;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载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页;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第347页。
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徐家力.中华民国法律制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原文载《中国律师》2006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 |
240331
赵旭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一、关于程序性违法
相对于实体性违法,程序性违法是指程序参与主体违反某一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这里的程序参与主体,既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双方、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也包括程序的主持者——法官,还包括其他参与诉讼程序、在诉讼中负有一定义务的主体,如鉴定人员、翻译人员、证人等。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工具主义观念在司法界、理论界及社会公众中的深刻影响,程序性违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至今也没有)。一般而言,程序性违法行为只要没有严重到影响实体判决的公正,该行为即不会受到惩戒。这种情况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程序性违法中尤为严重。理论上,任何违反程序法的行为都应当由该主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将会导致该证据在庭审中被排除,再如合议庭的组成不合法将可能导致案件的发回重审。在立法上,两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都有相关的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对法官的程序性违法,除了列举的三四种违法行为,对其他的违法行为只要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正确判决”即不会被发回重审。逻辑的可笑之处在于,即便是因为程序违法严重到影响了“公正审判”的地步,其导致的结果却是未违法的程序参与人要承担相当程度的不利后果,因为案件被发回重审了,意味着被告人可能被合法地延长羁押、当事人的纠纷被合法地久拖不决、证人要因此耗费更多的时间来出庭,而法院却没有对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导致的诉讼拖延等损失进行赔偿。导致这种情况的制度原因极其深刻,比如侦查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构造中的“侦查本位”、法官的不独立等等。革除这些弊端非一日之功,亦非某一项单纯的规则改革所能完成,更何况某些改革时机未必成熟。[①]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借助某些微观方面的努力来制约这些程序性违法行为。
本文之所以选取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制约为视角来进行考量,是因为:第一,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法官的程序性违法受到忽略的现象更为严重,尤其在民事诉讼中。这个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司法的纠问式诉讼导致公众程序观念的虚无,不晓得有程序性违法;另外,大部分当事人,由于对法律(尤其是程序)的陌生,往往不知道法官是否违法;再者,即便是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来解决,比如法官违反审限的规定导致诉讼拖延的情况,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救济渠道;最后,当事人往往会有这样的观念:法官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法官自己的案子怎么办?所以即便是法官有些许程序性违法,只要不是太“欺负人”就算了。这些便引出本文之所以采此视角原因之第二,作为法律职业者,作为诉讼程序的亲身参与者,律师最知道法官有无程序违法情况,而作为委托人利益的维护者律师也最应当负有制约法官的义务。第三,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及时制约,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司法成本。如果案件由于程序性违法的及时被纠正,而不须等到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等来通过重审或再审来纠正,那么诉讼参与人的因此不利益便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再次使用也可以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对法官程序性违法的事情大部分得过且过,其原因何在?而如果律师愿意制约,途径应当如何呢?此即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先从两个真实的法官程序违法个案谈起。
二、个案的启示
(一)一个典型的法官程序违法个案
2004年11月12日,北京市宣武区法院立案受理了一起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于案情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不大(纠纷标的为价值约20万元的机器设备的搬迁),法院决定采取简易程序审理,独任审判员为该院民庭秘法官。案件于2004年11月29日正式开庭审理,其间11月29日、12月29日、2005年1月5日、1月6日开庭四次,于2005年1月6日庭审结束。然而,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却迟迟得不到本案的判决。原告代理律师多次打电话给本案审判员秘法官询问何时下判决,该法官总是推说太忙,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手头案子积压太多,结不了。”案件拖了三个月之久,仍无消息。在律师的一再追问、要求判决的情况下,该法官说:“本案法定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已过,要改成普通程序审理,何时开庭,另行通知。”于是本案当事人再次陷入了对开庭通知的漫长等待,一个多月后,在律师的多次催问下,2005年4月22日,本案终于再次以普通程序开庭,法庭由审判员秘法官及两名陪审员组成。于是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又走了一遍,终于普通程序庭审完毕,结果该案件再次陷入了对判决的苦苦等待。至2005年8月9日,本案件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诉讼过程后,当事人终于难熬等待的折磨,被迫部分和解,第三人同意原告将设备拉走(因为原告急需设备投入新的合作项目,正是由于案件的久拖不决原告已经丧失了一个合作机会;第三人急需设备占据的厂房进行生产,也是由于案件的久拖不决,第三人多付了几个月的房租)。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秘某的很多表现很发人深思,出于本文的意旨,笔者举出其中两次。一次是在庭审后,该法官曾经很不屑地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说:“人家那么多案子都能调解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另有一次,原告代理律师曾经于2005年5月23日,应该法官的要求向其提交书面材料一份,后来在谈话中提及,该法官抱怨代理人未将情况反映给他,当代理人提到材料已交给他后,秘法官竟然很坦然地说根本没看这个材料。时至2005年11月3日,案件立案近一年了,该案仍然没有得到法院判决。[②]
这个普通的经济案件,反映的问题的确很多,比如法官的素质问题,强制调解的问题等等。但最根本的,笔者认为还是法官的程序性违法的问题。本案的法官的一个很明显的违法之处,在于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案件自立案之日,拖延了五个月之久仍未给出判决,远远超过了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对于此,当事人及代理人没有丝毫办法,因为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关于违反该程序应当如何救济的规定。而本案的秘法官却有办法:超过审限了?好说,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便罢。全然不顾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纠纷的最终、尽快解决的切盼。使得纠纷当事人利益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尊严和公信力。并且,本案法官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的作法,其本身也很难说是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院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70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次日起计算。”可见,即便是案情复杂(最高院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68条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给出了解释,但案情究竟复杂与否仍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从本案看,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无疑。因为本案最初就是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完毕,只需一个判决即可终结的。更何况法官已经给出了案件为何久拖不决的原因:案件积压太多,结不了。)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那也应当是在审理过程中作出决定,更何况即便是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审理期限仍然超过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案件六个月的审理期限。当然,民诉法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有特殊情况吗?难道“案件积压太多,结不了”也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如果有,并且经过了院长批准那有什么拿不到台面上的,还需要以“案件积压”为借口来搪塞代理人的追问呢?
案例中所示法官的行为,明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笔者称之为“典型的程序性违法”。
(二)一个非典型案例
据笔者的了解,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这种违反审限、拖延诉讼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还是有法可循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更多的时候法官的行为根本不违背任何法律。比如,案件中所提到的律师就在北京市大兴区法院遇到过另外一件事情,执行庭某法官通知被执行人和其代理人于2004年某月某日上午9点在法院某谈话室谈话,第二天早上当被执行人和律师风尘仆仆从市里花费了近2个小时按时赶到法院,却找不到法官,打电话一联系,法官出去办事了,法官很坦然地说:“忘记了”,让被执行人和律师回去,“改天再说”。
这个案例,很难明确地说法官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哪一条,哪一款。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法官不按时出庭应当如何处理,笔者姑且在本文中称之为“非典型程序错误”,之所以将之称为“错误”而不是“违法”是因为人家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肯定不正确,法官通知当事人及代理人到庭谈话,却忘记了,便临时取消,该法官不算违法也并不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是当事人忘记了出庭会怎样?是要为此承担不利结果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一百三十条也规定了当事人不出庭的程序后果,原告按撤诉处理,被告缺席判决。同样是程序的参与主体,为什么法官不出庭就没有相应的后果?如果说,当事人不出庭是对法庭的藐视,那法官不按时出庭不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吗?不是更应当受到制裁吗?或许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法官又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凭什么制裁法官。笔者看来,无论哪个国家的程序法律都没有必要对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作出规定,我们也从没见过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官必须按时出庭的”。法官是“游戏”的主持者和裁判者,法官随意的不出庭,纠纷当事人凭什么相信这样随意的法官会作出公正的裁判?法官——这个所谓的精英分子,连“诚实、守信”这个市场经济下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怎么能让当事人尊重其“权威”?
(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法官之所以会如此大胆地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或未规定的程序,原因并不复杂。第一、司法传统所导致的程序虚无;第二、对法官程序违法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法治的最大障碍来自文化传统。(P8)在中国传统司法中,“全能型衙门”的“些小吾曹州县吏”,居于本级政府权力格局的核心,地位至高无上,大堂之上说一不二(P60)。滋贺秀三将这种法官以“父母官”的身份“坐堂问案”的方式称为“父母型诉讼”。(P16)在这种“庭审”中,大老爷说什么便是什么,说什么时候开庭便什么时候开,说什么时候“休庭”便什么时候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的,更无论有法可循了。《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便写贾语村刚补授了应天府便接了人命官司,语村听了原告的陈述大怒,正待发签捕人、拿人拷问之际,葫芦僧出现了,向语村使眼色儿,“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一个眼色,心下“疑怪”,便退堂“休庭”,哪里需要什么法定“诉讼中止”啊什么的。这种司法传统,其影响便会是:其一,法官拿程序不当回事;其二,当事人拿法官程序违法不当回事。法官、当事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程序岂能不虚无?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小民”们不愿挨,又有什么渠道救济呢?只要程序违法不“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错案追究制度”又会追究到哪个法官头上呢?这恰好说明了对法官程序违法的制约无力,陈瑞华教授对此早有深刻的揭示,(P8-69)笔者深表赞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病症,是一项庞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司法体制、全社会的法制观念等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笔者本文不拟探讨这个问题,只希望在当前的体制框架内找到一种微观的方法,暂时缓解病痛,以无奈地等待“大手术”。
三、律师在制约法官程序违法中的作用
(一)律师所应有的作用
笔者在前面提过,相对于“外行”的当事人,律师最了解法官在诉讼中有无程序违法,而同时律师如果能及时对这种程序违法进行制约,那么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司法成本。此外,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也是律师职责的应有之意。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法官还是律师,他们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而所谓职业共同体应当有同一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其中很重要的几点是应当具有“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以及程序优先和形式理性。[③]正是有以这些法律家所应有的独特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职业素养,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和权威、保证司法自治与司法优先,保证法治对人治的阻隔。遵守和维护这些原则,应当是“法律人”最基本的道德和使命。这也许是中国“法律人”遭遇信任危机的最根本所在,正如孙笑侠教授所述:“我国的部分‘法律人’……缺乏相应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失职于对正义的维护并且还进一步亵渎了正义。”(P74)律师在面对法官的程序违法的时候,应当有维护法律职业尊严的使命感,而不应当是保持“明哲保身”的沉默甚或于“进一步亵渎正义”。因为,律师并非以维护委托人职责为其惟一职责,他还应当肩负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使命。
在我国,律师对法官的制约,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制度背景的。尽管中国的“讼师”已有千年的历史,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在中国的出现却晚至鸦片战后,从租界的领事法庭走向“会审公堂”,逐渐介入晚清直至民国的社会生活。清末的司法改革,律师制度进入了“改革派”视野,而这些“有识之士”之所以推崇参照西方设立律师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律师在公堂上的出现可以制约法官(当时称为推事)。当时的邮传部主事陈宗蕃在其1910年的“司法独立之始亟宜预防流弊以重宪政”奏折中就提出:“律师之用,所以宣达诉讼者之情,而与推事相对待,有推事而无律师,则推事之权横而恣。”(P10)当时的立法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目的?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官治国、司法行政不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地方官兼任司法官主持审判,而这些官员多由科举出身,并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对法律条款也多一知半解,不客气的说,这些所谓的法官多是“法盲”。当然,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浓厚的儒家思想。“德主刑辅”、“春秋决狱”这些儒家观念决定了司法官裁判的依据可以、而且主要不依靠法律,而是儒家伦理道德。比如,中国古代官僚的模范海瑞就以这样的标准来执行法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样的精神,与“四书”的训示想符合,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P135)在这样的审判标准下,法官是不需要懂法的。
“法盲”法官,再加之其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政务繁忙,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了解案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幕友对于那些只通制艺、不晓律例的官吏,在进行司法审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463)这就导致了大堂上的草菅人命、百弊丛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末司法改革家们才力主引进西方律师制度以制约“推事”。
其实今天中国的法官,虽然不可拿之与当年的司法官相比较。但从法官的素质、法庭上法官的作用来看,恐怕难逃当年的影子。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不高,审理方式上表现出超职权主义的倾向,这些学者们都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④]面对这样的司法现状,恐怕我们的律师还应当与当年一样担负起制约法官的重任吧!
(二)当前律师制约法官程序违法的困局
笔者曾经跟很多律师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其实就当前的司法体制也并非绝对没有制约的途径,那就是法院内部的法官评价机制。法官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如果反映到领导(院长或者庭长)那里,还是可以得到适当解决的,这个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批评。当然,姑且不论这样的“惩戒”是否合乎法官惩戒应有的程序与强度,仅就这样的“反映问题”本身,笔者的律师朋友们还没有人实行过,包括本文案例中的律师。问及原因,有二:第一,不愿意或者不敢得罪法官。这个律师朋友回答地很直接:“谁知道以后我还有没有案子落在他手上,而且我得罪了一个法官就相当于得罪了这个法院所有的法官,我以后在这个法院的案子都可能会被在合法的限度内‘穿小鞋’,你还吐不出一个‘苦’字来。”第二,担心当事人会因此遭受不利的判决。可见,律师的苦衷只有两个字——不敢。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实在厚重,法官虽然没有同检察官、律师形成职业共同体,却形成了法官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你得罪了一个法官,这个院里其他该法官的朋友都会视你为“敌人”,视你为异类。还有的律师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举报了他以后见面多尴尬?”这就更说明了中国的“熟人社会”人情的厚重啊。更为重要的是,你违反了中国司法的一个“潜规则”——法官程序无违法。尽管诉讼法上规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则,但法官却无视这些规则的存在,因为只要不会影响到实体上的审理结果,程序上的违法是很少会受到惩戒的。这个“潜规则”并非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P2)而仅仅是中国司法传统的影响。这个传统是:(1)法官在程序上历来“一家独大”,也即纠问式诉讼传统影响下的所谓职权主义;(2)实体正义至上,程序虚无。
大家都遵守这个“潜规则”,法官才会跟律师“fair play”,否则,律师如果敢于打破这个规则,法官难免会有给律师“穿小鞋”,并且是在程序的框架内,让你有苦难言。司法实践中究竟是不是会这样,笔者所接触的律师当中还没有人“以身试法”,所以也无从得知。但律师们对此的担心是一致的,而仅仅是潜在可能的危险也足以使律师对法官的程序违法视而不见了。因为律师从“举报”法官中并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相反却有足够大的潜在危险。
另外,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遭遇法官程序违法的当事人未必就愿意律师“投诉”法官。原因也很简单,案子还在人家手里呢,判决还没下呢,怎么敢得罪法官?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是律师职责的根本所在,一边是程序利益一边是实体利益,律师当然得选择实实在在的实体利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局。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当是建立法官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但凡程序违法而无论是否影响实体结果都应当受到相应的制裁。但在这样的机制还未诞生,甚至还未引起学界、立法者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途径稍加改造,也好扬汤止沸,稍解燃眉之急,以待将来釜底抽薪时,锅还未煮漏。
笔者的建议:首先,律师协会应当担负起制约法官的重任。中国人的传统,爱找组织解决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当面锣对面鼓”地发生正面冲突,尤其是当对方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很“熟”的时候。由律师协会代替自己的会员来进行投诉,会有效地缓解人情的“尴尬”。当然,这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法官也同样会知道是谁在投诉他,但当这种投诉成为普遍,“潜规则”便会被打破,当投诉的律师不再是少数,那他也不会被视为“异类”。律师应当将诉讼中的法官程序违法的情况反映给当地的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向有关机构或官员反映。这就需要律师协会内部建立相应的投诉机构,专司程序违法投诉。其次,这种行政式的投诉应当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案件审理完毕,律师协会根据律师的反映来进行投诉,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遭受不利益的实体判决。当然,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违法发生时就进行纠正,提起程序性裁判程序,但在目前的司法体制内,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地论证,这种裁判程序还未进入改革视野,起不到立竿见影之效。再次,对于法官程序违法的情况,投诉应当是“绝大多数”。理论上,投诉与否主动权在律师,但法官的程序违法破坏的是整个司法秩序、司法权威,是与国家设立司法程序的初衷相背离的。打个比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犯罪是因其破坏了公共利益而必受国家追诉从而排斥了被害人的意愿的话,那么法官的程序违法也应当因其破坏了司法秩序、公共利益而在相当程度上排斥当事人的意愿。如何来实现这种“绝大多数”,笔者的想法是由律师协会建立程序违法调查制度,律师每当诉讼终结都必须将诉讼程序合法与否的情况反映给律师协会,由律师协会汇总投诉。当然,律师协会不能因律师的不投诉而惩戒该律师。但这种制度的建立,相信会使律师对法官程序违法的投诉变成常态,而不至于顾虑重重。
注释:
[①] 比如法官独立,在目前的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尤其是程序虚无的观念盛行的情况下追求法官独立,笔者认为可能结果会适得其反。
[②] 本案由笔者的一位律师朋友提供,笔者亲眼见到了该案的有关诉讼文书,出于种种顾虑本文在引用的时候对有关人员名字做了文字处理。
[③]关于法律职业思维方式,很多学者都有过详尽的分析和列举,可参见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总第86期;孙笑侠:“法官与政治家思维的区别”,载《法学》2002年第1期;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④] 可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84页;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载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页;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第347页。
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徐家力.中华民国法律制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原文载《中国律师》2006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