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获得更多功能使用权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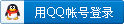
x
徐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四)美国
自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4.1条被采纳以后,美国各州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得到了统一。目前,在联邦法院,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如下:
1、由当事人提出外国法申辩
依据F.R.C.P44.1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欲提出一项关于外国国家法律的争点时,应当在其诉答文书中给予通知或其它合理的书面通知。之所以要求当事人就外国法给予通知,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法院和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的突然袭击,不过通知中所含概的外国法的信息量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则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些法律系统评注认为,通知必须详述争议中被认为取决于外国法的部分,并指明是哪个国家的哪些法律。[lxi]但是,规则并不要求依赖于外国法的当事人在他申辩的最初阶段就表明他的意图,他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提出外国法申辩,而外国法的信息量则取决于作出通知的时间。通知作出的时间越晚,外国法的资料应越详细。此外,在通知中应当以恰当的援引的方式说明相关的外国法(法典、制定法或判例)确实存在。如有必要,通知还应就该外国法提供充分的背景资料以便对方当事人能够就该外国法进行辩论,并使法院能够决定该外国法是否具有可适用性。规则44.1并未对通知的期间作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法院可以自由确定,法案修订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建议法院考虑以下因素:案件所处的阶段,未能及早通知的原因,提出外国法对本案的重要性。[lxii]如果没有减轻情节,不允许当事人在审前会议结束后提出外国法申辩。
2、法官决定外国法
规则44.1规定:法院,在决定外国法上,可以考虑任何相关材料或来源,包括证言,无论其是否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及是否符合《联邦证据规则》的可采性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是出于诉讼经济的目的。如果严格地遵守证据规则,专家证词必须接受交叉询问,这样就使外国法的证明变得十分烦琐、昂贵。准许引入不具可采性的外国法证明方式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同时该规定也准许法官自行研究可适用的外国法。顾问委员会认为:法官有权,但非强制性地,自行调查外国法。[lxiii]当事人关于外国法的证明最常用的方式是,提供附相关外国法原件副本及英译本副本的专家宣誓书或专家证言。不同的法官对当事人提供的外国法信息量的要求各不相同。在一个案件中,法官认为当事人提供《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有关条款的翻译文本就足够了,[lxiv]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关于法文“lesion corporelle”(身体伤害)这一术语,法官要求当事人提供法国权威专论、法国官方杂志、法文条约草案的翻译文本及法英普通词典和法英法律词典。[lxv]而在Kalmich v.Bruno一案中,原告提供的一份未经宣誓亦未经交叉询问的南斯拉夫法学家的意见书,即被法官认可了。[lxvi]虽然规则44.1允许法官就外国法自行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都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很少主动查明外国法。
3、未能证明外国法及外国法适用错误的后果。
由于一方当事人在决定提出外国法申辩前,都会对外国法有一定的了解,因此通常,未能证明外国法的情形很少发生。从理论上看,未能证明外国法会产生驳回诉讼或适用本地法两种后果,至于实际产生何种后果,则由该外国国家法律制度的性质决定。如果属于普通法国家,则法官推定适用美国法;如为非普通法国家,则产生驳回诉讼的后果。由于规则44.1规定,法院关于外国法的决定应当被视为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因此,当事人可以就外国法的适用错误提起上诉。而且,上诉法院不受地区法院所获得的关于外国法资料的限制,在审核外国法材料方面上诉法院与审判法院有同等的自由。[lxvii]
(五)英国
1、一般规则
由于外国法被视为事实问题,因此,非经一方当事人申辩,英国法院不会主动适用外国法,即使冲突规范已指明应适用外国法;证明外国法的责任在于其主张或抗辩是以该外国法为基础的当事人,如该当事人提不出外国法证据或证据不足,法院就将把一个含有涉外因素的案件视为一个纯粹英国国内的案件来审理。
通常的外国法的证明方式是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es)。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靠简单地援引外国立法条文或外国法院判决或权威著作来证明。这些材料只能作为专家证人的部分证据被提交,但没有专家证人的协助,法院就不可能评估和解释这些材料。而且,外国法必须在每一个案件中加以证明,不能从过去审查过同样的外国法规则的英国法院的判决中推断外国法规则,这种判决只是一种“准先例”(quasi-precedent),它对于后来的法院没有约束力。英国1972《民事证据法》(Civil Evidence Act 1972)第4(1)规定:被要求就外国法作证的专家证人必须依其认知或经验是适格的,但并非必须是或有资格是外国的执业律师。他可以居住在英国,也可以是外国居民,可以是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也可以是大学教师。比如,伦敦大学东方和非州研究所的法学教授可以就加纳法作证。[lxviii]同样,纽约律师协会的成员或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也可以就美国法作证。[lxix]任何由于其职业或工作已获得外国法律实际知识的人均可以成为有资格的专家证人。
对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他并没有义务也就外国法提出专家证人。如果他未提出,则法院通常会接受一方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假定这些证据是首尾连贯、清楚且无明显错误的。[lxx]如果专家证人的意见书不被他所提交的外国法律渊源支持,那么法院会自行对这些渊源进行审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通常,由于普通法诉讼制度的高度对抗性,双方当事人都会就外国法提出专家证人,然后由法院推理裁定,或者倾向于一方的证据或者接受每一方所提出的部分证据。法院的审查范围严格限定于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外国法律渊源内,如果专家援引的是外国判决中的一段或外国法律评论书中的一段,则法院就不应当查看该判决或评论书中的其它内容。对此,Chelmsford勋爵这样表述:“法官自行探究外国法律渊源将与证明的性质相违背……法官不应拥有了解和处理外国法的机构,也不应要求得到那些懂得解释外国法的律师的帮助。”[lxxi]对于在外国法律渊源的效力方面相互抵触的几个专家证人的意见,法院有权且有义务审查这些渊源并对之自行做出决定。而对于那些相互抵触的外国判决,法院也必须就其效力作出决定,如果依据所提示的证据,法院确信某个判决并未准确表达外国法的内容,那么法院就不会适用该判决。不过,法官所作的这一切都仅限于推理判断,他的行为不能超出当事人所提供的材料范围。
传统的英国上诉制度规定,只有初审法院有权听取证人陈述。由于上诉法院是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作出裁决,因此上诉法院不能考虑新的证据方法,不过,上诉法院在评论初审法院对向其提供的文件的证据所作的解释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所以,在外国法的问题上,过去,上诉法院只能通过修正初审法官对文件和证据的解释来作出变更有关外国法含义的判决。但是现在,英国法院已抛弃了传统的上诉制度,规定上诉法院的上诉应使用重新听审的方式(by way of rehearing),因此,上诉法院有第一审法院所有的修改诉讼文件的全部权力,有就事实问题接受新的证据的全部自由裁量权。自英国上诉制度改革后,虽然上诉法院怠于介入涉及一般事实裁决的判决,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更乐于介入修正一审法院在外国法问题上的判决。因为“外国法的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实,但却是一种特殊事实。关于外国法的事实裁决与普通事实裁决具有不同性质。”[lxxii]上诉法院认为自己有责任审查关于外国法的证据从而得出自己的决定。在英国,因外国法的错误不仅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也可以对法院上诉的裁决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上议院在这方面也不乏推翻上诉法院判决的案例。
2、例外规则
关于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规则存在着以下例外情形:
(1)简易判决
《最高法院规则》014规定的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程序是这样进行的:原告以宣誓声明提出他认为被告除关于损害赔偿金额外,对原告的请求提不出任何防御方法。但是当争议明显涉及外国法时,原告不能基于外国法未被申辩即假定外国法与英国法相同这一假设而申请简易判决。对此,Buckley法官在国民航运公司诉阿拉伯一案中这样解释:“我们的法律的确承认这种假设,即英国法与外国法相同,除非有证据证明其差异。本案原告也正是基于这一假设申请简易判决。但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明显涉及外国法律因素的案件中,原告基于上述假设而获得简易判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必须向我们证明外国法与英国法没有差异。”[lxxiii]
(2)国际义务(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这个例外规则是由Diplock勋爵在UCM诉加拿大皇家银行一案中确立的。其内容是:如果在对一案件听审的过程中,法院意识到原告所诉的合同是一个因本国已接受了一项国际义务从而使之已成为一个不可执行的合同时,即使被告没有提出有关国际义务的申辩,法院也必须自己确定这一要点,并拒绝提供强制执行合同的救济。[lxxiv]
UCM诉加拿大皇家银行是一个违约之诉,所诉的合同与加拿大外汇管理条例有关。Diplock勋爵认为,这里的“国际义务”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ivⅢ(2)(6)条规定,即“有关任何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契约,如与该国按本协定所施行的外汇管理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无效。此外,各会员国得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使彼此的外汇管理条例更为有效,但此项措施与条例应符合本协定。”Diplock勋爵认为,该规定旨在禁止强制执行违反外国法律的合同以保护外国国家的利益。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合同违反加拿大外汇管理条例的申辩,但是英国法院应当根据国际义务自行考虑争点,所以,法院要求原告证明合同不是非法的,如他未能证明,则法院将拒绝强制执行该合同。
(3)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即使在没有国际条约的约束下,“如果一英国法院意识到一个合同违反外国法律,尽管当事人并未提出外国法申辩,英国法院出于礼让和公共利益的考虑也不会强制执行这类合同”。[lxxv]这就是公共利益规则,该规则是于1958年在Regazzon诉Sethia一案中确立的。它要求,如果合同涉及一个在外国国家从事的并被该国法律认为是非法的行为,则英国法院不得强制执行该合同或给予违约赔偿。此规则的目的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执行一个对外国国家实施非法行为的合同将与礼让的职责相冲突,而且会影响英国与外国国家的良好关系,所以不应当仅仅因为当事人未提出外国法申辩就不考虑这种风险。”[lxxvi]
英国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是一个纯粹的程序规则——申辩与证明规则,它是建立在法院不得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争点这个英国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由于基本原则本身就有例外,因此,关于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的一般规则亦有例外。
四、国际公约
事实上,无论是由法院还是由当事人负责确定外国法的内容,都存在很多困难。在应适用外国法的案件中,如因无法确定外国法而不予适用或适用不当,都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早在1877年,国际法协会就曾召开会议,谋求设立国际法律调查局,负责证明外国法。1891年,国际法协会又作出决议,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对于外国法的存在或内容发生争议时,可由法院依职权,经司法部或外交部,向外国司法部提出调查请求书,以查明应适用的法律。1968年,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还专门就相互提供法律资料问题缔结了《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又称伦敦公约)。1979年,美州国家组织成员国也缔结了一项《美州国家间关于外国法证明和查询的公约》。这两个公约就缔约国间在相互查明外国法方面的协助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它们不仅允许本组织内的成员国参加,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因此这两个公约在国际上都具有重大影响。
(一)公约的实施
1、交换外国法资料的范围
由于各国在审判实践中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往往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因此,各国对于“外国法资料”的范围一般也取广义的解释,其范围不仅仅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而且还包括其他对于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或参考价值的文件。同时,所提供的法律亦不以现行有效者为限,对于过去曾经施行过的法律也在可请求提供之列。如伦敦公约规定,请求国可以要求提供被请求国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资料,以及有关司法组织的资料。被请求国的答复应当包括,在必要时,有关的法律文本、司法判例。同时还应附具使请求机关正确理解所必需的任何其他资料,诸如理论文章的摘要和立法过程中的准备文件,也可以附些说明性的注解。
2、提供外国法的程序
在提供程序上,两公约均规定由每个缔约国设立或指定一个国家级部门或中央机关。接受来自其他缔约国的请求,同时设立或指定一个或数个机构,接受来自其本国司法机关的提供资料的请求,并将其转递给外国相应的接受机构。伦敦公约规定:“请求提供资料只能由司法机关提出,即使其请求并非由该机构拟定,提供资料的请求只有在诉讼开始后才可提出。”1978年于斯特拉斯堡订立的该公约附加设定书中,对此作了补充规定:“请求提供资料,不仅可以由司法机关提出,也可以由在官方司法救助和咨询体制中代表经济贫弱者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不仅可以在诉讼实际开始后提出,也可以在诉前准备阶段提出。”这项修订主要是为了与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衔接。就提供程序而言,两公约均规定,应由转递机构直接将提供资料的请求书,送交被请求国的接受机构,如无转递机构,也可由有权提出请求的机关直接送交。在答复的送交上,如果请求是由转递机构转递的,则接受机构应将答复送交转递机构,如果请求是由请求机关直接送交的,则答复也直接送交请求机关。
在提供外国法所使用的语言上,通常提供资料请求书及其附件应使用被请求国语言或其官方语言中的一种,或附上有该种语言的译本。答复则使用被请求国语言。
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费用,依据两公约的规定和各国的司法实践,通常除了由私人团体和律师个人负责实施有关请求时所引起的费用由提出请求的国家负担外,答复不得征收任何费用或付任何开支。
3、提供外国法的拒绝
依据公约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请求国国家联络机构收到请求国有关机关递交的提供外国法资料的请求后,对提供资料的请求都应尽快答复,当答复需要较长时间时,接受机构应及时通知提出请求的外国机关,并告知其送交答复的大概日期。但是,如果提供资料的案件影响被请求国的利益、主权或安全时,则被请求国有权拒绝执行,这是各国公认的原则,对此,两公约都作了相应的拒绝提供外国法的规定。从司法实践中看,提供外国法资料涉及主权、安全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请求方要求提供立法过程中的资料,而其中有部分内容就可能涉及被请求国的主权或安全,或者请求国为确定外国法的内容而提出提供资料的请求但该案件本身可能涉及被请求国的主权或安全等。在实践中,这一问题都是由中央机关或主管机关判断确定的。
4、交换外国法情报的效力
关于外国法证明的国际公约,其目的旨在制订若干规则,以调整缔约国之间相互取得外国法的证明要点和查询方面的国际合作。因此,作为一般性的法律交流,通常不会产生交换的法律情报的效力问题。但是,在查明外国法的过程中,对于缔约国所提供的外国法资料对另一缔约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绝大多数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均拒绝给外国法与本国法相同的效力。如1968《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第8条规定:“答复所提供的资料,对提出要求的司法机构均无约束力。”1979《美州国家间关于外国法证明和查询的公约》第6条也规定:“对提出……报告的国家,不得认为应对其发表的意见负责,他不得要求其根据提供的答复内容而适用该法律,或者促使该法律得以适用。”所以,缔约国间根据公约提供的外国法情报的效力,仍受请求国国内法的约束,由请求国法院根据本国法律制度自由决定是否适用。
(二)伦敦公约的实际效果
作为在外国法证明与查询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伦敦公约,自1968年订立以来,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其间,欧洲理事会已有39个成员国签署加入该公约,此外,还有2个非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也加入了该公约。公约的主旨在于“为了便利司法机构取得外国法资料的工作而建立一个国际协助制度”,从而使“缔约国……相互提供各自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资料,以及有关司法组织的资料。”1978年,该公约签字国又在斯特拉斯堡订立了《附加议定书》,“将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互助体制在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多边结构中,扩展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同时,“考虑到为消除法律程序中的经济障碍和使经济贫弱者在各成员国内更易于行使其权利,希望将本公约所确立的体制扩展至民商事司法救助和咨询领域。”依据附加议定书的规定,缔约国不仅可以相互提供其刑事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律和司法组织包括起诉机关的资料,及有关执行刑事处分的法律,而且提供资料请求不仅可以由司法机关提出,也可以由在官方司法救助和咨询体制中代表经济贫弱者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在提出阶段上,不仅可以在诉讼实际开始后提出,也可以在诉前准备阶段提出。《附加议定书》的订立使伦敦公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那么,自公约实施以来,其成效究竟如何呢?自1993年起,Strathclyde大学的Barry J.Rodger和阿姆斯特丹的律师Julietie Van Doorn两位学者在欧洲理事会的协助下,从事了有关公约实施成效的调研工作。调查所取得的主要数据如下:[lxxvii]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因其涉及专家与翻译的问题,所以,虽然有的国家声称没有语言困难,但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语言障碍是主要问题。从所提供的数字来看,公约机制的利用率并不高,这有可能是由于时间与费用方面的原因。至于高昂的费用应当如何分配,由于调查工作未涉及此项内容,因此我们也就无从揣测,但总体而言,过于高昂的费用无论是作为公共开支还是私人开支,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通过调研,二位学者对于公约的成效所作的结论是:“伦敦公约只是一个极为有限的成功”。
五、启示与思考
自有法律冲突的概念提出以来,外国法的证明就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性的重要议题。在最初,不同法系的国家均是从当事人申辩的角度进行外国法的证明,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萨维尼国际私法学说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才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出现了分化,外国法的“法律说”和依职权适用外国法的制度才逐渐形成。对于不同法系国家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有学者称其是“一个连续统一体”(Hartley语),英国和德国分别为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极,在两极之间则渐次排列着美国、法国、西班牙、芬兰、瑞典、瑞士、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尽管位于统一体中部的国家在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上的差别有限,但是,对于统一体的两极而言,其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在德国,法院有义务适用外国法,即使该外国法未被申辩。在英国,法院则不能适用未经当事人申辩与证明的外国法。在德国,法官有义务自行探究以确定外国法的内容,但是,在英国,法官则被严格禁止这样做,除非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申请。
在考查了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进程并对位于“连续统一体”中的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与结论:
(一)各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差异是由创设私权的内国民事诉讼的特定目的决定的。
在普通法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与法院的功能分配是建立在民事诉讼是一种纯粹的私人事务这一理念基础上的,因此其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和维护私权。争点的提出与调查均由当事人完成,“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lxxviii]在这方面,普通法国家学者相信,“最少的司法干预是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最有效的方式”(摩根语)。于是,法官的作用就显得极为有限和被动,法官仅限于对当事人,更确地说是当事人的律师所提出的、调查的及辩论的争点进行裁决,或对当事人提出的动议予以程序上的准许或禁止。“律师之间就证据开示而展开的准备程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法官原则上只是在双方意见不一致而提出了请求裁定的申请时才进行介入的。……当事者是展开程序的主体,法官的角色仅仅停留在被动的裁决者这一位置。”[lxxix]
同样,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团审理方式也是基于民事诉讼的私人性质确立的。由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对法律没有专门的研究,不作为职业化的化身,只是通过随机遴选临时组成的凭感性理解以认定案件事实的群体,因此,在这种审理方式下,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可以运用丰富的经验和职业化的技能在一系列询问中对陪审团的事实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使陪审团形式意义上的审判权实质上演变成当事人的律师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的诉讼技能争辩,从而使陪审团审理方式成为诉讼公众化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当事人具有高 度的意思自治选择,而且,法官还为维护陪审制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义务。譬如,F.R.C.P.第38条第1款规定:美国宪法第7修正案宣布的由美国制定法赋予的当事人要求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受到保护,第39条规定,在本来有权要求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未提出要求不问其懈怠,法院基于申请,或以裁量作出由陪审团审理争点的部分或全部命令,除非(1)当事人或其记录在案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书面协议,或在公开法庭上提出口头协议,并记录在案同意由法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该案;(2)法院基于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提出部分或全部争点并不涉及美国宪法或美国制定法规定的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彻底贯彻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的原则。
由于普通法国家创设私权的内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因此,外国法作为直接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相关的问题,其证明程序是不可能交由法院去处理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想彻底查明外国法这一关涉案件的重要问题而不过份介入私人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但这种介入无疑会违反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的原则。所以普通法国家宁可将外国法的问题归入当事人双方进行的攻击与防御之中,从而保证法官能够始终处在中立的立场上听取双方的辩论,使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具有高度尊重私权意见自治和程序中心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在普通法国家的对抗制民事诉讼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事实有无限的控制权,适用法律的事实条件是由当事人独立架构的,因此,他们的私权意思自治实际上不会限止于争议的事实,而是必然延伸至应适用的法律方面。相对于数量较少的法官和庞大复杂的法律体系而言,当事人的律师很自然地就承担了为支持他们客户的申辩而进行的对法律权威书的探究工作。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中,律师在搜寻和评价对抗性的先例和制定法方面不仅对当事人具有愈来愈多的责任,而且他们对于法院的责任也同样如此。律师有责任指挥法官的注意力,使他注意到那些有可能被他忽略的法律权威书,因此,法官是依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所以就外国法而言,虽然美国法视其为法律,但在基于普通法国家民事诉讼目的基础上形成的充分尊重私权和高度对抗的大背景下,由当事人及其律师证明外国法是必然的。
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程序法是以下述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如果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法官应有权、实际上是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的情况,尽可能地避免前后不一致和含糊不清,消除因为诉讼人或者律师不细心和不懂技术所造成的失误。[lxxx]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在大陆法国家中,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即使开始纯粹是私人间的事务,一旦交给法院处理就变成了公共事务”。[lxxxi]因此,私权公法化是大陆法系国家中创设私权的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在这方面,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1879年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由于正当欧洲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所以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点,在程序上都是由当事人自由支配,国家尽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后来,随着社会形态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促使国家自1898年以来每次修订民诉法典,都相应对当事人自由支配程序增设限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法律结构特征,即国家干预加强,法院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提高,强化了法院调查证据的职权行为,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自近代以来,在德国的民事诉讼目的论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维护法律秩序学说。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司法机关的活动即民事诉讼来对抽象的制定法加以具体化和个别化,并适用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民事案件,才能最终完成私法秩序的构造。对此,德国民事诉讼法学者标罗(Bu low)曾断言:由于私法案件的当事人对抽象的私法及其法律效果缺乏统一的理解,造成法律判断的冲突。因此国家必须预备解决这种冲突的手段,这就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正是从内部来协助私法法规实现它未能完成的私法秩序的构建。[lxxxii]正是基于这种诉讼目的论的指导,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与当事人一起澄清争点是法院的职责,而且,在法院认为必要时,法院可以和当事人一起讨论案情和争点,并向当事人发问。由于没有严格的审前与审判阶段的划分,法院可以在诉讼中的任何阶段与当事人讨论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法院具有三种权力:澄清不明确的陈述,将当事人的指控(可能是以外行语言表达的)转化为精确的法律术语,指出有关的和无关的指控及证据。如果一方当事人已宣称,案件事实涉及某一特定法规的适用,而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另一法规,它就必须提醒当事人注意这一点,并给予其补充陈述的机会。法院的此项保护性职权,实际上是当今德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大宪章”。[lxxxiii]很显然,由于法官已在其头脑中对案件进行归类,因此,法官事实上是积极地、有时甚至带点强制性地构架了案件的事实争议与法律争议。法官的这种主导性地位在对待证人的态度和方式上尤为突出。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法院的证人,当事人与证人严格分开,不依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区分原告方证人和被告方证人,证人作证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专家证人通常都是由法院基于自己的意愿而传召的。法院不必依赖当事人,就可引入专家证人。虽然一方当事人也可以让自己挑选的专家证人参加诉讼,来反驳法院指定的专家,但法官一般不会直接把当事人自己找的专家证人的意见作为判案的根据,而是将其意见作为反证,成为法院更换专家的原因或理由。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人制度均与德国法的规定相似。
在民事诉讼中,大陆法系国家律师的工作仅限于对证人的提名以及在开庭审理时,经审判长的许可,向证人作补充发问。因此,有人称大陆法国家的民事诉讼为“无律师的诉讼”。事实上,的确在某些大陆法国家,当事人可以在无律师代理的情形中进行诉讼。比如,在德国的地方法院(Amsgerichte)诉讼,当事人便不需要律师代理(诉讼法典第78、79条),而许多涉及外国法因素的案件都在地方法院的管辖权限之内。在奥地利,当事人也可以在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劳动法院及婚姻诉讼中自我代理。在荷兰,当事人可以在地区法院亲自诉讼。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丹麦、芬兰和瑞典,律师代理在全部诉讼程序中都是非强制性的。日本和韩国实行的也是任意代理主义。与这些国家法官的主导性、操纵性地位相比,律师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集确定事实、确定法律与适用法律三种职能于一身,在这种民事诉讼结构中,无论外国法属于事实性质还是法律性质,无疑都会被法官依职权确定。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法国法视外国法为事实,但法官在外国法的证明方面依然起主导作用,而法国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颇多前后不一致的决定的原因。由于大陆法国家从国家公权的角度出发,规范民事诉讼。因此,即使“法官知法”的前提中不包括外国法,法官也仍然有权自主确定外国法的内容,并要求政府机构帮助他完成这一职责。大陆法国家创设私权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私权公法化的特点是构成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根本原因。
质言之,构造不同法系国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事实说”与“法律说”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外国法的证明作为一种具体的操作程式,实则体现了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表达了立法者预期通过民事诉讼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即民事诉讼的目的。普通法国家将诉讼作为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最终手段,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执和冲突,因此坚持程序中心论,注重以程序制约和限制法官的权力,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导地位,实现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而大陆法国家则坚持“程序的目的不过是实体法内容的实现,具体说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民法规定的权利,或者说在于维持民法典所预定的私法秩序”,[lxxxiv]即实体中心论。在这一目的的主导下,法官具有最高的权威,能够依职权就其自己的意愿和观点出发积极介入到整个诉讼过程当中。如果就此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形成这些差异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普通法国家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仍然是以理想化的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为终极目标,相信完全的竞争市场是利益冲突的最佳协调者,能够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因此,普通法国家建立在这种公平、放任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诉讼程序坚持个人自治,强调民事程序以内在的方式来满足解决纠纷的直接需要。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在一个现代的复杂经济中,基于现代福利国家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确保经济体制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起来。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更倾向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上的法律秩序日益具有官僚政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特征,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自然享有广泛的监督与动议权。不同法系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而不同的目的论才是决定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差异的本质原因。
(二)在冲突规范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后,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正义的原则使外国法的证明更具有证据规则的性质。
传统的国际私法学说,认为国际私法的主要目标是在于贯彻简单、方便的原则以达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的目的。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判决的确定性(certainty)、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一致性(uniformity)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冲突规范成为国际私法的核心内容,在解决涉外民事案件时,只要法官对案件的性质进行识别,确定具体案件的“范围”即法律关系在性质上的归属,相应的冲突规范便会直接、主动地指示出案件应适用的法律。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相信,冲突规范的适用能够达到不论案件在何国法院审理,都会适用同一法域的法律并使判决结果趋于一致的目的。他们“还把冲突规范比作火车站中的一套信号灯,并把法官比作火车司机,他无需知道行驶前方是什么站,只需要按照信号灯所提供的信息往前开就行了。换言之,法官无需考察冲突规范所指向援用的那个国家实体法的具体内容,只要适用它就算完成任务。”[lxxxv]冲突规范及相关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法律选择规则的唯一内涵,而国际私法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制订、修改及运用冲突规范。
二战以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及科技的巨大进步,不仅出现了诸如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这些新的类别,而且也使国际民商事关系更趋复杂化,传统的、机械的冲突规范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国际民商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美国的柯里教授指责以冲突规范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是概念式的、毫无道理的、无头脑的,甚至称它是一个诡辩的、神秘的和失败的领域。他在其著作中宣称“我的观点是,这一体系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法律选择规范,我们会更好些。”同样,卡弗斯教授也指出,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只是一种机械性的盲目的方法,它依赖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冲突规范,指令法官适用一定的法律,因此很可能使判决结果不公正,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或危害法院地的利益。[lxxxvi]传统的冲突规范由于在解决法律冲突案件时,依据预先确定的联系因素去寻找具体案件的准据法,因此,从根本上忽视了同一种类案件的事实构成的复杂性,结果无法实现案件的公正解决。同时由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致使它将各类不同的法律冲突混为一谈,而对选择性冲突规范和重叠性冲突规范所作的“有条件”和“无条件”两种类别的区分又使法律适用问题更趋复杂化。这一切都说明冲突规范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个法学家不会不注意到,现代世界正在嘲笑各国的冲突法制度,国际私法实际上是对商业行为和解决争议而人为设置的障碍”。[lxxxvii]事实上,冲突规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缺陷是其内在固有的,它因依赖于萨维尼的国际私法学说体系而错误地推测道,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超级法律”,这个超级法律通过指导或限制的方式预先就确定了可资适用的法律选择规范,这种盲目性导致了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不公正,从而使法律最终丧失其正义性质。因此,冲突规范的这种缺陷在于其存在前提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它自身所不能够克服的,试图通过对冲突规范本身进行修修补补、抱残守缺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冲突规范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由于传统冲突规范的盲目性、机械性的特点愈来愈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那种试图以一种方法来决定法律冲突中碰到的一切问题的法律适用规范已被摈弃。面对社会的发展,现代法律选择制度在法律的安全性与灵活性的两难选择中,宁愿后退一步,放弃所谓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判决一致性的目的,代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等多种方法的运用。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传统国际私法的那些目的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阻碍了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正的实现。例如,传统侵权行为法律的适用原则是以侵权行为地法为主结合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共同住所地法,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以重叠法院地法对侵权行为地法进行限制。这种法律适用原则目标明确、具体、稳定,便于法院掌握适用,但却过多地考虑行为地或法院地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当事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利益,其实质只是解决了行为应由何国法律管辖的问题,却根本忽略了法律适用的后果,与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正目的不相符,而且,把偶然的连结因素作为确定准据法的因素,对当事人而言也显失公正。所以,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官放弃过去坚持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信条和法学原则,应高度重视社会的现状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应盲目地信仰无所不包的固定不变的法律规则,法律的适用不是如何运用法律,而是能否达到法律的社会目的,即公平正义地适用法律。因此法官在法律选择过程中应奉行最密切联系原则和追求案件的具体正义原则,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考虑当事人的公正期望,通过对各种有关的联系因素和相关的具体利益的分析比较来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减少先入为主的立法选择,宁可背叛陈旧的规则,也不能牺牲具体的正义。
为了贯彻最密切联系和实现具体正义的原则,法官在处理法律冲突案件时就必须在尊重具体案件事实构成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加以区别对待。这样无疑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加强了,而要使法官不从其个人好恶或自己的利益观念出发判断是非,就必须强化当事人在程序上的主导性,通过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制约法官的权力,即由当事人双方积极提出主张和法律内容及事实构成的材料,当事人和法院三方之间围绕这些材料进行认真的对话,通过“这样一种具有透明度和可视性的程序过程来逐渐形成并获得客观性”。[lxxxviii]事实上,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和具体正义的实现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为切实的保护,而对于当事人在具体的案件中有怎样的合法权益,需要得到何种保护,当事人及其律师才有最具体的了解。因此,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正义原则的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当事人的自主性,其实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当事人向法院展示其在不同法律规范下的利益对抗,要求法院切实保护其合法权益,并由法院对之进行分析、判断进而适用具体法律的过程。所以,在涉及法律冲突的案件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参加命题”,法官所作的选择与判断只能是盲目的与随意的。要防止法官的这种随意性,切实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把对当事人的保障扩展到选择和适用法律的程序,即外国法的证明方面,使法官在法律问题上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通过当事人及其律师以“内在视点”看待法规范、法体系,使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向当事人倾斜,把举证责任作为外国法证明的落脚点,这样才能使法官有意识地、深入地对法律内容进行分析,防止法官的恣意专断。“这就是从程序中产生实体规范的过程实现正当化的权利。”[lxxxix]由此可见,一方面,萨维尼国际私法学说体系的前提性错误使传统冲突规范见弃于现代社会,因此,外国法的证明中依职权适用外国法已丧失其法律前提,另一方面,在最密切联系和实体具体正义原则的指导下,外国法的证明早已脱离了简单的法院选择和确定法律的窠臼,从根本上转而向当事人倾斜,并具有证据规则的性质,成为实现具体正义的有利的程序保障。
(三)功能分析的结果表明,构建以当事人为主导的、灵活开放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法律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并非概念性的法律结构,而是这些法律结构应当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其目的就在于产生一个由功能综合构成的体系。功能分析由于立足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要素的综合作用,因此能够对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本质性的把握。具体到法学领域而言,“如果在功能上把法律看作是社会事实情况的调节器,那末,在每个国家里的法律问题都是相似的。人们能够在世界上所有的法律秩序中提出同样的问题,甚至在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或者处于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里,适用同样的标准。”[xc]从功能分析入手,对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进行比较、归纳后,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外国法的证明的“事实说”与“法律说”只是一种表象。即使一国视外国法为法律,它也并不必然将外国法与本国法同等对待,对这些国家而言,外国法是法律,但却是另类法律(law of a different kind),对于那些视外国法为事实的国家而言,外国法也被看作是一类特殊的事实(fact of a peculiar kind)。而且,在许多国家规定的上诉程序中,依事实而上诉较依法律上诉要困难得多,许多国家的上诉法院只负责法律审,但在对待外国法的问题上,事实与法律的区别实则有限之至。当一国视外国法为法律时,它并不必然允许因外国法适用的错误而上诉至最高法院,如德国,而在另一方面,视外国法为事实的国家,在能否因外国法的适用错误而上诉这个问题上,外国法与本国法被同样对待,如英国。况且,即使是处于“连续统一体”两极的英国与德国,它们之间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差异也不应被过份夸大,因为在合同和财产领域,两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就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体系产生了一种确实奇特的对比。这显然不是说在法院地法律体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法律体系,而是说法院地法律体系在其设立的法官眼里具有优越性。这并不是否认外国法律在其所管辖的领土上以及对于它所针对的法官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法律。这只是说,对于受理案件的法官来说,这种法律本身并不具有出自该法官所服从的权力机关的强制性。这是一种对抗力的问题,而不是性质的问题。”[xci]事实上,确定事实不能与确定法律及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截然分开,法律和事实这两方面的争执点贯彻于诉讼程序进行的始终。诉讼的进行不断地推动这两种争执点相互交叉、相互重叠,因此,二者是作为同一诉讼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被提出并加以评判的。引证事实总是带上法律的色彩。所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常常是很困难的,法定证据制的存在更说明事实与法律的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
功能分析揭开了外国法证明的“事实说”与“法律说”的面纱,使我们能够从更为本质的层次即证据制度上看待外国法的证明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涉及法律冲突的案件所关涉的实际上主要是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益问题,因此,在解决法律选择问题时,法院所关心的应当是案件当事人的私人利益,正如艾伦茨维格教授所指出的:“政府除了在海事法领域以外,关于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方面的利益,只存在于诸如税收或货币问题的一些例外案件中。”凯格尔教授则更加明确地认为:“我们在国际私法中所追求的正义,要求对利益进行估价,这同任何其他判决所要求的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政府利益,而是私人利益。”[xcii]由于民事权利属于私权性质,国家不加任意干预,因此在证据制度中包括举证责任在内的功能运作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私力救济的能力。处分原则作为民事程序的本质体现,历来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一般直接涉及其实体权益问题,所以法官过于介入当事人之间就外国法而产生的抗辩,实际上是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失法官中立的地位。因为“从国家处理纠纷的观点来看,公共权力无法平等地一一介入私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与摩擦。从近代法治国家的司法权性质来看,司法权不能积极介入市民生活,如果需要国家介入的话,主要应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来实行。”[xciii]涉外民事诉讼争议的事项仍然主要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权益纠纷,因此,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自己在程序上的自由处分权利。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上的适用范围也已由合同领域向侵权、不当得利、夫妻财产制等方面扩展。随着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连结点数量的不断增多,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的趋势。
外国法作为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直接问题,它在证明方式上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当事人的申辩与举证。实际上,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外国法的依职权适用并不会给国家或政府带来什么利益,而且,国家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原本就不具有什么利益,真正的利益方是当事人。因此,如果在外国法的证明上不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申辩与证明机会,仅由臆断的准据法替代当事人的自主选择与申辩,只会造成不公正的裁决。“法的判断不许当事者染指的结果往往是在程序上带来对当事者的不意打击。在法律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日常化了的今天,承认当事者意思自治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内及法律问题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过份强调法律问题严格区别于事实问题只能使纠纷难以得到恰当地处理。”[xciv]而且,依职权适用外国法本身不仅对法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给法院带来过份繁重的任务,其实际实施情况也并不顺利,辅助法官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伦敦公约就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极为有限的成功”。
构建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外国法证明制度并不意味着全然放弃国家干预,在涉及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案件中,譬如关系到公共利益、国际义务、海事、税收和货币政策等案件,法官就应当从国家公权的角度出发,依职权处理外国法证明中的程序事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法官的定位,在绝大多数的涉外法律冲突案件中,面对私人利益的纷争,法官就是一个中立裁决人,外国法主要应由当事人主张和申辩,法官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辅助性的调查,也可以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帮助经济上的贫弱者从事外国法的证明,但应当明确的是,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必须是由当事人占主导地位,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上的自主权。法官仅在涉及国家和政府利益的案件中,才不受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限制,有义务依职权查明并确定外国法。我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93条规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文件中则是将外国法规为法律,由法院主动查明,同时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辅助查明:①由当事人提供;②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方的中央机关提供;③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④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⑤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于我国并未对民事诉讼的目的展开有意识的探讨,而过去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采取的又是超职权主义结构,因此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强化处分原则已成为目前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前提下,纵观当前世界各国在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上的发展趋势,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出发,以当事人为主导,法院职权进行为辅应当是构造我国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方向。
注释: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vol.1. 12th edn. p506-511.
[ii] 参见莫里斯:《法律冲突法》,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p511-512页。
[iii] 参见李双元、金彭年编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第59-60页。
[iv] Chesh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2thed, 1992,Chap 7.
[v]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2thed,1993,p.8.
[vi]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vi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viii] 参见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第35-36页。
[ix]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x] Jhering:Geist des Zomischen Rechts, vol.1,9th ed. p.8.
[xi] 参见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7页。
[xii] 关于法律冲突法在英国的历史发展,详见W.S.Holdsm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526.1927.
[xiii] J.H.Beale, Conflict of Laws 1663-4,1st ed. 1935.
[xiv] See Uniform Proof of Stature Act, 1920; Uniform Laws Annotated 9B 626,1966.
[xv] See Conmissioners, Prefatory Note, Uniform Laws Annotated 9A 550-551,1965.
[xvi] 截止到1966年7月1日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44.1生效前,包括California, kansas, Maryland等在内的16个州均对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作了根本性改变。
[xvii]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257-258。
[xviii] New York Civil Practice Act 1943, §343-a.
[xix] [英]P.H.科林:《英汉双解法律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p367.
[xx] Miller, "Federal Rule 44.1 and the ‘Fact’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Foreign Law eath-Knell for a Die-Hand Doctrine," 65 Mich.L.Rev.613,1967. eath-Knell for a Die-Hand Doctrine," 65 Mich.L.Rev.613,1967.
[xxi] 梅仲协:《国际私法新论》,台湾,1980年第3版,第28页。
[xxii] G.Broggini,Die Maxime "Iura Novit Curia" und das auslanudische Recht, 155Archiv fu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469,457,1956.
[xxiii] Sohm, Mitteis, Nengen, Institntiomen 1520.
[xxiv] Ph.J.Eder, Tentative Note on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Latin Americ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 INT,L & Comp. L. Proceedings 160.
[xxv] G.F.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1. Teil. p150, 2. Teil, p151.
[xxvi]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 186, p24-28.
[xxvii] 39 Entscheidungen des Reichsgerichts in Zivilsahen 371, 376.
[xxviii] OGH 8.10.1964,10b, 59/64,cited by H.Koh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5thed, 1988, p26.
[xxix] B.Vouilloz, Le Role du Juge Civil a L,Egard du Droit Etranger, 1991, p7-8.
[xxx] R.D.Kolleuijn, American-Dutc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76.
[xxxi] Taborda Ferreira-Guggenheim, Portagal,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07.
[xxxii] Andersen, 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Scandinavian Legal Systems, A.B.A.Sec.Int,l And Comp. Law, Proceedings 135.
[xxxiii] Reinhold Geimer,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βrecht, 1987,note 2141.
[xxxiv] Bundesarbeitsgericht, judgment of 10.04,1975,R.I.W. 1975,p521.
[xxxv]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1页。
[xxxvi] Christian von Bar, Internationales Privatecht, vol.Ⅱ,1991,p341.
[xxxvii] Jan Krophol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2d edn,1994, p519.
[xxxviii] 《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如果外国法的内容无法查明,应适用瑞士法”。
[xxxix] Francosis Knoepfler, op. cit. Revue critique, 1988,p234,转引自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xl] Civ. 12May 1959.
[xli] Compagnie algerienne de Credit er de Banque v. Chemony, civ. 2 Mar.1960.
[xlii] 〖ZW(〗Civ. 9 Feb. 1983, Civ. 24 Jan. 1984.
[xliii] Civ. 25 Nov. 1986, Civ. 25 May.1987.
[xliv] Civ. 11 and 18 Oct. 1988.
[xlv] Civ. 4 Dec. 1990.
[xlvi] Lagarde, Rev. crit. dr. int. pr. 1994, p332,337.
[xlvii] Civ. 6 Feb. 1843.
[xlviii] 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xlix] Civ.6 Dec. 1977; Civ. 4 Apr. 1978.
[l] Lautour, Cour de cassation, Civ. 25 May 1948; Societe Thinet, Cour de cassation, Civ. 24. Jan. 1984.
[li] Civ. 24 Jan. 1984.
[lii] Civ. 15 June. 1982.
[liii] Ch. com. 16Nov. 1993.
[liv] Civ. 29 July 1929.
[lv] Civ. 6 Dec. 1972.
[lv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2页。
[lvii] 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lvii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7页。
[lix] 同上,第468页。
[lx] Civ. 2 Feb. 1966.
[lxi] Wright & Miller, Federal Practice & Procedure §2443,p403.
[lxii] 28 U.S.C.Rule 44.1,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1966 Amendments to Rule, p292.
[lxiii] 28 U.S.C.Rule 44.1,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1966 Amendments to Rule, p292.
[lxiv] Re Fotochrome, Inc., 377 F. Supp. 26, 29.
[lxv] Burnet v.Trans World Airline, Inc. 368 F.Supp.1152.
[lxvi] Ramirez v.Awto.Blancos Flecha Roja, 486 F.2d 493,497.
[lxvii] 9 Wright & Miller, Federal Practice & Procedure p2443 at 415.
[lxviii] Mccode v.Mccode, The Independent, 3 Sept, 1993.
[lxix] See X,Y and Z V.B, 1983 2 All E.R.464.
[lxx] 过去,外国法的问题由陪审团决定,现在根据1987《最高法院法》S69(5)的规定,外国法的问题由法官独自决定。
[lxxi] 11 ER 1168, p1175.
[lxxii] 2 L Loyd ,s Rep. 233, p286.
[lxxiii] [1977]LLoyd,s Rep. 363, p366(CH).
[lxxiv] [1983]A.C. 168, p189.
[lxxv] [1958]A.C.301.
[lxxvi] [1958]A.C.301.
[lxxvii] 有关调查内容详见“Proof of Foreign Law:The Impact of the London Convention”, I.C.L.Q., Jan.1997,p151-173.
[lxxvii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ZW)〗
[lxxix]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lxxx]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页。
[lxxx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26页。
[lxxxii] 标罗:《诉讼与判决》,转引自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lxxxiii] Peter Gottwald, "Simplified Civil Procedare in West Germany", 3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p687,1983.
[lxxxiv]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8页。
[lxxxv]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lxxxv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页。
[lxxxvii]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lxxxvii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21页。
[lxxxix]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xc]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xc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53页。
[xci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第139页。
[xciii] 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105页。
[xciv] 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出处:转载于中国法学网 |
240331
徐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四)美国
自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4.1条被采纳以后,美国各州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得到了统一。目前,在联邦法院,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如下:
1、由当事人提出外国法申辩
依据F.R.C.P44.1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欲提出一项关于外国国家法律的争点时,应当在其诉答文书中给予通知或其它合理的书面通知。之所以要求当事人就外国法给予通知,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法院和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的突然袭击,不过通知中所含概的外国法的信息量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则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些法律系统评注认为,通知必须详述争议中被认为取决于外国法的部分,并指明是哪个国家的哪些法律。[lxi]但是,规则并不要求依赖于外国法的当事人在他申辩的最初阶段就表明他的意图,他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提出外国法申辩,而外国法的信息量则取决于作出通知的时间。通知作出的时间越晚,外国法的资料应越详细。此外,在通知中应当以恰当的援引的方式说明相关的外国法(法典、制定法或判例)确实存在。如有必要,通知还应就该外国法提供充分的背景资料以便对方当事人能够就该外国法进行辩论,并使法院能够决定该外国法是否具有可适用性。规则44.1并未对通知的期间作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法院可以自由确定,法案修订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建议法院考虑以下因素:案件所处的阶段,未能及早通知的原因,提出外国法对本案的重要性。[lxii]如果没有减轻情节,不允许当事人在审前会议结束后提出外国法申辩。
2、法官决定外国法
规则44.1规定:法院,在决定外国法上,可以考虑任何相关材料或来源,包括证言,无论其是否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及是否符合《联邦证据规则》的可采性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是出于诉讼经济的目的。如果严格地遵守证据规则,专家证词必须接受交叉询问,这样就使外国法的证明变得十分烦琐、昂贵。准许引入不具可采性的外国法证明方式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同时该规定也准许法官自行研究可适用的外国法。顾问委员会认为:法官有权,但非强制性地,自行调查外国法。[lxiii]当事人关于外国法的证明最常用的方式是,提供附相关外国法原件副本及英译本副本的专家宣誓书或专家证言。不同的法官对当事人提供的外国法信息量的要求各不相同。在一个案件中,法官认为当事人提供《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有关条款的翻译文本就足够了,[lxiv]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关于法文“lesion corporelle”(身体伤害)这一术语,法官要求当事人提供法国权威专论、法国官方杂志、法文条约草案的翻译文本及法英普通词典和法英法律词典。[lxv]而在Kalmich v.Bruno一案中,原告提供的一份未经宣誓亦未经交叉询问的南斯拉夫法学家的意见书,即被法官认可了。[lxvi]虽然规则44.1允许法官就外国法自行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都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很少主动查明外国法。
3、未能证明外国法及外国法适用错误的后果。
由于一方当事人在决定提出外国法申辩前,都会对外国法有一定的了解,因此通常,未能证明外国法的情形很少发生。从理论上看,未能证明外国法会产生驳回诉讼或适用本地法两种后果,至于实际产生何种后果,则由该外国国家法律制度的性质决定。如果属于普通法国家,则法官推定适用美国法;如为非普通法国家,则产生驳回诉讼的后果。由于规则44.1规定,法院关于外国法的决定应当被视为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因此,当事人可以就外国法的适用错误提起上诉。而且,上诉法院不受地区法院所获得的关于外国法资料的限制,在审核外国法材料方面上诉法院与审判法院有同等的自由。[lxvii]
(五)英国
1、一般规则
由于外国法被视为事实问题,因此,非经一方当事人申辩,英国法院不会主动适用外国法,即使冲突规范已指明应适用外国法;证明外国法的责任在于其主张或抗辩是以该外国法为基础的当事人,如该当事人提不出外国法证据或证据不足,法院就将把一个含有涉外因素的案件视为一个纯粹英国国内的案件来审理。
通常的外国法的证明方式是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es)。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靠简单地援引外国立法条文或外国法院判决或权威著作来证明。这些材料只能作为专家证人的部分证据被提交,但没有专家证人的协助,法院就不可能评估和解释这些材料。而且,外国法必须在每一个案件中加以证明,不能从过去审查过同样的外国法规则的英国法院的判决中推断外国法规则,这种判决只是一种“准先例”(quasi-precedent),它对于后来的法院没有约束力。英国1972《民事证据法》(Civil Evidence Act 1972)第4(1)规定:被要求就外国法作证的专家证人必须依其认知或经验是适格的,但并非必须是或有资格是外国的执业律师。他可以居住在英国,也可以是外国居民,可以是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也可以是大学教师。比如,伦敦大学东方和非州研究所的法学教授可以就加纳法作证。[lxviii]同样,纽约律师协会的成员或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也可以就美国法作证。[lxix]任何由于其职业或工作已获得外国法律实际知识的人均可以成为有资格的专家证人。
对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他并没有义务也就外国法提出专家证人。如果他未提出,则法院通常会接受一方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假定这些证据是首尾连贯、清楚且无明显错误的。[lxx]如果专家证人的意见书不被他所提交的外国法律渊源支持,那么法院会自行对这些渊源进行审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通常,由于普通法诉讼制度的高度对抗性,双方当事人都会就外国法提出专家证人,然后由法院推理裁定,或者倾向于一方的证据或者接受每一方所提出的部分证据。法院的审查范围严格限定于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外国法律渊源内,如果专家援引的是外国判决中的一段或外国法律评论书中的一段,则法院就不应当查看该判决或评论书中的其它内容。对此,Chelmsford勋爵这样表述:“法官自行探究外国法律渊源将与证明的性质相违背……法官不应拥有了解和处理外国法的机构,也不应要求得到那些懂得解释外国法的律师的帮助。”[lxxi]对于在外国法律渊源的效力方面相互抵触的几个专家证人的意见,法院有权且有义务审查这些渊源并对之自行做出决定。而对于那些相互抵触的外国判决,法院也必须就其效力作出决定,如果依据所提示的证据,法院确信某个判决并未准确表达外国法的内容,那么法院就不会适用该判决。不过,法官所作的这一切都仅限于推理判断,他的行为不能超出当事人所提供的材料范围。
传统的英国上诉制度规定,只有初审法院有权听取证人陈述。由于上诉法院是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作出裁决,因此上诉法院不能考虑新的证据方法,不过,上诉法院在评论初审法院对向其提供的文件的证据所作的解释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所以,在外国法的问题上,过去,上诉法院只能通过修正初审法官对文件和证据的解释来作出变更有关外国法含义的判决。但是现在,英国法院已抛弃了传统的上诉制度,规定上诉法院的上诉应使用重新听审的方式(by way of rehearing),因此,上诉法院有第一审法院所有的修改诉讼文件的全部权力,有就事实问题接受新的证据的全部自由裁量权。自英国上诉制度改革后,虽然上诉法院怠于介入涉及一般事实裁决的判决,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更乐于介入修正一审法院在外国法问题上的判决。因为“外国法的问题,虽然是一个事实,但却是一种特殊事实。关于外国法的事实裁决与普通事实裁决具有不同性质。”[lxxii]上诉法院认为自己有责任审查关于外国法的证据从而得出自己的决定。在英国,因外国法的错误不仅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也可以对法院上诉的裁决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上议院在这方面也不乏推翻上诉法院判决的案例。
2、例外规则
关于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规则存在着以下例外情形:
(1)简易判决
《最高法院规则》014规定的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程序是这样进行的:原告以宣誓声明提出他认为被告除关于损害赔偿金额外,对原告的请求提不出任何防御方法。但是当争议明显涉及外国法时,原告不能基于外国法未被申辩即假定外国法与英国法相同这一假设而申请简易判决。对此,Buckley法官在国民航运公司诉阿拉伯一案中这样解释:“我们的法律的确承认这种假设,即英国法与外国法相同,除非有证据证明其差异。本案原告也正是基于这一假设申请简易判决。但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明显涉及外国法律因素的案件中,原告基于上述假设而获得简易判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必须向我们证明外国法与英国法没有差异。”[lxxiii]
(2)国际义务(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这个例外规则是由Diplock勋爵在UCM诉加拿大皇家银行一案中确立的。其内容是:如果在对一案件听审的过程中,法院意识到原告所诉的合同是一个因本国已接受了一项国际义务从而使之已成为一个不可执行的合同时,即使被告没有提出有关国际义务的申辩,法院也必须自己确定这一要点,并拒绝提供强制执行合同的救济。[lxxiv]
UCM诉加拿大皇家银行是一个违约之诉,所诉的合同与加拿大外汇管理条例有关。Diplock勋爵认为,这里的“国际义务”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ivⅢ(2)(6)条规定,即“有关任何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契约,如与该国按本协定所施行的外汇管理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无效。此外,各会员国得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使彼此的外汇管理条例更为有效,但此项措施与条例应符合本协定。”Diplock勋爵认为,该规定旨在禁止强制执行违反外国法律的合同以保护外国国家的利益。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合同违反加拿大外汇管理条例的申辩,但是英国法院应当根据国际义务自行考虑争点,所以,法院要求原告证明合同不是非法的,如他未能证明,则法院将拒绝强制执行该合同。
(3)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即使在没有国际条约的约束下,“如果一英国法院意识到一个合同违反外国法律,尽管当事人并未提出外国法申辩,英国法院出于礼让和公共利益的考虑也不会强制执行这类合同”。[lxxv]这就是公共利益规则,该规则是于1958年在Regazzon诉Sethia一案中确立的。它要求,如果合同涉及一个在外国国家从事的并被该国法律认为是非法的行为,则英国法院不得强制执行该合同或给予违约赔偿。此规则的目的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执行一个对外国国家实施非法行为的合同将与礼让的职责相冲突,而且会影响英国与外国国家的良好关系,所以不应当仅仅因为当事人未提出外国法申辩就不考虑这种风险。”[lxxvi]
英国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是一个纯粹的程序规则——申辩与证明规则,它是建立在法院不得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争点这个英国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由于基本原则本身就有例外,因此,关于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的一般规则亦有例外。
四、国际公约
事实上,无论是由法院还是由当事人负责确定外国法的内容,都存在很多困难。在应适用外国法的案件中,如因无法确定外国法而不予适用或适用不当,都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早在1877年,国际法协会就曾召开会议,谋求设立国际法律调查局,负责证明外国法。1891年,国际法协会又作出决议,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对于外国法的存在或内容发生争议时,可由法院依职权,经司法部或外交部,向外国司法部提出调查请求书,以查明应适用的法律。1968年,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还专门就相互提供法律资料问题缔结了《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又称伦敦公约)。1979年,美州国家组织成员国也缔结了一项《美州国家间关于外国法证明和查询的公约》。这两个公约就缔约国间在相互查明外国法方面的协助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它们不仅允许本组织内的成员国参加,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因此这两个公约在国际上都具有重大影响。
(一)公约的实施
1、交换外国法资料的范围
由于各国在审判实践中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往往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因此,各国对于“外国法资料”的范围一般也取广义的解释,其范围不仅仅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而且还包括其他对于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或参考价值的文件。同时,所提供的法律亦不以现行有效者为限,对于过去曾经施行过的法律也在可请求提供之列。如伦敦公约规定,请求国可以要求提供被请求国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资料,以及有关司法组织的资料。被请求国的答复应当包括,在必要时,有关的法律文本、司法判例。同时还应附具使请求机关正确理解所必需的任何其他资料,诸如理论文章的摘要和立法过程中的准备文件,也可以附些说明性的注解。
2、提供外国法的程序
在提供程序上,两公约均规定由每个缔约国设立或指定一个国家级部门或中央机关。接受来自其他缔约国的请求,同时设立或指定一个或数个机构,接受来自其本国司法机关的提供资料的请求,并将其转递给外国相应的接受机构。伦敦公约规定:“请求提供资料只能由司法机关提出,即使其请求并非由该机构拟定,提供资料的请求只有在诉讼开始后才可提出。”1978年于斯特拉斯堡订立的该公约附加设定书中,对此作了补充规定:“请求提供资料,不仅可以由司法机关提出,也可以由在官方司法救助和咨询体制中代表经济贫弱者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不仅可以在诉讼实际开始后提出,也可以在诉前准备阶段提出。”这项修订主要是为了与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衔接。就提供程序而言,两公约均规定,应由转递机构直接将提供资料的请求书,送交被请求国的接受机构,如无转递机构,也可由有权提出请求的机关直接送交。在答复的送交上,如果请求是由转递机构转递的,则接受机构应将答复送交转递机构,如果请求是由请求机关直接送交的,则答复也直接送交请求机关。
在提供外国法所使用的语言上,通常提供资料请求书及其附件应使用被请求国语言或其官方语言中的一种,或附上有该种语言的译本。答复则使用被请求国语言。
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费用,依据两公约的规定和各国的司法实践,通常除了由私人团体和律师个人负责实施有关请求时所引起的费用由提出请求的国家负担外,答复不得征收任何费用或付任何开支。
3、提供外国法的拒绝
依据公约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请求国国家联络机构收到请求国有关机关递交的提供外国法资料的请求后,对提供资料的请求都应尽快答复,当答复需要较长时间时,接受机构应及时通知提出请求的外国机关,并告知其送交答复的大概日期。但是,如果提供资料的案件影响被请求国的利益、主权或安全时,则被请求国有权拒绝执行,这是各国公认的原则,对此,两公约都作了相应的拒绝提供外国法的规定。从司法实践中看,提供外国法资料涉及主权、安全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请求方要求提供立法过程中的资料,而其中有部分内容就可能涉及被请求国的主权或安全,或者请求国为确定外国法的内容而提出提供资料的请求但该案件本身可能涉及被请求国的主权或安全等。在实践中,这一问题都是由中央机关或主管机关判断确定的。
4、交换外国法情报的效力
关于外国法证明的国际公约,其目的旨在制订若干规则,以调整缔约国之间相互取得外国法的证明要点和查询方面的国际合作。因此,作为一般性的法律交流,通常不会产生交换的法律情报的效力问题。但是,在查明外国法的过程中,对于缔约国所提供的外国法资料对另一缔约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绝大多数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均拒绝给外国法与本国法相同的效力。如1968《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第8条规定:“答复所提供的资料,对提出要求的司法机构均无约束力。”1979《美州国家间关于外国法证明和查询的公约》第6条也规定:“对提出……报告的国家,不得认为应对其发表的意见负责,他不得要求其根据提供的答复内容而适用该法律,或者促使该法律得以适用。”所以,缔约国间根据公约提供的外国法情报的效力,仍受请求国国内法的约束,由请求国法院根据本国法律制度自由决定是否适用。
(二)伦敦公约的实际效果
作为在外国法证明与查询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伦敦公约,自1968年订立以来,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其间,欧洲理事会已有39个成员国签署加入该公约,此外,还有2个非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也加入了该公约。公约的主旨在于“为了便利司法机构取得外国法资料的工作而建立一个国际协助制度”,从而使“缔约国……相互提供各自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资料,以及有关司法组织的资料。”1978年,该公约签字国又在斯特拉斯堡订立了《附加议定书》,“将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互助体制在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的多边结构中,扩展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同时,“考虑到为消除法律程序中的经济障碍和使经济贫弱者在各成员国内更易于行使其权利,希望将本公约所确立的体制扩展至民商事司法救助和咨询领域。”依据附加议定书的规定,缔约国不仅可以相互提供其刑事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律和司法组织包括起诉机关的资料,及有关执行刑事处分的法律,而且提供资料请求不仅可以由司法机关提出,也可以由在官方司法救助和咨询体制中代表经济贫弱者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在提出阶段上,不仅可以在诉讼实际开始后提出,也可以在诉前准备阶段提出。《附加议定书》的订立使伦敦公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那么,自公约实施以来,其成效究竟如何呢?自1993年起,Strathclyde大学的Barry J.Rodger和阿姆斯特丹的律师Julietie Van Doorn两位学者在欧洲理事会的协助下,从事了有关公约实施成效的调研工作。调查所取得的主要数据如下:[lxxvii]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因其涉及专家与翻译的问题,所以,虽然有的国家声称没有语言困难,但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语言障碍是主要问题。从所提供的数字来看,公约机制的利用率并不高,这有可能是由于时间与费用方面的原因。至于高昂的费用应当如何分配,由于调查工作未涉及此项内容,因此我们也就无从揣测,但总体而言,过于高昂的费用无论是作为公共开支还是私人开支,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通过调研,二位学者对于公约的成效所作的结论是:“伦敦公约只是一个极为有限的成功”。
五、启示与思考
自有法律冲突的概念提出以来,外国法的证明就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性的重要议题。在最初,不同法系的国家均是从当事人申辩的角度进行外国法的证明,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萨维尼国际私法学说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才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出现了分化,外国法的“法律说”和依职权适用外国法的制度才逐渐形成。对于不同法系国家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有学者称其是“一个连续统一体”(Hartley语),英国和德国分别为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极,在两极之间则渐次排列着美国、法国、西班牙、芬兰、瑞典、瑞士、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尽管位于统一体中部的国家在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上的差别有限,但是,对于统一体的两极而言,其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在德国,法院有义务适用外国法,即使该外国法未被申辩。在英国,法院则不能适用未经当事人申辩与证明的外国法。在德国,法官有义务自行探究以确定外国法的内容,但是,在英国,法官则被严格禁止这样做,除非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申请。
在考查了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进程并对位于“连续统一体”中的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与结论:
(一)各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差异是由创设私权的内国民事诉讼的特定目的决定的。
在普通法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与法院的功能分配是建立在民事诉讼是一种纯粹的私人事务这一理念基础上的,因此其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和维护私权。争点的提出与调查均由当事人完成,“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性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lxxviii]在这方面,普通法国家学者相信,“最少的司法干预是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最有效的方式”(摩根语)。于是,法官的作用就显得极为有限和被动,法官仅限于对当事人,更确地说是当事人的律师所提出的、调查的及辩论的争点进行裁决,或对当事人提出的动议予以程序上的准许或禁止。“律师之间就证据开示而展开的准备程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法官原则上只是在双方意见不一致而提出了请求裁定的申请时才进行介入的。……当事者是展开程序的主体,法官的角色仅仅停留在被动的裁决者这一位置。”[lxxix]
同样,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团审理方式也是基于民事诉讼的私人性质确立的。由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对法律没有专门的研究,不作为职业化的化身,只是通过随机遴选临时组成的凭感性理解以认定案件事实的群体,因此,在这种审理方式下,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可以运用丰富的经验和职业化的技能在一系列询问中对陪审团的事实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使陪审团形式意义上的审判权实质上演变成当事人的律师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的诉讼技能争辩,从而使陪审团审理方式成为诉讼公众化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当事人具有高 度的意思自治选择,而且,法官还为维护陪审制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义务。譬如,F.R.C.P.第38条第1款规定:美国宪法第7修正案宣布的由美国制定法赋予的当事人要求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受到保护,第39条规定,在本来有权要求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未提出要求不问其懈怠,法院基于申请,或以裁量作出由陪审团审理争点的部分或全部命令,除非(1)当事人或其记录在案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书面协议,或在公开法庭上提出口头协议,并记录在案同意由法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该案;(2)法院基于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提出部分或全部争点并不涉及美国宪法或美国制定法规定的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彻底贯彻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的原则。
由于普通法国家创设私权的内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因此,外国法作为直接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相关的问题,其证明程序是不可能交由法院去处理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想彻底查明外国法这一关涉案件的重要问题而不过份介入私人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但这种介入无疑会违反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的原则。所以普通法国家宁可将外国法的问题归入当事人双方进行的攻击与防御之中,从而保证法官能够始终处在中立的立场上听取双方的辩论,使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具有高度尊重私权意见自治和程序中心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在普通法国家的对抗制民事诉讼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事实有无限的控制权,适用法律的事实条件是由当事人独立架构的,因此,他们的私权意思自治实际上不会限止于争议的事实,而是必然延伸至应适用的法律方面。相对于数量较少的法官和庞大复杂的法律体系而言,当事人的律师很自然地就承担了为支持他们客户的申辩而进行的对法律权威书的探究工作。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中,律师在搜寻和评价对抗性的先例和制定法方面不仅对当事人具有愈来愈多的责任,而且他们对于法院的责任也同样如此。律师有责任指挥法官的注意力,使他注意到那些有可能被他忽略的法律权威书,因此,法官是依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所以就外国法而言,虽然美国法视其为法律,但在基于普通法国家民事诉讼目的基础上形成的充分尊重私权和高度对抗的大背景下,由当事人及其律师证明外国法是必然的。
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程序法是以下述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如果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法官应有权、实际上是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的情况,尽可能地避免前后不一致和含糊不清,消除因为诉讼人或者律师不细心和不懂技术所造成的失误。[lxxx]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在大陆法国家中,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即使开始纯粹是私人间的事务,一旦交给法院处理就变成了公共事务”。[lxxxi]因此,私权公法化是大陆法系国家中创设私权的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在这方面,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1879年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由于正当欧洲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所以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点,在程序上都是由当事人自由支配,国家尽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后来,随着社会形态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促使国家自1898年以来每次修订民诉法典,都相应对当事人自由支配程序增设限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法律结构特征,即国家干预加强,法院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提高,强化了法院调查证据的职权行为,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自近代以来,在德国的民事诉讼目的论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维护法律秩序学说。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司法机关的活动即民事诉讼来对抽象的制定法加以具体化和个别化,并适用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民事案件,才能最终完成私法秩序的构造。对此,德国民事诉讼法学者标罗(Bu low)曾断言:由于私法案件的当事人对抽象的私法及其法律效果缺乏统一的理解,造成法律判断的冲突。因此国家必须预备解决这种冲突的手段,这就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正是从内部来协助私法法规实现它未能完成的私法秩序的构建。[lxxxii]正是基于这种诉讼目的论的指导,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与当事人一起澄清争点是法院的职责,而且,在法院认为必要时,法院可以和当事人一起讨论案情和争点,并向当事人发问。由于没有严格的审前与审判阶段的划分,法院可以在诉讼中的任何阶段与当事人讨论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法院具有三种权力:澄清不明确的陈述,将当事人的指控(可能是以外行语言表达的)转化为精确的法律术语,指出有关的和无关的指控及证据。如果一方当事人已宣称,案件事实涉及某一特定法规的适用,而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另一法规,它就必须提醒当事人注意这一点,并给予其补充陈述的机会。法院的此项保护性职权,实际上是当今德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大宪章”。[lxxxiii]很显然,由于法官已在其头脑中对案件进行归类,因此,法官事实上是积极地、有时甚至带点强制性地构架了案件的事实争议与法律争议。法官的这种主导性地位在对待证人的态度和方式上尤为突出。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法院的证人,当事人与证人严格分开,不依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区分原告方证人和被告方证人,证人作证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专家证人通常都是由法院基于自己的意愿而传召的。法院不必依赖当事人,就可引入专家证人。虽然一方当事人也可以让自己挑选的专家证人参加诉讼,来反驳法院指定的专家,但法官一般不会直接把当事人自己找的专家证人的意见作为判案的根据,而是将其意见作为反证,成为法院更换专家的原因或理由。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人制度均与德国法的规定相似。
在民事诉讼中,大陆法系国家律师的工作仅限于对证人的提名以及在开庭审理时,经审判长的许可,向证人作补充发问。因此,有人称大陆法国家的民事诉讼为“无律师的诉讼”。事实上,的确在某些大陆法国家,当事人可以在无律师代理的情形中进行诉讼。比如,在德国的地方法院(Amsgerichte)诉讼,当事人便不需要律师代理(诉讼法典第78、79条),而许多涉及外国法因素的案件都在地方法院的管辖权限之内。在奥地利,当事人也可以在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劳动法院及婚姻诉讼中自我代理。在荷兰,当事人可以在地区法院亲自诉讼。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丹麦、芬兰和瑞典,律师代理在全部诉讼程序中都是非强制性的。日本和韩国实行的也是任意代理主义。与这些国家法官的主导性、操纵性地位相比,律师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集确定事实、确定法律与适用法律三种职能于一身,在这种民事诉讼结构中,无论外国法属于事实性质还是法律性质,无疑都会被法官依职权确定。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法国法视外国法为事实,但法官在外国法的证明方面依然起主导作用,而法国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颇多前后不一致的决定的原因。由于大陆法国家从国家公权的角度出发,规范民事诉讼。因此,即使“法官知法”的前提中不包括外国法,法官也仍然有权自主确定外国法的内容,并要求政府机构帮助他完成这一职责。大陆法国家创设私权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私权公法化的特点是构成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根本原因。
质言之,构造不同法系国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事实说”与“法律说”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外国法的证明作为一种具体的操作程式,实则体现了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表达了立法者预期通过民事诉讼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即民事诉讼的目的。普通法国家将诉讼作为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最终手段,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执和冲突,因此坚持程序中心论,注重以程序制约和限制法官的权力,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导地位,实现当事人私权意思自治。而大陆法国家则坚持“程序的目的不过是实体法内容的实现,具体说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民法规定的权利,或者说在于维持民法典所预定的私法秩序”,[lxxxiv]即实体中心论。在这一目的的主导下,法官具有最高的权威,能够依职权就其自己的意愿和观点出发积极介入到整个诉讼过程当中。如果就此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形成这些差异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普通法国家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仍然是以理想化的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为终极目标,相信完全的竞争市场是利益冲突的最佳协调者,能够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因此,普通法国家建立在这种公平、放任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诉讼程序坚持个人自治,强调民事程序以内在的方式来满足解决纠纷的直接需要。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在一个现代的复杂经济中,基于现代福利国家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确保经济体制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起来。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更倾向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上的法律秩序日益具有官僚政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特征,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自然享有广泛的监督与动议权。不同法系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而不同的目的论才是决定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差异的本质原因。
(二)在冲突规范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后,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正义的原则使外国法的证明更具有证据规则的性质。
传统的国际私法学说,认为国际私法的主要目标是在于贯彻简单、方便的原则以达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的目的。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判决的确定性(certainty)、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一致性(uniformity)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冲突规范成为国际私法的核心内容,在解决涉外民事案件时,只要法官对案件的性质进行识别,确定具体案件的“范围”即法律关系在性质上的归属,相应的冲突规范便会直接、主动地指示出案件应适用的法律。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相信,冲突规范的适用能够达到不论案件在何国法院审理,都会适用同一法域的法律并使判决结果趋于一致的目的。他们“还把冲突规范比作火车站中的一套信号灯,并把法官比作火车司机,他无需知道行驶前方是什么站,只需要按照信号灯所提供的信息往前开就行了。换言之,法官无需考察冲突规范所指向援用的那个国家实体法的具体内容,只要适用它就算完成任务。”[lxxxv]冲突规范及相关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法律选择规则的唯一内涵,而国际私法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制订、修改及运用冲突规范。
二战以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及科技的巨大进步,不仅出现了诸如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这些新的类别,而且也使国际民商事关系更趋复杂化,传统的、机械的冲突规范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国际民商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美国的柯里教授指责以冲突规范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是概念式的、毫无道理的、无头脑的,甚至称它是一个诡辩的、神秘的和失败的领域。他在其著作中宣称“我的观点是,这一体系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法律选择规范,我们会更好些。”同样,卡弗斯教授也指出,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只是一种机械性的盲目的方法,它依赖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冲突规范,指令法官适用一定的法律,因此很可能使判决结果不公正,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或危害法院地的利益。[lxxxvi]传统的冲突规范由于在解决法律冲突案件时,依据预先确定的联系因素去寻找具体案件的准据法,因此,从根本上忽视了同一种类案件的事实构成的复杂性,结果无法实现案件的公正解决。同时由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致使它将各类不同的法律冲突混为一谈,而对选择性冲突规范和重叠性冲突规范所作的“有条件”和“无条件”两种类别的区分又使法律适用问题更趋复杂化。这一切都说明冲突规范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个法学家不会不注意到,现代世界正在嘲笑各国的冲突法制度,国际私法实际上是对商业行为和解决争议而人为设置的障碍”。[lxxxvii]事实上,冲突规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缺陷是其内在固有的,它因依赖于萨维尼的国际私法学说体系而错误地推测道,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超级法律”,这个超级法律通过指导或限制的方式预先就确定了可资适用的法律选择规范,这种盲目性导致了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不公正,从而使法律最终丧失其正义性质。因此,冲突规范的这种缺陷在于其存在前提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它自身所不能够克服的,试图通过对冲突规范本身进行修修补补、抱残守缺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冲突规范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由于传统冲突规范的盲目性、机械性的特点愈来愈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那种试图以一种方法来决定法律冲突中碰到的一切问题的法律适用规范已被摈弃。面对社会的发展,现代法律选择制度在法律的安全性与灵活性的两难选择中,宁愿后退一步,放弃所谓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判决一致性的目的,代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等多种方法的运用。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传统国际私法的那些目的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阻碍了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正的实现。例如,传统侵权行为法律的适用原则是以侵权行为地法为主结合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共同住所地法,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以重叠法院地法对侵权行为地法进行限制。这种法律适用原则目标明确、具体、稳定,便于法院掌握适用,但却过多地考虑行为地或法院地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当事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利益,其实质只是解决了行为应由何国法律管辖的问题,却根本忽略了法律适用的后果,与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正目的不相符,而且,把偶然的连结因素作为确定准据法的因素,对当事人而言也显失公正。所以,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官放弃过去坚持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信条和法学原则,应高度重视社会的现状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应盲目地信仰无所不包的固定不变的法律规则,法律的适用不是如何运用法律,而是能否达到法律的社会目的,即公平正义地适用法律。因此法官在法律选择过程中应奉行最密切联系原则和追求案件的具体正义原则,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考虑当事人的公正期望,通过对各种有关的联系因素和相关的具体利益的分析比较来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减少先入为主的立法选择,宁可背叛陈旧的规则,也不能牺牲具体的正义。
为了贯彻最密切联系和实现具体正义的原则,法官在处理法律冲突案件时就必须在尊重具体案件事实构成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加以区别对待。这样无疑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加强了,而要使法官不从其个人好恶或自己的利益观念出发判断是非,就必须强化当事人在程序上的主导性,通过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制约法官的权力,即由当事人双方积极提出主张和法律内容及事实构成的材料,当事人和法院三方之间围绕这些材料进行认真的对话,通过“这样一种具有透明度和可视性的程序过程来逐渐形成并获得客观性”。[lxxxviii]事实上,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和具体正义的实现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为切实的保护,而对于当事人在具体的案件中有怎样的合法权益,需要得到何种保护,当事人及其律师才有最具体的了解。因此,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实现具体正义原则的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当事人的自主性,其实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当事人向法院展示其在不同法律规范下的利益对抗,要求法院切实保护其合法权益,并由法院对之进行分析、判断进而适用具体法律的过程。所以,在涉及法律冲突的案件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参加命题”,法官所作的选择与判断只能是盲目的与随意的。要防止法官的这种随意性,切实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把对当事人的保障扩展到选择和适用法律的程序,即外国法的证明方面,使法官在法律问题上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通过当事人及其律师以“内在视点”看待法规范、法体系,使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向当事人倾斜,把举证责任作为外国法证明的落脚点,这样才能使法官有意识地、深入地对法律内容进行分析,防止法官的恣意专断。“这就是从程序中产生实体规范的过程实现正当化的权利。”[lxxxix]由此可见,一方面,萨维尼国际私法学说体系的前提性错误使传统冲突规范见弃于现代社会,因此,外国法的证明中依职权适用外国法已丧失其法律前提,另一方面,在最密切联系和实体具体正义原则的指导下,外国法的证明早已脱离了简单的法院选择和确定法律的窠臼,从根本上转而向当事人倾斜,并具有证据规则的性质,成为实现具体正义的有利的程序保障。
(三)功能分析的结果表明,构建以当事人为主导的、灵活开放的外国法的证明制度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法律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并非概念性的法律结构,而是这些法律结构应当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其目的就在于产生一个由功能综合构成的体系。功能分析由于立足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要素的综合作用,因此能够对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本质性的把握。具体到法学领域而言,“如果在功能上把法律看作是社会事实情况的调节器,那末,在每个国家里的法律问题都是相似的。人们能够在世界上所有的法律秩序中提出同样的问题,甚至在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或者处于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里,适用同样的标准。”[xc]从功能分析入手,对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不同国家的现行制度进行比较、归纳后,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外国法的证明的“事实说”与“法律说”只是一种表象。即使一国视外国法为法律,它也并不必然将外国法与本国法同等对待,对这些国家而言,外国法是法律,但却是另类法律(law of a different kind),对于那些视外国法为事实的国家而言,外国法也被看作是一类特殊的事实(fact of a peculiar kind)。而且,在许多国家规定的上诉程序中,依事实而上诉较依法律上诉要困难得多,许多国家的上诉法院只负责法律审,但在对待外国法的问题上,事实与法律的区别实则有限之至。当一国视外国法为法律时,它并不必然允许因外国法适用的错误而上诉至最高法院,如德国,而在另一方面,视外国法为事实的国家,在能否因外国法的适用错误而上诉这个问题上,外国法与本国法被同样对待,如英国。况且,即使是处于“连续统一体”两极的英国与德国,它们之间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差异也不应被过份夸大,因为在合同和财产领域,两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就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体系产生了一种确实奇特的对比。这显然不是说在法院地法律体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法律体系,而是说法院地法律体系在其设立的法官眼里具有优越性。这并不是否认外国法律在其所管辖的领土上以及对于它所针对的法官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法律。这只是说,对于受理案件的法官来说,这种法律本身并不具有出自该法官所服从的权力机关的强制性。这是一种对抗力的问题,而不是性质的问题。”[xci]事实上,确定事实不能与确定法律及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截然分开,法律和事实这两方面的争执点贯彻于诉讼程序进行的始终。诉讼的进行不断地推动这两种争执点相互交叉、相互重叠,因此,二者是作为同一诉讼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被提出并加以评判的。引证事实总是带上法律的色彩。所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常常是很困难的,法定证据制的存在更说明事实与法律的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
功能分析揭开了外国法证明的“事实说”与“法律说”的面纱,使我们能够从更为本质的层次即证据制度上看待外国法的证明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涉及法律冲突的案件所关涉的实际上主要是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益问题,因此,在解决法律选择问题时,法院所关心的应当是案件当事人的私人利益,正如艾伦茨维格教授所指出的:“政府除了在海事法领域以外,关于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方面的利益,只存在于诸如税收或货币问题的一些例外案件中。”凯格尔教授则更加明确地认为:“我们在国际私法中所追求的正义,要求对利益进行估价,这同任何其他判决所要求的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政府利益,而是私人利益。”[xcii]由于民事权利属于私权性质,国家不加任意干预,因此在证据制度中包括举证责任在内的功能运作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私力救济的能力。处分原则作为民事程序的本质体现,历来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一般直接涉及其实体权益问题,所以法官过于介入当事人之间就外国法而产生的抗辩,实际上是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失法官中立的地位。因为“从国家处理纠纷的观点来看,公共权力无法平等地一一介入私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与摩擦。从近代法治国家的司法权性质来看,司法权不能积极介入市民生活,如果需要国家介入的话,主要应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来实行。”[xciii]涉外民事诉讼争议的事项仍然主要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权益纠纷,因此,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自己在程序上的自由处分权利。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上的适用范围也已由合同领域向侵权、不当得利、夫妻财产制等方面扩展。随着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连结点数量的不断增多,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的趋势。
外国法作为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直接问题,它在证明方式上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当事人的申辩与举证。实际上,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外国法的依职权适用并不会给国家或政府带来什么利益,而且,国家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原本就不具有什么利益,真正的利益方是当事人。因此,如果在外国法的证明上不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申辩与证明机会,仅由臆断的准据法替代当事人的自主选择与申辩,只会造成不公正的裁决。“法的判断不许当事者染指的结果往往是在程序上带来对当事者的不意打击。在法律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日常化了的今天,承认当事者意思自治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内及法律问题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过份强调法律问题严格区别于事实问题只能使纠纷难以得到恰当地处理。”[xciv]而且,依职权适用外国法本身不仅对法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给法院带来过份繁重的任务,其实际实施情况也并不顺利,辅助法官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伦敦公约就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极为有限的成功”。
构建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外国法证明制度并不意味着全然放弃国家干预,在涉及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案件中,譬如关系到公共利益、国际义务、海事、税收和货币政策等案件,法官就应当从国家公权的角度出发,依职权处理外国法证明中的程序事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法官的定位,在绝大多数的涉外法律冲突案件中,面对私人利益的纷争,法官就是一个中立裁决人,外国法主要应由当事人主张和申辩,法官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辅助性的调查,也可以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帮助经济上的贫弱者从事外国法的证明,但应当明确的是,外国法的证明程序必须是由当事人占主导地位,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外国法的申辩与证明上的自主权。法官仅在涉及国家和政府利益的案件中,才不受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限制,有义务依职权查明并确定外国法。我国关于外国法的证明,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93条规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文件中则是将外国法规为法律,由法院主动查明,同时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辅助查明:①由当事人提供;②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方的中央机关提供;③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④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⑤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于我国并未对民事诉讼的目的展开有意识的探讨,而过去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采取的又是超职权主义结构,因此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强化处分原则已成为目前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前提下,纵观当前世界各国在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上的发展趋势,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出发,以当事人为主导,法院职权进行为辅应当是构造我国外国法的证明制度的发展方向。
注释:
[i] 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vol.1. 12th edn. p506-511.
[ii] 参见莫里斯:《法律冲突法》,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p511-512页。
[iii] 参见李双元、金彭年编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第59-60页。
[iv] Chesh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2thed, 1992,Chap 7.
[v]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12thed,1993,p.8.
[vi]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vi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viii] 参见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第35-36页。
[ix]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x] Jhering:Geist des Zomischen Rechts, vol.1,9th ed. p.8.
[xi] 参见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7页。
[xii] 关于法律冲突法在英国的历史发展,详见W.S.Holdsm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526.1927.
[xiii] J.H.Beale, Conflict of Laws 1663-4,1st ed. 1935.
[xiv] See Uniform Proof of Stature Act, 1920; Uniform Laws Annotated 9B 626,1966.
[xv] See Conmissioners, Prefatory Note, Uniform Laws Annotated 9A 550-551,1965.
[xvi] 截止到1966年7月1日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44.1生效前,包括California, kansas, Maryland等在内的16个州均对其外国法的证明制度作了根本性改变。
[xvii]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257-258。
[xviii] New York Civil Practice Act 1943, §343-a.
[xix] [英]P.H.科林:《英汉双解法律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p367.
[xx] Miller, "Federal Rule 44.1 and the ‘Fact’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Foreign Law:Death-Knell for a Die-Hand Doctrine," 65 Mich.L.Rev.613,1967.
[xxi] 梅仲协:《国际私法新论》,台湾,1980年第3版,第28页。
[xxii] G.Broggini,Die Maxime "Iura Novit Curia" und das auslanudische Recht, 155Archiv fu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469,457,1956.
[xxiii] Sohm, Mitteis, Nengen, Institntiomen 1520.
[xxiv] Ph.J.Eder, Tentative Note on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Latin Americ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 INT,L & Comp. L. Proceedings 160.
[xxv] G.F.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1. Teil. p150, 2. Teil, p151.
[xxvi]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 186, p24-28.
[xxvii] 39 Entscheidungen des Reichsgerichts in Zivilsahen 371, 376.
[xxviii] OGH 8.10.1964,10b, 59/64,cited by H.Koh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5thed, 1988, p26.
[xxix] B.Vouilloz, Le Role du Juge Civil a L,Egard du Droit Etranger, 1991, p7-8.
[xxx] R.D.Kolleuijn, American-Dutc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76.
[xxxi] Taborda Ferreira-Guggenheim, Portagal,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07.
[xxxii] Andersen, 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in Scandinavian Legal Systems, A.B.A.Sec.Int,l And Comp. Law, Proceedings 135.
[xxxiii] Reinhold Geimer,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βrecht, 1987,note 2141.
[xxxiv] Bundesarbeitsgericht, judgment of 10.04,1975,R.I.W. 1975,p521.
[xxxv] 沃尔夫:《国际私法》,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1页。
[xxxvi] Christian von Bar, Internationales Privatecht, vol.Ⅱ,1991,p341.
[xxxvii] Jan Kropholler,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2d edn,1994, p519.
[xxxviii] 《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如果外国法的内容无法查明,应适用瑞士法”。
[xxxix] Francosis Knoepfler, op. cit. Revue critique, 1988,p234,转引自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xl] Civ. 12May 1959.
[xli] Compagnie algerienne de Credit er de Banque v. Chemony, civ. 2 Mar.1960.
[xlii] 〖ZW(〗Civ. 9 Feb. 1983, Civ. 24 Jan. 1984.
[xliii] Civ. 25 Nov. 1986, Civ. 25 May.1987.
[xliv] Civ. 11 and 18 Oct. 1988.
[xlv] Civ. 4 Dec. 1990.
[xlvi] Lagarde, Rev. crit. dr. int. pr. 1994, p332,337.
[xlvii] Civ. 6 Feb. 1843.
[xlviii] 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xlix] Civ.6 Dec. 1977; Civ. 4 Apr. 1978.
[l] Lautour, Cour de cassation, Civ. 25 May 1948; Societe Thinet, Cour de cassation, Civ. 24. Jan. 1984.
[li] Civ. 24 Jan. 1984.
[lii] Civ. 15 June. 1982.
[liii] Ch. com. 16Nov. 1993.
[liv] Civ. 29 July 1929.
[lv] Civ. 6 Dec. 1972.
[lv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2页。
[lvii] 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lvii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7页。
[lix] 同上,第468页。
[lx] Civ. 2 Feb. 1966.
[lxi] Wright & Miller, Federal Practice & Procedure §2443,p403.
[lxii] 28 U.S.C.Rule 44.1,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1966 Amendments to Rule, p292.
[lxiii] 28 U.S.C.Rule 44.1, 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1966 Amendments to Rule, p292.
[lxiv] Re Fotochrome, Inc., 377 F. Supp. 26, 29.
[lxv] Burnet v.Trans World Airline, Inc. 368 F.Supp.1152.
[lxvi] Ramirez v.Awto.Blancos Flecha Roja, 486 F.2d 493,497.
[lxvii] 9 Wright & Miller, Federal Practice & Procedure p2443 at 415.
[lxviii] Mccode v.Mccode, The Independent, 3 Sept, 1993.
[lxix] See X,Y and Z V.B, 1983 2 All E.R.464.
[lxx] 过去,外国法的问题由陪审团决定,现在根据1987《最高法院法》S69(5)的规定,外国法的问题由法官独自决定。
[lxxi] 11 ER 1168, p1175.
[lxxii] 2 L Loyd ,s Rep. 233, p286.
[lxxiii] [1977]LLoyd,s Rep. 363, p366(CH).
[lxxiv] [1983]A.C. 168, p189.
[lxxv] [1958]A.C.301.
[lxxvi] [1958]A.C.301.
[lxxvii] 有关调查内容详见“Proof of Foreign Law:The Impact of the London Convention”, I.C.L.Q., Jan.1997,p151-173.
[lxxvii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ZW)〗
[lxxix]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lxxx]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页。
[lxxx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26页。
[lxxxii] 标罗:《诉讼与判决》,转引自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lxxxiii] Peter Gottwald, "Simplified Civil Procedare in West Germany", 3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p687,1983.
[lxxxiv]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8页。
[lxxxv]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lxxxv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页。
[lxxxvii]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lxxxviii]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21页。
[lxxxix]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xc]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xci] 巴蒂福尔、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53页。
[xcii] 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第139页。
[xciii] 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1996年版,第105页。
[xciv] 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出处:转载于中国法学网
|